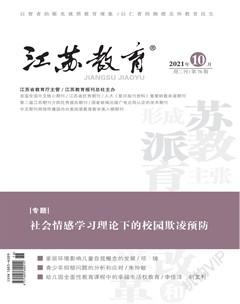欺凌主題校園心理劇創作的實踐與思考
【摘 要】校園心理劇作為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一課三式五策”心育行動的具體形式,有助于處理學生的情緒及行為問題,幫助學生提升自我發展、塑造健康人格。在編排原則方面,欺凌主題校園心理劇的編排以學生為主要角色、以體驗為主要方式、以成長為主要目的;在主題選擇方面,可以通過校園欺凌的類型、期望達成的目標來確定主題;在角色塑造方面,要讓學生了解可尋求幫助的對象及求助方法。
【關鍵詞】校園欺凌;校園心理劇;劇本創作
【中圖分類號】G441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005-6009(2021)76-0018-04
【作者簡介】胡靜嫻,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霞浦學校(浙江寧波,315807)教師,一級教師。
校園欺凌是一個或多個學生對其他學生進行持續的、集中的故意性傷害,從而造成被欺凌學生身心受到傷害的行為。欺凌事件會給學生成長帶來不可逆的心理創傷,甚至引發傷害他人或者自我傷害事件。校園心理劇有助于處理學生的情緒及行為問題,幫助學生提升自我發展、塑造健康人格。本文基于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一課三式五策”心育行動“三式”中的原創心理微劇,從欺凌主題校園心理劇的創作流程入手,為具體的實踐工作提供參考。
一、欺凌主題校園心理劇的編排原則
1.以學生為主要角色。
校園心理劇的選材應源于學生的真實生活,以學生為主要角色。校園欺凌行為本身具有隱蔽性,往往不易被教師察覺。教師可以通過欺凌主題的心理健康教育課、調查問卷、心理測量、個別訪談等方式深入學生生活,了解學生經歷的校園欺凌事件,剖析他們的內心沖突,再將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提煉成一部生動形象、貼近實際的校園心理劇。
2.以體驗為主要方式。
校園心理劇不是單純地向學生傳授知識,而是讓學生對校園欺凌產生沉浸式的共鳴與感悟。演員或觀眾中也會有經歷過校園欺凌的學生,出演或觀看心理劇能夠讓他們在劇中體驗自己當時的情緒和想法,也有機會體驗其他角色的內心沖突。在體驗的同時,他們又有機會從角色中剝離出來,以全面的、全新的視角看待校園欺凌事件。而沒有經歷過校園欺凌的學生也能在心理劇中擁有模擬式的體驗,懂得如何保護自己。
3.以成長為主要目的。
校園心理劇是同伴心理互助的一種重要形式,它促使學生在交流、碰撞的過程中學會互助和自助。校園心理劇重視的就是這種共同的成長,演員和觀眾共同成長,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共同成長,主角和配角共同成長。這種成長還體現在應對方式的改變上。欺凌主題校園心理劇的故事發展往往一波三折,遵循著“問題產生—消極應對—矛盾爆發—資源介入—積極應對—成長轉變”的規律。校園心理劇的前半段更多地以共情、接納為主要手段,讓觀眾和劇中的角色一起進入成長的準備狀態;后半段則更多地以影響、改變為主要手段,最終促使學生實現自我成長。
二、欺凌主題校園心理劇的主題選擇
1.根據校園欺凌的類型確定主題。
校園欺凌根據欺凌手段、方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身體欺凌、言語欺凌、關系欺凌、性欺凌和網絡欺凌等。身體欺凌是所有欺凌形式中最容易辨認的,它有著相當具體的行為表現,如踢、打弱小的同學。如原創心理劇《To be or not to be》中就展現了身體欺凌的一幕。
胡圖圖:聽說你在班級QQ群里說“矮子的智商弱爆了”?
小宋:我說的是游戲里的人物。
胡圖圖:那你覺得我長得高嗎?
小宋:還好。
胡圖圖一點頭,他的小跟班立刻重重地拍了一下小宋的后腦勺。
小宋:高。
胡圖圖又一點頭,另一個小跟班直接抓起小宋的頭發,并且捂住他的嘴巴。胡圖圖上來就給了小宋兩巴掌。
言語欺凌是學生之間常見的一種欺凌形式,主要通過語言來刺傷或嘲笑別人,這種方式造成的心理傷害有時候比身體上的攻擊更嚴重,并且言語欺凌很可能是身體欺凌的前奏。原創心理劇《我是劉恒凱》中的主人公就因為個子矮小被同學嘲笑,還有同學取笑他的名字——“恒凱=很矮”,導致他飽受自卑帶來的困擾。
關系欺凌是最常見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一種欺凌形式,通常通過拉攏他人來排擠某位同學,使處于弱勢的同學被排擠在團體之外,或借此切斷他們的社會聯結,讓他們覺得被孤立。被欺凌學生常常會覺得無助、沮喪。在原創心理劇《我們不孤獨》中,轉學生楊悅因為成績優異得到教師的贊賞,卻被妒火中燒的班長張怡聯合其他同學孤立了。
張怡:她有什么了不起的,還不是因為她媽媽是大學教授、和老師關系好,老師才表揚她的。
高穎:看她平時一副清高的嘴臉就讓人惡心,我看你的作文寫得比她好多了,她居然還能得獎?得獎有什么了不起的,哼!肯定是在背后拍老師馬屁,馬屁精!
林嫻:她剛轉來我們班時,我們幾個跟她最要好,現在卻害得我們要重寫作文,可惡!
張怡:她走過來了,有什么好得意的。你們要是還把我當朋友,就都不許理她。
性欺凌包括有關性或身體部位的有害評論,或是流傳有關于性的謠言,還可能有更直接的身體上的侵犯。網絡欺凌也是目前較常見的一種形式。現在的學生處于信息爆炸的時代,他們能通過快速、多元且便利的渠道進行聯系,由于具備匿名性、傳播廣等特性,網絡成為欺凌發生的重地。
2.根據期望達成的目標確定主題。
校園心理劇在主題的選擇上不一定要圍繞欺凌的種類,也可以通過培養學生的某種積極品質幫助他們應對校園欺凌,以達到預防和干預的目的。北侖區預防校園欺凌課題組基于社會情感學習理論,制定了預防校園欺凌系列心理劇的三大目標:同理——直面欺凌;融通——性格養成;互助——同伴相助。“同理”是讓學生在與他人產生矛盾時能夠理解他人的感受,換位思考,減少極端情緒的產生,避免做出傷害、欺凌他人的行為。“融通”建立在獲得同理能力的基礎之上,如通過校園心理劇讓學生學會做負責任的決定,積極地看待生活中的不確定因素,養成融合、包容、主動的解決問題的品質。“互助”是讓學生通過校園心理劇學會處理人際矛盾,獲得并維持友誼,互相幫助。在選擇校園心理劇的主題時,也可以從培養這些積極品質的目標切入。
三、欺凌主題校園心理劇的角色塑造
1.欺凌者角色。
欺凌者往往是一些沒有耐心、做事魯莽沖動、喜歡支配他人的學生,他們對他人缺乏同理心、不愿意遵守規矩,認為暴力行為可以快速解決問題或認為欺凌他人是很“酷”的表現。在塑造欺凌者角色時,除了要展現他們的性格特點,還要揭示欺凌者這些行為的產生原因以及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他們是如何在認知、行為、情感上發生轉變的。這一點尤為重要,這表明欺凌者也是可以成長的,欺凌行為也是可以發生轉變的。原創心理劇《也是霸凌》關注了反擊型欺凌,有部分學生因受到過其他人的欺凌而采取消極的應對方式,最終自己也成了欺凌者。劇中對欺凌者心路歷程的展現有助于他們得到理解,進而放下心中的“執念”并做出積極的改變。
2.被欺凌者角色。
通過調查研究發現,我們往往認為有身體缺陷、朋友少、受教師批評較多、成績差、家庭貧困的學生容易被他人欺凌;而身體強壯、朋友多、家庭條件富裕的學生不容易被他人欺凌。而真實情況是,成為欺凌對象的學生并不一定擁有某一個特征。以原創心理劇《我們不孤獨》為例,主人公楊悅心地善良、成績優異、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卻受到同學的排擠;張怡十分優秀,是班長,也是老師信任的學生,卻因一念之差帶頭排擠新同學。因此,在編排心理劇時,塑造被欺凌者角色不宜有局限性、刻板印象,以此呼吁師生關注欺凌隱患。
3.旁觀者角色。
旁觀者角色常常作為欺凌主題校園心理劇中的配角出現,其實他們才是學生中的大多數。而且校園欺凌事件對旁觀者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旁觀者包括不同的類型,有的會協同欺凌者,有的會勇敢地保護被欺凌者,有的則置身事外。旁觀者可能出現的內心沖突有“要不要向老師報告?”“如果我站出來說‘不,是否也會被欺凌?”也可能面對“想幫卻不知道該如何幫忙”的困惑。在編排校園心理劇時,可以將旁觀者角色的內心沖突展現出來,并對他們進行積極的引導。原創心理劇《To be or not to be》直接將旁觀者小樂作為本劇的主角,利用心理劇中的多重替身技術將旁觀者小樂正義面和懦弱面的沖突展現出來。
正義面:怎么說小宋也是你的同學,朋友有難,該出手時就出手。
懦弱面:一出手必遭斷手。
正義面:要不你和班長說一下,讓他去告訴老師,這樣既方便又安全。
懦弱面: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遲早會查到你頭上,難道你認為能逃得掉?
4.其他角色。
在欺凌主題的校園心理劇中,除了欺凌事件的當事人以外,還可能存在其他角色,如父母、班主任、心理健康教師等。這類成年人角色應該伸出援手,要有一雙敏銳的眼和一顆敏感的心。父母要能夠從孩子的眼神、表情、肢體動作等覺察到孩子的細微變化;教師要能發現校園欺凌的征兆,采取積極的措施促使欺凌者改變、幫助被欺凌者成長、激發旁觀者的正義心。通過觀看校園心理劇中這些角色的處理策略,學生可以知道尋求幫助的對象并掌握尋求幫助的方法。
四、欺凌主題校園心理劇的注意事項
1.強調立意上的正向引導。
欺凌主題的校園心理劇通常演繹的是心理問題甚至心理創傷的成因、表現和解決方法。因此,在創作欺凌主題校園心理劇的過程中,要著眼于開發學生的自身潛能、塑造健全人格。在校園心理劇的結尾部分,要讓學生看到積極的應對方式能更好地推動問題解決,避免出現自傷式、回避問題式的結局。
2.注重結束后的分享反饋。
校園心理劇對學生的影響不應該隨著劇目的散場就戛然而止。在展演過后,教師可以引導演員和觀眾進行感悟分享。一方面,觀眾的反饋可以將劇本再次完善,在下一次創作和展演時有提升的空間;另一方面,分享有助于校園心理劇的內涵被進一步放大。每一位學生在參與創作、觀看展演后都有可能聯想到不同的經歷和感受。這一部分是校園心理劇發揮作用的關鍵,教師要引導每一位學生意識到預防校園欺凌問題的重要性并學會在認知、情感和行為上進行心理調節。分享過程中還要注重營造真誠、尊重、傾聽的氛圍,讓學生在安全的環境中結合自身實際談真實的感受。
【參考文獻】
[1]韋紅斌.初中生校園欺凌應對策略探析[J].江蘇教育,2017(96):55-56.
[2]朱曉艷.發展支線故事 走出校園欺凌[J].江蘇教育,2019(4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