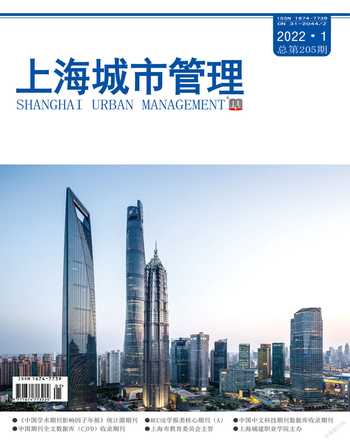“區域經濟韌性”視角下廣東防范重大經濟風險的實施路徑研究
蔡錦萍 陳世棟










摘要:全球化的不確定性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壓力給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性帶來潛在風險,如何通過建設“韌性經濟”體系來防范重大外部沖擊,成為各界共同關注熱點。根據區域經濟韌性的相關理論,選擇經濟穩定性、經濟結構多元性、經濟創新能力及經濟系統活力四個維度14項指標,構建廣東經濟韌性的指標體系,綜合評價了2015—2020年廣東經濟韌性演化情況,分析各分項指標的演化特征,并提出增強廣東經濟韌性的建議。
關鍵詞:廣東;經濟韌性;重大風險;實施路徑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2.01.003
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及2020年初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對世界經濟產生了較大影響,對全球產業鏈及供應鏈產生了較大沖擊。為了加強對經濟領域外部風險沖擊的應對,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建設“韌性城市”,旨在提升城市風險防控能力①。2021年發布的國家“十四五規劃”,也提出了要“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防范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風險”。“韌性”作為近幾年城市與區域發展各領域新興的防范外部風險的相關理論,獲得了極大的關注,目前形成的研究成果及實踐經驗,為防范和化解風險提供了新思路。韌性理論包括生態韌性、經濟韌性和社會韌性,其中,經濟韌性研究經濟系統在受到內外沖擊時,能夠抵御沖擊并及時恢復的能力。廣東省作為中國經濟規模和外貿進出口規模第一的大省,外向型經濟非常活躍,在面對大國博弈可能的潛在沖擊和公共安全突發事件,韌性經濟理論研究及實踐成為廣東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向。
一、“韌性經濟”研究進展
(一)“韌性經濟”研究緣起
韌性經濟的研究緣起于“韌性城市”。近年來,學界對“韌性城市”的研究和實踐十分重視。“韌性”(Resilience)一詞來源于拉丁語中的“resilio”,19世紀50年代,機械和物理學領域將之表達為物體在受到外力沖擊產生變形后恢復到初始狀態的一種性質。韌性概念隨著不同學科間的發展而深化,由最初表示系統應對變化或干擾時保持自身基本狀態不變的能力,到系統吸收狀態變量、驅動變量和參數帶來的變化而依舊維持運轉的能力,[1]至今還包括了學習、適應、自組織能力等更廣泛的、不斷演進的內涵。[2]近年來城市韌性作為應對城市風險的一種理念受到廣泛關注,[3]相關討論應向著全過程、多因素、多維度(包含社會、經濟、空間環境、文化、管理、基礎設施建設等)的綜合治理轉變。[4-7]近年來相關研究集大成于適應性循環理論,該理論由Holling和Gunderson在2002年提出,[8]認為系統始終處在不斷變化的循環狀態,依次經歷開發、保存、釋放和重組等階段,系統具有潛能性、聯結性和韌性等三種屬性。潛能性是反映系統變化的空間和程度;聯結性是反映系統和外界變化之間的影響程度,聯結性越小,系統內部受外界變化的影響越大。
(二)區域經濟韌性
Simmie和Martin在適應性循環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區域經濟韌性理論,[9]區域經濟韌性的一般有兩種演化路徑;一是區域經濟會先后經歷開發、保存的循環階段,即發展、穩定經濟增長和穩定的路徑;二是區域經濟進入釋放、重組的循環階段,即經濟結構出現不斷地僵化、衰退、重組的路徑。Cross(1993)、[10]Gocke(2002)、[11]Hill(2012)[12]等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系統存在著多重平衡或穩定域,且一個經濟體可能由于沖擊或擾動從一個穩定態轉移到另一種平衡當中,受到同樣的沖擊,不同地區有不同的韌性表現。因此,經濟學領域將韌性描述為地區能從經濟沖擊中恢復到穩定狀態的能力。區域經濟韌性有四種演進路徑:一是遭受沖擊后恢復到原有路徑,保持原有增長速度;二是無法恢復到沖擊前穩定態,但保持原有增速、結構和功能,以低于原水平的穩定態繼續發展;三是無法回到原有增長路徑,結構和功能退化,持續衰退;四是在沖擊中把握契機,通過自身重組和創新,超越原有增長路徑并進入更高水平的穩定態。
經濟韌性的測度。國內也嘗試從不同角度構建指標體系,陳夢遠(2017)從技術關聯度和復雜度對經濟韌性進行定量測度。[13]朱金鶴等(2020)基于生態、經濟、社會、工程四個維度研究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城市韌性,[14]張俊威等(2019)對武漢經濟韌性水平測度,[15]馮苑等(2020)利用經濟產出變化與預期產出變化,比較中國11個城市群經濟韌性,[16]李金滟等(2020)從經濟、社會和社區三個層面建立包容指數來評價韌性水平。[17]Martin(2012)從抵抗能力、恢復能力、更新能力以及重新調整能力四個層面描述區域經濟應對經濟衰退或沖擊,[18]為國內研究提供了全面視角。綜合來看,現有測算方法實證分析包括空間特征、空間相關性分析,還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
經濟韌性的影響因素。胡樹光(2019)從區域異質性的角度證實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對韌性的提高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就業率水平以及GDP水平對于城市經濟韌性也存在明顯的促進作用。[19]不同地區存在創新水平上的差異,其產業相關多樣性對韌性水平具有顯著區間效應。[20]區域層面的制度能力、創新能力、基礎設施質量對經濟韌性的提高有正向作用,對外開放程度則相反。[21]由于區域經濟系統的復雜性,經濟韌性也存在多重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企業家精神、產業結構、就業水平、GDP水平、制度能力、技術水平、基礎設施、生命質量等,但國內目前的研究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定量亟待深入。
二、廣東經濟總體特征及可能受到沖擊的領域
(一)經濟總量邁入“十一萬億”,繼續保持全國首位
2020年,廣東生產總值110 760.94億元,增長2.3%。第一產業增加值4 769.99億元,增長3.8%;第二產業增加值43 450.17億元,增長1.8%;第三產業增加值62 540.78億元,增長2.5%。三次產業結構比重為4.3:39.2:56.5,新經濟增加值27 862.23億元,增長3.0%,占地區生產總值的25.2%。分區域看,珠三角地區占全省比重為80.8%,東翼、西翼、北部生態發展區分別占6.4%、7.0%、5.8%②。廣東GDP總量繼續保持全國首位(圖1)。
(二)區域分化明顯,廣深成為廣東兩大核心引擎
目前,廣東經濟形成了廣州和深圳兩大綜合實力強勁的核心城市。根據全國七普人口數據和城市級別劃分標準③,2020年,廣東超大城市有3個,廣州、深圳、東莞,特大城市則有佛山和惠州,其余均為大城市。另據由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編制的全球城市分級排名④,能夠位列Alpha級的城市則被稱為“世界一線城市”。2000年,廣東僅有廣州上榜,但位列Gamma-級,排在全球109位,深圳則沒有上榜。而在2020年的排名榜單中,廣東入列的城市為廣州和深圳,均為Alpha-級,排名為34和46名,這表明廣州和深圳已經從國內的一線城市晉升為世界一線城市。
(三)外向型經濟明顯,易受外部不穩定性因素影響
外貿進出口一直是廣東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之一。2020年,廣東外貿進出口7.08萬億元人民幣,占全國22%,規模繼續穩居全國第一,比2019年下降0.9%。出口規模創歷史新高,達4.35萬億元,同比增長0.2%,已連續4年增長。廣東作為中國對外貿易大省,對外貿易依存度相當高,易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自2018年中美貿易沖突以來,穩外貿一直是廣東的重要工作。
廣東近半貿易額發生在亞洲,但順差主要來源于北美洲。從廣東與各大洲的外貿依存度來看,以中美貿易爭端發生之前的2017年為例⑤,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GDP)最高為亞洲,達到48.64%;第二為北美洲,為10.33%;第三為歐洲,達到9.57%。以出口額計算的外貿依存度最高為亞洲,達到25.83%;其次為北美洲,達到8.71%;第三為歐洲,為7.31%。但如果從貿易順差來看,占比最高的是北美洲,達到了7.09%;第二位為歐洲,為5.06%;第三為亞洲,為3.02%;第四為拉丁美洲,為1.52%。從貿易順差計算的貿易依存度來看,最高為美國,為6.71%;其次為歐盟,為4.63%;第三為印度,為1.24%。作為中國第一外貿大省的廣東,盡管近半的外貿進出口總額發生在亞洲,但對外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仍是美國,同時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美國和歐盟等地。
受影響較大的集中于九大行業。如果以出口額占GDP比重大于1%作為主要判別指標,發現廣東有九大行業可能受到較大影響(見表1),主要為科技類產業及下屬行業。根據海關統計的二十二個進出口商品大類中的二十一個大類(本文不分析武器、彈藥及其零件、附件大類),按照上述三種貿易依存度的計算方法,從出口額占GDP比重來看,機械、電氣設備、電視機及音響設備行業達到24.88%的水平,占到以該指標計算的全省對外貿易依存度的一半以上,可見其是廣東出口領域的大頭;另外,從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及順差額占GDP比重來看,該行業也分別達到了41.49%和8.27%;此外,較為重要的儀器、醫療器械、鐘表及樂器類也達到了2.11%。
三、總體思路與指標體系
本文采用復合指標法,以城市經濟穩定性、經濟結構多元性、創新能力和系統活力4個維度共14項三級指標構建廣東城市經濟韌性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第一,經濟穩定性。城市經濟穩定性準則層共選取了人均GDP、城鎮登記失業率、城鎮化率、外貿依存度四項指標。GDP可反映經濟的總體情況,考慮到不同可比性,本文選取人均GDP,人均GDP水平越高則經濟基礎較好,屬于正向指標。城鎮化率越高代表城市化發展水平越高,屬于正向指標。失業率越高常常伴隨著諸多社會問題,不利于經濟的穩定發展,屬于負向指標。外貿依存度能夠反映經濟對外貿易的依賴程度,與經濟的穩定性密切相關,屬于負向指標。
第二,經濟結構多元性。經濟結構多元性準則層選取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比重和實際利用外資占GDP比重四項指標。第三產業反映經濟結構的合理程度,是正向指標。實際利用外資占GDP比重能夠反映外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程度,是正向指標。
第三,經濟創新能力。經濟創新能力準則層選取在校大學生數、科技和教育支出占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和專利授權量三項指標。在校大學生數是潛在的創新資源,反映城市創新能力,屬于正向指標。科教水平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水平越高,創新潛力越大,是正向指標。專利授權量能夠反映區域的科技創新水平,授權量越多,城市創新能力越強,是正向指標。
第四,經濟系統活力。經濟系統活力準則層選取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資產投資額、規上工業企業平均增加值和規上服務業企業平均增加值四項指標。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生活水平,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越高,該城市生活水平越高,城市吸引力越強,越容易吸引外來人口,為城市發展增加活力,屬于正向指標。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反映地區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水平,水平越高,城市越具有活力,屬于正向指標。規上工業企業平均增加值和規上服務業企業平均增加值指標從產業結構上,反映工業企業的數量和結構,表示的是經濟在一旦受到外界沖擊的背景下,生產能力的恢復能力,屬于正向指標(表2)。
數據主要來源于《廣東省統計年鑒》,統一采用2020年度的數據。通過對經濟韌性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采用專家打分的方式,構建指標之間的成對比較矩陣,綜合宏觀經濟、城市規劃、應急管理、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打分結果并取平均值,得出科學綜合的權重結果。最后采用加權求和模型對廣東經濟韌性指數進行處理,建立經濟韌性評估體系(表3)。
四、結果分析
通過對歷時性指標的比較,從年度的演變可以發現廣東總體上經濟韌性逐漸增強。四大分項指標演化情況并不一致,除了創新能力經歷了2017年的下降外,其他時間均處于增長趨勢,而且近兩年增長強勁。經濟活力分項指標表現較為平穩,波動性不大。經濟結構穩定性和經濟結構多元化分項指標表現并不理想,近兩年出現向下趨勢。因此,廣東2015—2020年經濟韌性的增強,得益于創新能力的增強,經濟活力總體表現平穩,但在外部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廣東經濟的穩定性和結構多元化受到一定挑戰,目標可能出現向下趨勢(表4)。
(一)總體情況
從廣東區域經濟韌性的總指標值來看,從2015年至2020年間,雖然2017年有所下降,但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表明廣東經濟的韌性總體有所增強(圖2)。從分項指標來看,經濟創新能力2017年之后強勁增長,其他三個指標表現平平,甚至在2019—2020年,經濟穩定性、經濟結構多元性、經濟系統活力均較平緩,受到疫情的影響,近年來有向下趨勢。
(二)分指標情況
1.經濟穩定性
經濟穩定性包括四大指標,分別是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城鎮登記失業率、城鎮化率和外貿依存度(圖3)。其中,人均GDP處于逐漸上升的趨勢,但相比之下,2020年增長趨勢趨于平緩。城鎮化率處于逐年提升的趨勢,城鎮等級失業率波動較大,2019年達到了最高之后,2020年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外貿依存度從2016年激烈下降后,雖然有所提升,但基本穩定,在2020年依存度已經小于20%。表明,廣東經濟的穩定性主要得益于工業化帶來的人均GDP的增長和城鎮化進一步深化發展所帶來的動力。
2.經濟結構多元性
經濟結構多元性包括第三產業貢獻度、實際利用外資/GDP比重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GDP比重三個指標(圖4)。三大指標均表現出激烈波動的過程,其中,第三產業貢獻度經歷了2015—2018年的快速增長后,2019和2020年趨于平緩并逐漸穩定在1左右。而實際利用外資占GDP的比重逐漸下降至2019年后,2020年雖有所提升,但幅度不大,這表明,廣東作為引進外資第一大省,外資對廣東經濟的貢獻逐漸下降,廣東已經走出了對外資的依賴階段,經濟的增長更多依賴于本地要素的驅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GDP的比重2015—2019年緩慢上升,但2020年出現激烈下降,主要的原因在于疫情的影響。總體上,廣東經濟結構的多樣化有所下降的主要在于一方面本地消費不足,第二方面,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對居民消費造成了極大的阻礙,需求的不足導致了經濟結構多樣化水平的下降。
3.經濟創新能力
創新能力是保障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之一,從廣東經濟創新能力的三大指標R&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專利授權量、在校大學生人數三大指標來看(圖5),R&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除了2020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保持較快增長勢頭,2020年該項指標所有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公共衛生應急系統的投入較大,可能抑制了R&D經費的投入。專利授權量除了2017年,其他年份均處于逐漸上升的趨勢。在校大學生數量近年來一直處于上升趨勢,且2019—2020年增長勢頭更為強勁。因此,廣東經濟創新能力逐年增強,正是創新能力的增強,有力對沖了外部環境的部分不利影響。
4.經濟系統活力
經濟系統活力體現在地區居民購買能力、對公共投資的負擔能力、工商業企業的生產能力等方面,具體而言,體現為四大指標,分別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固定資產投資額、規上工業企業平均增加值、規上服務業企業平均增加值。
從2015—2020年四項指標表現來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固定資產投資額基本處于同步增長的趨勢,從工業和服務業企業數量和增加值關系來看,廣東平均每個工業企業的增加值處于逐年下降的趨勢,表明工業增加值增長的速度遠低于企業增長的速度,或工業企業產能規模有總體縮小的趨勢。服務業企業平均增加值經歷了2015—2018年的增長后,2018—2020年處于下降趨勢,其中2019—2020年雖有稍微下降,但幅度較小。工業企業平均增加值和服務業企業增加值相比,則規模更小,且下降趨勢更加明顯,可能的原因是廣東的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果,服務業成為經濟的第一主導動力(圖6)。
五、廣東增強韌性經濟的主要路徑
(一)重點關注外貿領域的風險
一是落實減稅降費政策,減輕企業成本。對沖外部風險的政策首選是減稅降費,落實年度的《廣東省企業減負降本政策》。進一步降低社保費率,爭取向中央協調,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稅率的可能,提升企業盈利能力。針對部分無法完全避免使用美國進口產品和實施出口替代戰略的外貿企業,還需要協調相關部委調整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進一步研究制定加大對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清理規范涉企收費,下調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和工商業用電價格,適當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把減稅降費措施落實到位,為我省外貿企業營造更為良好的營商環境。
二是指導不同類別企業實施市場替代策略,減少單一市場的依賴度。指導可能受影響的企業及時調整出口銷售策略,推動出口市場的多元化發展,避免因市場過度扎堆某國而出現“雪崩”的情況。深入推動與不同國家的貿易往來,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興市場國家、東盟國家、拉美國家的經貿往來,以培育多元化出口市場。同時,鼓勵農產品加工企業、造紙企業、石油化工企業、鋼鐵制品企業,從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等國進口原材料和能源,逐漸降低對美國農產品、紙漿原料、油氣資源和鋼材的依賴度。
三是扶持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積極發展轉口貿易。針對機電和電子信息產業中的部分外商投資企業和本土大企業在美國設有生產基地,以及部分雖然出口美國占比較大但采用在第三國設立生產基地以供應美國市場的情況,引導龍頭企業、上市公司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在全球范圍整合資源,一方面通過當地生產滿足當地的市場需求,另一方面通過組建跨國公司,讓資本、技術、知識、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全球價值鏈的范圍內重新分工。同時,針對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如紡織服裝、箱包、鞋類、玩具、家具等,應積極發展轉口貿易,將附加值較低、不具備相對優勢的生產工序轉移到越南、印度、泰國等國家,再把該地區作為產品增值地和出口平臺,避免直接從廣東出口而遭遇高額關稅。
四是從速制定生活必需品市場供應價格波動應急調控預案。以糧油、肉菜等主要生活必需品市場供應和價格波動幅度作為市場應急調控的基本預警指標,分區間進行預警和市場調控,以將生活必需品價格波動幅度保持在正常區間。將物品同比變動幅度作為指標,按照價格漲幅小于5%、5%~10%、10%~20%、大于20%等作為區間,分別制定相對應的“正常”“二級響應”“一級響應”及“大規模異動”等四級響應機制。
(二)關注重點產業領域及產品
一是機電產業領域。廣東順差來源最大的產業為機械、電氣設備、電視機及音響設備等機電產業,順差規模大,占順差總額的45.76%;第二為雜項制品領域,規模占比達到了24.34%;第三為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為17.34%;第四為鞋帽傘杖、加工羽毛、人造花、人發制品,占比達到了6.99%;第五為賤金屬及其制品業,順差規模達占5.24%。上述排名前五產業的順差占比累計超過了99%。
二是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從對外貿易結構上看,廣東輸出產品主要是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而進口的更多是資源類產品。自2011年至今,從美國對中國進口行業占比平均值(NAICS三級分類)來看,電腦及電子產品的占比高達36.1%,電氣設備、電器和組件占比7.99%,其次是服裝配件(7.28%)、機械設備(5.91%)、鞋類與皮革制品(5.33%)、家具(4.06%)等,這些行業是廣東對美國貿易保護相對敏感的行業。
三是針對40個產品門類將受到實行一業一策扶持政策。在廣東對外貿易依存度大于1%的九大行業的46個商品類別中,以涉及中美貿易沖突的2000億元加征25%關稅目錄的有40個商品為例,僅有4個類別不在名單之列,可見涉及廣東對外出口的主打產品均在其中,這將大大增加廣東相關企業的成本,壓縮外向型企業的生存空間。從受影響最大的產品來看,主要為機械、電氣設備、電視機及音響設備等機電產品;雜項制品;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賤金屬及其制品;儀器、醫療器械、鐘表及樂器;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及石材制品、陶瓷產品、玻璃及其制品等。
(三)加強都市圈和鄉村振興建設,提升抗風險能力
1.強化都市圈內部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本地保障能力
要重點加強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和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建設,通過都市圈建設,調節核心城市和外圍城鎮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減輕外部依賴性。都市圈地區一方面要維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發展環境,優化產業布局,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提高經濟系統結構的多元性。另一方面,重點要提高在校大學生質量,擴大對外開放程度,吸引流動人口,提高經濟創新能力和系統活力,增強城市經濟韌性水平。提升都市圈核心城市的競爭力,增強核心區域對周邊城市經濟韌性低值區的輻射帶動作用。并加強區域之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健全區域之間路網和信息網等設施,保證經濟韌性高值區與經濟韌性低值區的流通和聯系,及時為經濟韌性低值區提供資金、技術、優質信息和管理經驗等,進而抓住發展機遇。
2.通過鄉村振興擴大腹地經濟水平
粵東、粵西北地區經濟韌性低,要努力抓住國家“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等戰略先機,積極開發本區域的優勢條件,努力爭取財政支持。借助“雙核+雙副中心”區域動力系統,強化區域中心城市對周邊的輻射帶動作用,積極承接廣深等核心城市產業轉移,積極吸引產業轉出地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因地制宜地發展代表本土特色的經濟產業和特色品牌。提高本地經濟的結構多元性和創新能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積極吸引人才及外來人口,提高經濟活力,促進城市經濟韌性的提升。
注釋:
①2020年11月3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②數據來自《2020年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③根據2014年中國城市的分類指標,分別將城區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的城市稱為超大城市,500至1000萬之間的城市稱之為特大城市,100至500萬之間的城市稱之為大城市,50至100萬為中等城市,50萬以下為小城市。
④作為全球最著名的城市評級機構之一,GaWC在其自2000年起發布的《世界城市名冊》中將全球361個城市分為四個大的等級,即Alpha(世界一線城市,分為Alpha、Alpha+、Alpha++、Alpha-)、Beta(世界二線城市,Beta+、Beta、Beta-)、Gamma(世界三線城市,Gamma+、Gamma、Gamma-)、Sufficiency(自給型城市,也可理解為世界四線城市)。
⑤2018年發生的中美貿易摩擦,是我國經濟面臨外部風險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2017年前后數據對比,對經濟韌性所受到的沖擊具有較大的說服力。
參考文獻:
[1]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4): 1-23.
[2]歐陽虹彬,葉強.彈性城市理論演化述評:概念、脈絡與趨勢[J].城市規劃,2016,40(3): 34-42.
[3]翟國方,鄒亮,馬東輝,等.城市如何韌性[J].城市規劃, 2018, 42(2): 42-46+77.
[4]Colten C E, Kates R W, Laska S B. Three years after Katrina: lessons for community resilience[J].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8, 50(5): 36-47.
[5]Renschler C S, Frazier A E, Arendt L A, et al. A framework for defining and measuring resilience at the community scale: the PEOPLES Resilience Framework[R]. Buffalo: MCEER, 2010.
[6]Cimellaro G P, Renschler C, Reinhorn A M, et al. PEOPLES: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resilience[J].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2016, 142(10):04016063.
[7]Burton I, Kates R W, White G F. The environment as hazard: second edition[M].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3.
[8]Holling C S, Gunderson L H.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ycles[M]//Gunderson L H,Holling C S,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2;34.
[9]Simmie J,Martin R.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 Towards an evolutionray approach [J].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 3(1):33.
[10]Cross,R.On the foundations of hysteresis in economic systems[J].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1993,9:53-74.
[11]Gocke, M. Various concepts of hysteresis applied in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2,16: 167-188.
[12]Hill. Economic shocks and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J]. Urban and Regional Policy and Its Effects, 2012(4): 23-35.
[13]陳夢遠.國際城市經濟韌性研究進展——基于演化論的理論分析框架介紹[J].地理科學進展,2017,36(11):1435-1444.
[14]朱金鶴,孫紅雪.中國三大城市群城市韌性時空演進與影響因素研究[J].軟科學,2020,34(2):72-79.
[15]張俊威,姜霞.武漢市經濟韌性水平測度及提升對策研究[J].價值工程,2019,38(28):146-150.
[16]戰艷.聚焦高質量發展解讀中國經濟韌性[J].對外傳播,2019(09):60-61.
[17]李金滟,張嘯.廣東經濟韌性水平測度與提升路徑[J].中國經貿導刊(中),2020(3):76-77.
[18]Martin R.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 2012,12(1):1-32.
[19]胡樹光.城市經濟韌性:支持產業結構多樣性的新思想[J].區域經濟評論,2019(1):143-149.
[20]郭將,許澤慶.產業相關多樣性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地區創新水平的門檻效應[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9,36(13):39-47.
[21]曾冰.城市經濟韌性內涵辨析與指標體系構建[J].區域金融研究,2020(7):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