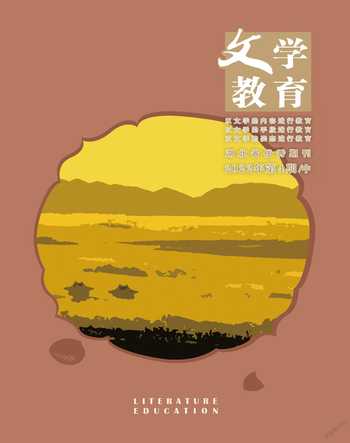論兒童哲學課堂中的情感缺席
鄺曉月
內容摘要:兒童哲學應用的關鍵,不在于群體探究中探討內容的性質,而是教師與兒童、兒童與兒童的互動方式。教師是否具備情感人文色彩和踐行人文主義關懷?兒童是否做到內在情感的聯結與外在行為的參與?但目前,兒童哲學教室中已然出現情感的缺席,成為阻礙兒童思維發展與情感表達、理性培養與人文關懷雙路徑實現的現實障礙。為解決當前的現實困境,從情感在場維度深入,加強情感參與:構建師生對話之間的情感回應關系;落實情感喚醒:以對話作為激活思維的外顯手段,深化情感體驗:搭建情感萌發的外界空間物質世界,使情感對話參與探究過程,實現兒童思維與情感的雙向發展,成為解決當前現實困境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兒童哲學 群體探究 情感對話 情感參與
“無論是教育還是人的發展,都逐漸要求并呼喚一種內質性的生長。”[1]在兒童哲學領域強調教兒童哲學性的思考,以哲學對話的方式促進兒童思維的發展。語言、對話作為思維的外顯表現形式,以情感對話的方式參與在群體探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發揮著重要的價值。美國著名兒童哲學研究者安妮·夏普(Ann Sharp)提到倫理敏感度、同情心、傾聽能力、對他者的注意力、團結精神在哲學對話中尤為重要。[2]但當前的現狀是:情感參與的喪失、情感對話的功利、情感體驗的缺失,用情感對話的方式參與群體探究的過程依舊處在應為、難為、與可為的尷尬境地。因此,本研究從應為之由、難為之境、可為之路三個維度對當前的困境進行突破。日常交往中,教師扮演的不僅是榜樣、引導者和參與者等角色,更要成為兒童情感萌發的喚醒者,以“愛”作為情感參與底色,以情感的參與喚醒情感的萌發,對兒童進行情感關懷教育,促進兒童思維與情感的雙向發展。
一.教室中的危機:情感的缺失
20世紀60年代,自李普曼(Lipman M)創立兒童哲學(Philosophy for Children,簡稱P4C)以來,經過近五十年的發展,逐漸在全球六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本土化實驗和推廣。但我國對兒童哲學的關注較晚,發展依舊處在起步階段。群體探究(communal inquiring)的概念最早由皮爾士(Peirce,C. S.)提出,后由李普曼引入兒童哲學。群體探究亦稱探究群體、探究團體、團體探究和探究共同體等,強調以群體的方式進行探究和展開活動,是兒童哲學實施與展開的主要途徑,兒童哲學的重要教學法。李普曼認為兒童具有強大的思維潛力,教育系統應該能夠有效地培養他們天生的好奇心、反思性思考的能力。[3]群體探究的實施與開展不是以教師為主導,兒童被動接受、灌輸的過程,而是強調兒童在教師的協助下,在民主的環境中,通過成員之間相互尊重彼此的觀點和立場的前提下,互助合作、溝通交流,積極解決當前問題,并且使兒童的思維得到啟迪與發展的過程。群體探究的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使兒童進行“哲學思考”,實現兒童思維的發展。李普曼也強調過“我們的教育如果不能教會孩子思考,那么這種教育從根本上來說是失敗的”。[4]
兒童的思維可以借助于對話或語言以外顯的方式得到展現,但目前,群體探究中對話缺少面部表情、眼神交流、音調起伏、重音強調和手勢配合等身體的參與和情感的滲透。傳統對話具有靜態性、標準化、嚴謹性和預設性的特點,教師按照預設的各種可能發生的場景進行,將兒童視為統一性、標準化與規范化的對象,嚴重忽視兒童個體差異性,背離了兒童發展的發向。而情感參與更強調對話的動態性、發展性、隨機性和生成性的特質。教師根據場景中實際發生的狀況,針對性、靈活性解決群體探究中隨時發生的意外和出現的問題。但當前群體探究的過程中已然存在情感維度的缺失,具體的表現為群體探究中情感主體意識薄弱、情感化功能的弱化和情感價值取向偏離。
1.探究群體中情感主體意識薄弱
正如盧梭所言:“如果想用我們的看法、想法和情感去代替他們的……那簡直是最愚蠢的事情。”[5]兒童作為獨立的個體,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和整全性,具備參與探究的權利與能力。探究群體為兒童進行哲學性思考提供了機會、路徑和選擇,參與的成員有教師和兒童,但在平衡教師與兒童的關系權重時出現失衡。兒童情感主體意識存在離場的現象,教師的適當引導變成過度的控制與壓制,兒童作為情感主體的意識受到干擾。“混合式學習模式下,學習者的主體意識主要體現在自我意識、實踐意識和關系意識三個方面。”[6]兒童參與群體探究的過程中,作為鮮活且獨立個體,情感主體意識受到削弱,主動參與探究的意識、行為以及承擔的責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教師作為探究過程中的成人,以身體、力量與權利的絕對優勢,擠壓兒童在探究場域內的范圍,往往主導性意識強烈,忽視兒童的主體地位。
兒童作為參與的主體,發揮個體的主體性價值,增強兒童的參與感和積極性,實現個體的主動參與。探究依靠教師情感的參與,激發兒童情感的萌發,建立起教師與兒童、兒童與兒童、兒童與社會、兒童與自然之間情感聯結,喚醒參與主體的意識,使兒童與教師的情感主體意識回歸到教育場域內,實現“兒童在場”。但“兒童在場”并非是“教師離場”,良好的教育場域應該是兒童的教育場就是教師的教育場。[7]要正確處理好師生在探究過程中的地位、角色和關系,明確教師參與的邊界與責任。
2.群體探究中情感化功能的弱化
李普曼在《教育中思考》(Thinking in Education)中提到關懷性思考(caring thinking),是通過哲學思考的故事、小說等達到教育的培養目標,實現兒童思維的發展。關懷性思考要兼容理性與情感,更加關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探究過程中更強調人性化、人文性和情感性。根據布魯姆教學目標分類學,教學目標分為三個層次,但在工具理性主義指導下,社會對實踐應用人才的迫切需要,情感層面的目標成為虛設。幼兒園開始片面追求知識、技能的迅速發展,功利和工具主義傾向嚴重。教育面對應試、升學和擇校的壓力,內卷現象嚴重,兒童知識、技能的掌握成為當前考察教育質量的指標,情感體驗成為應試教育下可以被犧牲的對象。國家的教育目的、地方的培養目標和教師的教學目標都被窄化為知識的機械掌握和課程分數的高低,忽視情感維度的有效參與和培養,即使有意識增加情感的參與,也僅僅是停留在外在形式主義的追求,而非實現外在目的與內在情感的全面契合。
情感培養具有內潛性、長效性的特點,情感發展伴隨在兒童的整個生命歷程中。但知識和技能的學習削減了兒童的情感的體驗,壓縮了兒童情感參與的時間。人是認知與情感相互交融發展的完整的生命體,[8]是感性與理性兼具的復雜的矛盾統一體。“我們盼望一個完整的教育,而不是德智體美勞分離的教育。我們希望回歸整體教育思想,整體的培養人的思想。”[9]理想的教育培養的人不是理性高度發展的片面的人,而是理性與情感雙重發展的整全的人,兒童可以在每個不同發展階段中實現自身功能的最大化發展,生命逐漸趨向完整而健全。[10]兒童哲學強調思維、認知和理性的發展,但情感的參與才能塑造起整全人的發展。
3.群體探究中情感價值取向偏離
情緒具有暫時性、易變性的特點,而情感具有長期性、穩定性的特質。“情感對于人的發展而言是一種基膜性的質料,它與生俱來,不斷發展成為支持德、智、體、美諸方面素質發展的基礎性、內質性材料。”[11]情感的參與為教育的發展、兒童的成長打下堅實的基礎,兒童情感發展為理性與智力的發展起著奠基性的作用和價值,在情感發展的基礎上構建起個體生命的生成性、動態性的發展。根據情感的分類,教師的道德感指的是要具備從事教育事業的熱情、信仰和責任意識,致力于生命和個體的整全性發展;理智感是指教師不僅要具備專業教育的知識與能力,更具備一定的教育機智,靈活處理教育過程中出現的突發問題;美感是指教師要具備一定的感受美、欣賞美和體驗美的能力和素養,引導兒童去感悟和體會生活、學習、社會和自然的美。但在應試教育大環境之下,對教師情感素養回歸的呼喚受到削減,情感參與價值遭到忽視。功利主義指導下,教師對情感參與的理解存在偏差,狹隘的認識情感參與的功能與作用,情感對話的價值理解過于片面化、世俗化和功利化,探究中情感價值取向出現偏離。
“教育的原則,是通過現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導向人的靈魂覺醒之本源和根基。”[12]教育起到的作用是喚醒靈魂中已有的知識與經驗,實現的是靈魂與靈魂的深刻交流。“哲學并不能給予,它只能喚醒——它能提醒并幫助人去獲取和保存”。[13]群體探究為兒童思維的發展提供途徑和手段,是橋梁和中介。兒童思維的發展,是兒童在教師幫助下,根據自己已有的經驗,探討生活和學習中的各種問題,通過群體之間的對話、交流和探討,彼此之間的觀點和思想相互碰撞,激活兒童思維,喚起兒童的思考與反思。哲學探究的過程是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過程,要超越工具主義的精神文化,豐盈兒童的個性和靈魂,在思維發展的同時,實現知情意行的統一,最終回歸教育的本源和目的,實現人類的自由解放。
二.情感參與群體探究的現實困境
1.思維發展與情感表達的雙向實現
知識的掌握與學習,激活思維的發展,探究群體是發展兒童思維的具體的手段和方法,但思維與情感的發展不是矛盾沖突的,而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探究過程中要實現的并非其中一方面的單向的發展,而是雙向的促進。如果大腦思維的發展制約情感的發展,生命便會失去本質價值,情感得到自由發展的同時,心智也會快速成熟。[14]在用情感對話的過程中,寄希望于兒童思維與情感的雙向發展。但在實踐應用中,既要做到兒童思維發展,又要做到兒童情感表達的實現,對兒童的接受能力與教師的教學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實踐推進中兒童的情感接受能力、情感的及時反應與回饋、語言表達能力、思維與邏輯能力、教師的邊界意識、教育機智、民主環境的創建等受到嚴峻考驗,能否做好“兒童在場”與“教師不離場”,平衡好之間的復雜關系成為實現思維與情感雙向發展的關鍵突破。
2.理性培養與人文關懷的全面達成
“完成從而認識理性是什么,從來是并且永遠是真正的哲學任務。”[15]但對理性的深刻認識不僅僅是哲學的任務,更是教育的永恒的價值追求。古希臘亞里士多得的“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將批判精神發揮到極致,面對矛盾與沖突時,在理性主義指導下,兒童哲學立足于對真理的不懈追求,能夠反思、質疑、批判教師、權威和真理。兒童理性的培養與發展更是關乎教育的進步、技術的革新和社會的發展,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理性精神”是追求真理、實現價值的統一。[16]英國兒童哲學家羅伯特·費舍爾(Robert Fisher)提到探究群體能增強學生的自尊、智力自信和參與理性討論的能力。[17]人文關懷是現代教育的追求,教師與課堂的人文關懷精神主要體現在,尊重兒童,突顯生命的主體性與個性;尊重生命,實現生命的在場與回歸;教育的內容落實在實際生活當中,與兒童的實際日常生活相關聯。在探究中用情感對話介入,“生命是情感與理性的結合體,生命倚重情感,情感支撐生命”,[18]是建立在尊重、信任生命的基礎上,立足于民主、平等的環境中,充分彰顯人文關懷的核心理念。在探究過程中理性培養與人文關懷的全面實現,需要在哲學故事的選擇、課程開發與實施與教師的情感素養等多方面上進行合理的培育。
三.情感在場:情感參與群體探究的實踐策略
1.情感參與:構建師生對話之間的情感回應關系
情感參與群體探究要建立起教師與兒童的融洽關系,良好關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各抒己見,求同存異。首先,教師要尊重差異,建立好兒童的信任關系,進行合理且恰當的平等對話,探究的問題或者對象是波浪式前進或者螺旋式的上升,維度是多樣的,深度是適宜的,彼此相互關聯、層層推進。其次,教師要加強自身的責任意識,了解不同年齡階段兒童的“最近發展區”,將探討的問題控制在“最近發展區”內。教師在一定程度上要選擇放手,將討論的權利歸還給兒童,尊重且信任兒童的能力。再次,兒童作為鮮活的生命個體,其身體和靈魂都是自由的。兒童的身體不是承載知識的“容器”,兒童的靈魂更不是誰的附屬品。教師要明確邊界觀念,探究過程是在教師引導下進行,但引導不是聽取,更不是控制。兒童處在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教師的合理引導不能越界,相互尊重彼此的觀點,包容兒童出現的錯誤,給與兒童及時的支持與回應。最后,教師對兒童的回應要建立在情感關懷的基礎之上,對兒童的發言、觀點給與及時的反饋與回應,使兒童的情感得到寄托,立場得到支持。兒童得到回應后也能給予教師反饋,使得情感回應的流程形成良好的閉環。只有建立情感上的雙向通道,才能真正喚起雙方的情感共鳴,建立起兒童與教師的情感回應關系。
2.情感喚醒:以對話作為激活思維的外顯手段
“任何事物處于最好狀態之下,是最不容易被別的東西所改變的。”[19]未知會吸引兒童的關注,引發兒童的求知欲,激發兒童的冒險精神。教師要引發、喚醒兒童自身的探究欲望,激發兒童對問題的無限好奇,減少外界環境中存在的干擾,使兒童沉浸在探究的熱情中,用情感對話喚醒兒童思維的發展,搭建兒童豐富的情感世界。對話是兒童與兒童、教師進行溝通、交流和交往的途徑和方法,雙方的對話是建立在彼此平等的基礎之上,實現的是觀點的交互、心靈的溝通和靈魂的碰撞。諾丁斯的關懷理論注重對話和交流,通過對話和交流喚醒思維的活力和觀念的碰撞。兒童與兒童的交往對話,針對一個對象、話題或者故事,通過同伴合作的方式,在問題討論的中,激發兒童對未知的好奇,喚醒兒童運用已有知識解決現有問題的意識,推動問題進行深入的理解,鍛煉兒童的批判能力和輯推理能力。兒童與教師間的互動對話,本著民主的原則,從尊重生命出發,通過語言的交流喚醒兒童的主體性、自主性和自覺性,讓兒童可以獨立參與到探究的過程中,具備獨立判斷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兒童創造性思維和批判性思維。
3.情感體驗:搭建情感萌發的外界空間物質世界
情感參與群體探究不僅需要參與主體的主觀努力,更加需要外界物質環境的搭建。幼兒園或學校的建筑、班級環境、桌椅擺放等,作為兒童外在接觸的物質世界和建筑空間,都與兒童情感的發展密切相關,是引發兒童情感體驗的重要維度。[20]但現代學校的建筑和空間設計缺乏對兒童情感的關注,相較于西方的實用主義傳統,中國學校的建筑標準深刻體現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標準化的模式。[21]中國傳統幼兒園的圍墻,將兒童的學習環境與外界的社會環境進行嚴格的劃分,具有明顯的封閉化和區域化的特點。幼兒園或學校圍墻一方面將兒童作為未成熟的對象保護在限定的區域內,但另一方面也將幼兒園與“外面的世界”相隔離。冰冷的圍墻通過訓育的方式不僅隔絕了兒童與社會的聯系,也阻斷了兒童情感互動和交流的途徑。情感-空間的建立可以適當減少幼兒園圍墻的構建,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適當保留幼兒園與外界空間的互動空間,增加柵欄、花草等“軟”圍墻的設立,為幼兒園增添活力和生命。現代幼兒園和學校班級課桌的擺放大都是工業革命影響下的秧田式,教師在課堂中教師居高臨下,起著絕對的主導作用。教師對兒童以俯視的視角與兒童進行溝通與交流,兒童對教師是以仰視的方式回應,師生間存在嚴重的不平等性。適當改變傳統課桌的擺放方式,可采用會議圓桌式,或者在課堂中不設桌椅,或者去到大自然中,將探討的內容與自然相融合,與自然相聯系,成員之間席地而坐展開交流和討論,增加師生、生生之間的眼神交流、肢體的互動,加強情感的對話與互動。
兒童哲學原是以美國為中心,后逐漸推廣至國際的一種學術,[22]通過不斷地推理,強調以對話的方式,促進兒童思維的發展。國外在兒童哲學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中已卓有成效,但中國本土化推廣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物質至上和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造就的是片面發展的人,在關注理性發展的同時,忽視情感的參與。然而,教育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是有溫度的、有情感的,而不是冰冷的。教育培養的人也不是學習知識的機器、整齊劃一的模具,而是溫暖且鮮活的個體。探究群體作為兒童哲學實踐應用的重要途徑,情感這一重要角色的缺失,制約著兒童培養的完整性。用情感對話參與探究群體,用情感滋養兒童的生命、塑造兒童完整人格、豐盈兒童的心靈,在踐行人文主義關懷中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1]王平,朱小蔓.建設情感文明:當代學校教育的必然擔當[J].教育研究,2015,(12):12-19.
[2]Sharp M, Ann. The Face of the Other [J].Thinking,2006,18(2):43-47.
[3]Raymond S. Nickerson. Reviewed Work:Thinking in Education by Matthew Lipma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993,(4):620-633.
[4]Lipman M.Thinking in educa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0.
[5][法]讓雅克·盧梭.愛彌兒[M].李平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91.
[6]衷克定,岳超群.混合學習模式下學習者主體意識發展研究[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17(06):48-56.
[7]付有能,陳燕浩.由“兒童立場”走向“兒童在場”——教育立場的反思與追問[J].中國教育科學(中英文),2020,3(06):31-38.
[8]王平.價值觀育人的情感教育闡論[J].教育研究,2020,41(10):33-44.
[9]朱小蔓.情感德育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1、101.
[10]劉鐵芳.走向整全的人:個體成長與教育的內在秩序[J].教育研究,2017,38(05):33-42.
[11]朱小蔓.情感教育論綱(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6.
[12][德]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3.
[13][德]雅斯貝爾斯.智慧之路[M].柯錦華,范進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7.
[14]A.S.Neil.Summerhil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M],New York: Hart Publishing Company,1960.
[15][德]雅斯貝斯.生存哲學[M].王玖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1994:51-52.
[16]吳永軍.理性精神:教育的永恒追求[J].教育發展研究,2020,40(02):1-8.
[17]Robert Fisher.Teaching Thinking-Philosophical Enquiry in the Classroom [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2016:54;171- 172;169;173.
[18]張學茹,李永生.生命在場:德育人文關懷的起點[J].中學政治教學參考,2017,{4}(15):40-41.
[19]柏拉圖.理想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08、77.
[20]Hamlett,J. Spac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ish Public School Dormitories[C]//Olsen, S.Childhood, Youth and Emotion in Modern History, National, Coloni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2015.
[21]王瑩.兒童“失樂園”——標準化學校建筑對童年的放逐及尋回[J].教育科學研究,2018(04):31-35.
[22]詹棟梁.兒童哲學[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7.
(作者單位:江蘇大學教師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