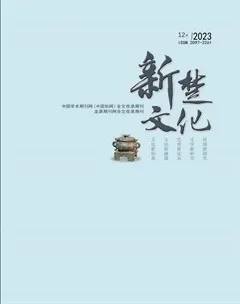莊子哲學視閾下的兒童哲學本土化
郭文娟 魏鳳云
【摘要】為探尋兒童哲學的中國化、本土化之路,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儒學經典出發來挖掘、整理中國古典中的兒童哲學思想,但對莊子及其哲學的關注還不夠,莊子哲學的終極追求與兒童哲學終極根源的契合性,恰好證明了莊子哲學與兒童哲學之間對話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基于此,莊子哲學的本體論與兒童哲學產生了理論共鳴,為其本土化建構提供了中國哲學理論支撐;其次,兒童哲學的實踐淵源與莊子哲學的實踐論相契合;如此,莊子哲學便以其別具一格的視角打開了兒童哲學本土化的“破曉”之門。
【關鍵詞】莊子哲學;兒童哲學;《莊子》;本土化
【中圖分類號】B223.5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35-0016-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3.35.005
【基金項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項目編號:JJKH20230875SK)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毋庸置疑,兒童哲學只有與中國相融的部分結合,才能使廣大民眾更好地接受。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試圖從儒學中探索兒童哲學本土化之路,莊子哲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之一,國內對其與兒童哲學本土化的探究甚少。兒童對諸多問題的思考恰恰來自對生命的直觀感受與本真感悟,這樣的思維方式與莊子推崇的思維方式一致。
二、莊子哲學與兒童哲學的契合:
何以可能?
(一)莊子哲學的終極追求
司馬遷曾以“游戲”一詞作為莊子的精神寫照,以此來點明莊子的“游戲”一生。可以說,這里的“游戲”,是一種“自快”的方式,也是一種生存狀態。誠然,司馬遷深刻理解莊子的精神,參悟莊子哲學,因此他說莊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莊子作為“真人”,他確實是“適己”的,他更是看重自身的意志,做一個純粹的人是他對自我生命的期盼,也是對個體整全生命本身的復歸。
莊子“適己”“不能器”,卻并非是不問世事之人。正如在《莊子》內篇《人間世》中,開篇即闡述來人際關系的艱難。莊子在這段師生趣味對話中道出:“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兇器,非所以盡行。”[1]此處,莊子筆下的孔子是謹慎懂自保的師者,顏回依舊是心懷政治抱負的熱血青年,在莊子看來,顏回這敢于在暴君前游說的滿腔熱情無疑會讓他難以保全性命。除了孔子和顏回的趣味對話外,莊子還描述了葉公子高(楚國的大夫)的困境,以此說明,即使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政治家,面對現實也可能無所用處。但也是這樣,卻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之后的支離疏和楚狂接輿也是莊子所描繪出的人物,正所謂“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只用”,這是莊子一生所求,也是莊子哲學的終極追求,即探索個體生命在這人世間的出路。
(二)兒童哲學的終極根源
雅思貝爾斯的精神遺產之生存哲學從一個新的視角為我國的兒童哲學研究打開了嶄新的一扇窗。譬如,雅思貝爾斯在其著作中所言:“哲理思考的原動力來自于根源。”[2]兒童哲學在新時代中,其價值在于:我們每個人在面對無法逃避的、威脅到人之生命本身的“終極境況”時,兒童哲學能夠從根源上幫助我們的兒童更好地理解人類生存的危機,面對死亡、面對生命攸關的終極境況能夠擁有正確的意識。
今天,兒童哲學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時,也開始趨向于工具主義。隨后,國內相關學者對這種工具主義進行了反思[3],以呼吁學界超越工具價值,尋求兒童哲學的根源。兒童哲學之父李普曼也曾認為應從小、從根源抓起。“幫助兒童自發地、批判地、合理地思考,從而將他們從確定性中解放出來。”[4]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莊子察看到兒童生命中要面臨的困境,于是生成了尊重個體、尊重兒童本身的理論。因此,莊子哲學的終極追求便與兒童哲學所面對的終極根源不謀而合。也就是說,莊子哲學關切的問題正是兒童成長中遇到的現實問題,也是終極問題,這種完滿的契合證明了莊子哲學與兒童哲學之間存在可能和必要的聯系。
三、莊子哲學之本體論:
與兒童哲學的理論共鳴
(一)泰初有無是兒童哲學的初始共鳴
《莊子》全文以“卮言曼衍、行文逶迤”[5]的言說方式獨具特征。開篇便由鯤鵬引出“小大之辯”,再由“小大之辯”引出“圣人無名,神人無功,至人無己”[6]。全篇對無名和無功進行論證,之后回到小大之辯論,又用辯說大的用處結尾。“鯤鵬”隱喻著莊子哲學的基礎,也就是說莊子的視野寬闊,是面向無垠的天空和宇宙的,他的思想遼闊,志在探索浩渺宇宙的奧秘。兒童作為天地間最初的“渾沌”體,并不是誰的產物,自出生之日起,兒童就是獨立的個體,是身心、內外、知行的“合一”體,是生命的泰初,是生命最原本的樣子,也是最初的本體。兒童哲學不僅是幫助兒童進行哲學思考,更多的是引導兒童對宇宙、世界以及自身的好奇和探索,以致達到自己未曾知曉的體悟和驗證。基于此,莊子以“鯤鵬之大”預見宇宙初始之端正是與兒童哲學產生了一種不容忽視的“情愫”。
(二)自然之道是兒童哲學的生命顯現
《莊子》通篇貫穿“道”,它所強調的“道”是自然之道,是“鵬負青天,而后圖南”的“扶搖九萬里”,是“斥鷃奚笑,而后騰躍”的“蓬蒿數仞下”,是一切的可能性,也是自然界的混一生命境界。馬修斯曾在其著作中說:“許多幼童會自然地提問題,做評論,甚至從事哲學專家承認的哲學推理。他們不僅自然地做哲學,而且是以清新的觀點、敏銳的問題意識以及概念匹配等來做哲學的。成人必須培養做好哲學所要的天真,而對兒童來說,這樣的天真完全是天然的。”[7]馬修斯所言的兒童哲學便是兒童自發地提出傳統中的哲學之問,并能以最初的本然之道來進行哲學之思,這是兒童生命本身的樣子,也是兒童哲學的價值顯現。從這些視域出發,莊子哲學的自然之道其實都是與兒童之性、與兒童哲學之道、與人之道都有著極大的契合境界。
(三)逍遙之境是兒童哲學的自我生成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顯然,這種超越時空、超越物我的“無所侍”的絕對自由的生活,千百年來只能存在于人們的夢境中。因此,他用魚與鯤、鳥與鵬、彭祖與大椿、魚蝦與大鯤、鳥雀與大鵬這些看似無用之對比,用萬事萬物的“相對”來順其自然地生成“無己、無功、無名”。誠然,我們前文提到過,在莊子哲學視域下,充分尊重每個兒童,尊重兒童在場域中的展開與生成。從兒童哲學的具體實踐來說,本應是共在、共生以及共融的,在這種場域里,應該給予兒童自我生成需要的足夠空間和環境,用合適的“逍遙”精神與兒童虛壹共生,給兒童足夠的時間實現自我生成,在此基礎上喚醒藏于深處的童心。
四、莊子哲學的實踐論:
兒童哲學實踐的基石
(一)任情率性是兒童哲學實踐的返璞之路
莊子同老子一樣,亦主張返璞歸真,復歸于嬰兒。其在《人間世》中也提出:“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8]在莊子看來,一切事物的大小、是非都是相對的,人生的貴賤、榮辱也是無常的,因而要求人們不執著于人為得失而傷害自然本性。也就是一切要順應自然而返歸純真的本性。莊子所說的這種返歸純真的本性正是兒童哲學實踐所倡導的保護兒童的天性。從這個角度出發,莊子哲學所反對的以外在的標準限制人的天性和兒童哲學本身所倡導的返璞歸真之路完全契合。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莊子哲學的這種任情率性又何嘗不是兒童哲學進行本土化實踐的基石。
(二)省察思行是兒童哲學實踐的修行之路
“未經省察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像蘇格拉底一樣,莊子也提倡將人的生存價值建立在“思考—省察”的基礎之上。從思考到省察到行動,這是人們從認識到實踐的修行之路,同樣也是進行兒童哲學實踐的必經之路。在海神與河伯對話中,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而莊子則予以指導:堅守大道,順其自然。兒童哲學實踐活動中,兒童以其自然本真的樣子思考,之后通過教師的引導進行省察,最終呈現出自然而然的樣貌。
(三)道通為一是兒童哲學實踐的理想圖景
《秋水》圍繞道物之辯,衍生出“以道觀之”和“以物觀之”兩種哲學視角,誕生了齊物論和相對論兩種對立統一的重要思想——“以物觀之”,萬物不同,議論蜂起,形成相對論;“以道觀之”,道通為一,齊同物論,形成齊物論[9]。以莊子哲學的這種道心來會通兒童、童心[10],便能說明兒童哲學實踐活動背后的理想圖景與莊子哲學的道通為一是完美契合的。《秋水》全篇通過海神與河伯的對話,將認識論結合實踐論,使得道通為一,同兒童哲學的實踐圖景相契合,呼吁返璞歸真、解放心靈,以此才能激發兒童創造性的靈感和動力。
五、莊子哲學:
打開兒童哲學本土化的“破曉”
基于以上對莊子哲學與兒童哲學的文本分析,本節旨在從“渾沌之死、復歸本性、互通交融”三個方面進一步論證莊子哲學是能夠打開兒童哲學本土化的“破曉”之路。
(一)渾沌之死:還原兒童的真實空間
“渾沌”一詞最初出現在《內篇·應帝王》。莊子用疾速之意的“儵”“忽”二字比喻有為之帝,用純樸未曾開發之意的“渾沌”一詞喻無為之帝,有為之帝為了報恩,讓無為之帝與眾生一樣具有“視聽食息”的七竅,結果“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莊子從生死存亡的角度,表明了帝王從政應當以無用為用、無功為功、無為而治。“空間”作為實施兒童哲學的一個重要載體,在互聯網飛速發展的時代,空間的概念逐漸被淡化甚至被認為無用。正如杜威曾說:“經驗表明,當兒童有機會從事各種調動他們的自然沖動的身體活動時,上學便是一件樂事,兒童管理不再是一種負擔,而學習也比較輕松了。”這個時候這種“無用”的空間或許對兒童來說是“有用”的。因此,渾沌之死又何嘗不是一種警示,警示歸還兒童的真實空間。
(二)復歸自性:反對吞噬兒童的時間
“復歸自性”追溯至《逍遙游》篇:“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既是莊子哲學的體悟表征,也是兒童哲學反擠壓兒童時間的淵源。在功利主義的驅使下,兒童被利益和功利指標物化且異化,成人世界的功利擠壓和吞噬了兒童的時間。譬如兒童被迫緊張地穿梭在課后的各種補習班和興趣班中,父母們不愿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固然能夠理解,但大多數時候缺乏溝通與關懷的“為你好”卻在悄無聲息中束縛了兒童的雙腳,蒙蔽了本該屬于兒童本身的童年童趣。毋庸置疑,長此以往,這種病態的成人與兒童之間的關系會長出蟲洞的:兒童不愿甚至厭惡主動學習,成人為之愛莫能助,直至陷入死循環。而莊子哲學的復歸本性又何嘗不是解開兒童與成人二者之間那把無形枷鎖的秘鑰?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莊子哲學呼吁復歸兒童的本性,歸還兒童的時間。
(三)互通交融:感知兒童的生命在場
“任情率性”就是要從兒童本身出發,關注兒童的自然生成。兒童哲學實踐要保證兒童與成人的關系是平等的,是能使兒童的生命在場。除了莊子,海德格爾也認為,棲居就是要在空間中逗留或者持存,“人,詩意地棲居于大地”[11]。這種“詩意的棲居”就是一種回歸自然的樣態,是人類生存的應然,也是兒童哲學的必然。正如馮建軍教授所言:“兒童身心都應當在兒童哲學中尋得棲息地,因為人的存在絕不是生物意義上的生存,更有生命意義上價值發展與生成。”[12]為了使這種“返璞歸真的樣態”變為現實,讓兒童的生命始終在場,可以通過行感知和哲學對話消除成人與兒童的疏離感和邊界感,使二者的互通交融成為可能。
六、結語
莊子哲學是一種生命哲學,以“逍遙游”開篇,逍遙本質上在于將每一個生命個體的靈魂都歸還給個體本身,意味著“率性”,這與鄭玄注解和朱熹章句主張的“循其性之自然”是不謀而合的。或許這種“逍遙”才是兒童哲學研究前輩們一直在追尋的旨歸,就是這種可能路徑的方向。因此,本文便嘗試從莊子哲學本身出發,包括但不限于以《逍遙游》《秋水》為主線,試圖尋找莊子哲學在兒童哲學本土化的進程中,二者可能產生的“火花”。事實證明,莊子哲學的終極關懷和兒童哲學所追求的終極根源是契合的,莊子哲學體現出的生命之“真”,是返璞歸真,也是天地大道,但歸根結底,是赤子之心,是童心,或許童心與道心的交織會開辟出生生不息的兒童哲學本土化之道。
參考文獻:
[1]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2:141.
[2]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M].鄒進,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3]白倩,于偉.馬修斯兒童哲學的要旨與用境——對兒童哲學“工具主義”的反思[J].全球教育展望,2017,46(12):3-11.
[4]于雪棠.《逍遙游》的主旨與戰國公共話語——兼及文本問題[J].求是學刊,2019,46(05):128-138+181.
[5]冀昀.莊子[M].北京:線裝書局,2007:7.
[6]馬修斯.童年哲學[M].劉曉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210-211.
[7]郎擎霄.莊子哲學[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20.
[8]劉廣濤.外篇不外 道通為一——《秋水》篇哲學思想探析[J].理論學刊,2022(02):152-160.
[9]王安琪.《莊子》與兒童哲學的交互性連接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22.
[10]杜威.民本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07.
[11]馬丁·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M].孫周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194.
[12]馮建軍.走向道德的生命教育[J].教育研究,2014(06):33-40.
作者簡介:
郭文娟(1998-),女,漢族,陜西渭南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學原理。
魏鳳云(1981-),通訊作者,女,漢族,河北人,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學原理、教育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