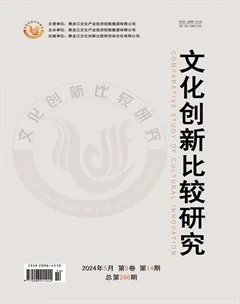出版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關系探析
曹騰
摘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幾千年中華文明的精神結晶,借助出版而不斷傳承發揚,出版需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優秀內容,以繁榮自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出版業的支持,出版業的進步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的養分,這些在中國古代經典的出版歷程中均有所體現。所以,該文厘清傳統文化與出版業的關系:傳統文化孕育催生出版, 出版業的興起促使傳統文化井噴式發展。在此基礎上,該文總結出近代傳統文化出版的啟示。傳播掌握其中的定律,對當代出版業的發展有著積極作用,并能為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古代典籍;傳承;文明;傳播
中圖分類號:G122?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文章編號:2096-4110(2024)05(b)-0108-05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O Teng
(The People' Daily Press, Beijing, 100733, China)
Abstrac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crystallization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is continuous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rough publishing. Publishing needs to draw excellent content from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prosper itself. Th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nutrients provided by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se can all be reflected in the publishing process of ancient classics. So,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tional culture nurtures and gives birth to publishing, and the rise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promotes the explo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publication of modern traditional culture. Mastering the laws of communic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ublishing; Ancient classics; Inheritance; Civilization; Dissemination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著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1]。當代出版是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基礎建構力量[2]。
本文所說的傳統文化,特指具有特點、世代相傳的精神財富,如哲學、文學、藝術、科學等。論及的出版業主要包括出版形式及出版發行的狹義文化產品,即人們在思想、文學、藝術等精神生產和交往活動中獲得的,并用語言、文字等載體表達的產品;重點闡述書籍的出版發行,時間界定在古代和近代。
傳統文化與出版的關系極為密切,毫不夸張地說,二者密不可分,互為命脈。縱觀中國數千年歷史,可以發現,傳統文化借出版發行不斷地傳承、發展、壯大,推動社會繁榮進步;出版業則因出版傳統文化的精神產品而繁榮自身。
1 傳統文化孕育催生出版
傳統文化的精神產品,伴隨人類創造物質財富而產生,但因最初沒有出版發行,人們只能將原始思想、文學與勞動經驗口傳心授,傳播有限,作用亦有限。為了人類自己的生存、繁衍、壯大,一代代能人想方設法傳播勞動心得,因而產生了原始出版模式。我們或可將原始巖畫看成最早的出版物,因為它刻畫的內容,顯然與放牧和狩獵有關,既是物產的提示,又是獲取的指引,目的是傳播自己掌握的知識,以便能夠幫助別人。
隨著人類勞作不斷豐富,產生的精神財富亦快速增長,逐漸有了哲學、文學、科學等方面的精神成果,單靠結繩記事、圖畫傳播已不足以將它們記錄下來、傳播出去,而為了更好地記錄、傳播它們,人們創造出了文字。
文字最早出現在獸骨、龜板上,曰甲骨文;后出現在青銅器上,曰金文;出現在石鼓上,曰石鼓文。從現存的這幾種刻品的內容判斷,古人之所以刻,是為了記載重要事件,并希望傳之子孫。我們或可視其為出版雛形。到木櫝、竹簡大量刻制,可以說,我國的原始出版已經形成。最早的木櫝、竹簡版本書尚待考證,而20世紀70年代在山東銀雀山漢墓中出土的竹簡版《孫子兵法》,7 200余字,規模宏大。同時同地出土的竹簡版《孫臏兵法》,萬余字,規模更大。兩部竹簡書是否為“二孫”本人刻,未知,但他倆的著作記錄在何處?那時沒有紙張,要么刻在竹簡上,要么寫在竹簡上,傳世的《竹書紀年》初版本,就是用戰國古文字漆書在竹簡上的。就是說,漆書竹簡最晚也出現在戰國時期。“二孫”有條件漆書。
漢代蔡倫改進造紙術,促使真正意義上的出版正式形成。最早出現的規模出版物,是石刻版本和木刻版本,先刻版,后印刷,再裝訂成冊,一版起碼能印數百冊。這雖然比竹簡、木櫝版本好很多,卻仍受局限,不能滿足人們需要。待到北宗慶歷年間,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從而帶來了出版業的春天。
2 出版業的興起促使傳統文化井噴式傳播
活字的出現,大大提高了刻字的利用率,一字多用,從而節省了刻版時間和精力,但它并未完全取代石刻版和木刻版。三種版本一起使用,使先秦、兩漢、隋唐的大批精神財富廣泛傳播成為可能。
由于社會需求日增,出版的內容擴展到精神財富的各個方面。現存的古籍告訴我們,古代出版的書籍內容,已經包括以下方面:文學、歷史、哲學、宗教、政治、法律、軍事、語言、地理、民族、醫學、科技、物產、動植物、娛樂等,所有精神產品幾乎無一遺漏。
隨著出版內容的擴大、數量的增加,為了便于人們查找、閱讀、使用,編纂人員特意將書籍分類。粗略統計,成類的至少有6種,即總集、別集、類書、叢書、辭書、百科全方。未能歸入這6類的其他精神產品,也都悉數出版。
2.1 總集
總集是將許多人的同種作品匯集而成的詩文集。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成書于春秋時代,共計300多篇,大致是周初到春秋中葉的民間作品,其不知名作者遍布陜、晉、豫、魯、鄂等。后來的若干詩集,皆源于此。詩歌總集多如牛毛,有名的便有宋代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輯錄漢魏到唐的樂府歌辭。我國現存最早的“騷體”總集是《楚辭》。“楚辭”一名,出自西漢初年,由稍后的西漢文學家劉向編輯成集,所輯文稿,以屈原作品為主,旁及宋玉等人之作。我國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名曰《文選》,世稱《昭明文選》,由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選,輯錄先秦至梁的詩、文、辭、賦700余篇,分為38類,保存了許多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后朝不斷有人對其增補、注解,出版新的詩文集,可見其地位之重要、影響之深遠。其他有名詩文總集婦孺皆知者,有《唐百家詩選》(北宋王安石選編)、《全唐詩》(清康熙彭定求等人編)、《唐詩三百首》(清乾隆蘅塘退士編)、《古文觀止》(清康熙吳楚材、吳調候編選)等。大致統計,從南朝到近代存世的詩文總集影響較大的至少百部以上。規模之大,令人驚訝。
2.2 別集
別集為收錄某一個人的作品而成的詩文集。凡有點規模的圖書館,舉目可見“別集”,只是近、現代再版的多,而宋、元、明、清版本,都當寶貝珍藏了。有名的別集數不勝數,但凡古代名人,只要有水平高的詩文作品,便被后人編成別集。人們熟悉的別集有:《孔北海集》(孔融)、《魏武帝集》(曹操)、《曹子建集》(曹植)、《諸葛亮集》、《陶淵明集》、《李太白集》(李白)、《杜工部集》(杜甫)、《白氏長慶集》(白居易)、《駱賓王文集》、《孟浩然集》、《昌黎先生集》(韓愈)、《歐陽文忠集》(歐陽修)、《臨川集》(王安石)……
總集和別集“兩大筐”所裝詩文, 均為作者原創,而不包括對詩文的評點、論述著作。但評論詩文的著作很多,也很重要,在各朝出版總量中占比不小。為了眉目清晰,便于參閱,文史研究者將其單列一類,名曰“詩文評”。詩文評中好書不少,順便一指便有:《詩品》(古代詩論,兩部。其一,南朝梁鐘嶸撰,名《詩品》;其二,唐朝司空圖作《二十四詩品》,簡稱《詩品》)、《文心雕龍》(南朝梁劉勰撰)、《詩話總龜》(北宋阮閱編)、《全唐詩話》(南宋尤袤撰)、《藝苑卮言》(明王世貞撰)、《隨園詩話》(清袁枚撰)、《人間詞話》(近代王國維撰)……這些著作對古詩文進行研究,補充其背景,評論其優劣,強調其特點,并闡明自己對詩文藝術的主張,對后人閱讀古詩文幫助甚大。
2.3 類書
類書為摘錄現存各種書籍上的材料,按照內容分門別類編排,以便人們檢索的書籍,動輒成千上萬卷,厚厚的數百冊。現存最早且規模很大的類書,是唐代的《藝文類聚》,而名氣極大且應用廣泛的類書,非《太平御覽》《永樂大典》《古代圖書集成》莫及。《藝文類聚》是唐初歐陽詢等人奉敕編撰而成。當時,唐高祖李淵因古今圖書日漸繁多,欲知事之源流頗難尋究,故命歐陽詢等編輯此書。7年乃成,100卷,引證唐以前1 400余種,而原件已損毀十之八九。后世類書多仿其體。《太平御覽》初名《太平總類》,北宋李昉等奉太宗之命編修,1 000卷,約470萬字。《永樂大典》初名《文獻大成》,解縉奉明成祖朱棣之命主持編纂。收有歷代重要典籍達7 000多種,約37 000萬字。分作20 000余卷,裝訂成10 000多冊。《古今國書集成》,清朝陳夢雷原編,蔣廷錫等人奉帝命校勘重編,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修成,輯為3 600余卷。雍正初再編,歷經四年而成,得10 000卷,16 000萬字。此書“采集廣博,資料宏富,分類詳致,條理清晰,撿一得百,通慣古今”[3]。
2.4 叢書
叢書是將許多種書按某一主題匯編成的套書,如《四庫全書》《知不足齋叢書》和《二十二子》。《四庫全書》為清乾隆皇帝命令編修,共3 503種,79 327卷,分藏于北京、沈陽等地。整理保存古籍之功甚巨,在古籍整理方法、校勘、輯佚及目錄學等方面,對后代學術界影響很大。《知不足齋叢書》,清鮑廷博輯,取《大戴禮記》中“學然后知不足”為義,30集,207種,781卷。這是個人編輯的富有參考價值的大型叢書之一。《二十二子》,題目頗為有趣,原來是清光緒年間浙江書局輯錄的、諸子百家的22種書,計有《老子》《莊子》《管子》《列子》《孫子》等。所據均為明代精刻、清代學者校訂之本,以精審著稱。
更有將同一種著作的各種版本匯集成書的,美其名曰“百衲本”,如百衲本《二十四史》。
2.5 辭書
辭書是指字典、詞典一類工具書的統稱。古舊辭書,既有綜合性的,更有專業性的,多不勝數。但字典比詞典更早成書,且影響更大。我國的第一部字典是《說文解字》,東漢許慎撰。“許典”歷經22年始成,收錄9 000余字,按部首排列,旨在分析文字形體結構,探究其原始意義。從漢字中析離出部首,以部首統類字典,是《說文解字》的首創,對后世影響巨大。我國第一部將古代字書編撰成后來通行字典模式的是明朝的《字匯》。該書由梅膺祚撰,共收字33 000余個,風靡于《康熙字典》問世以前。《康熙字典》由張玉書、陳廷敬等人奉康熙皇帝之命編撰,歷經6年始成,收47 000余字,成為我國收字最多的字典。在編撰字、詞典的基礎上,為滿足社會需求,編撰出更加大型的工具書,別其名曰“百科全書”。它收錄各種專門術語和名詞,按詞典形式分類編排,解說,引證極其詳細。
凡未能歸類的精神產品,只要有意義、有作用,也一律出版。存世的名著很多,如通俗小說四大名著;筆記神話《山海經》《西京雜記》《世說新語》《酉陽雜俎》《太平廣記》《夢溪筆談》;歷史軍事《左傳》《史記》《漢書》《孫子》《孫子兵法》……一言以蔽之,我國古代、近代出版的書籍,足以令世人震驚,所傳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加震驚世界。
更令人驚奇的是,古人為方便學子、官吏檢索所需字、詞、知識,不但編修綜合性的字典、詞典及百科全書,還編修出版專一用途的工具書,如《佩文詩韻》。
《佩文詩韻》由清代周兆基輯,輯自《佩文韻府》。此韻府是張玉書等人奉康熙之命編修的,444卷。詳則詳矣,但頗難翻檢。于是,周兆基刪繁就簡,“另成《佩文詩韻》, 專供作詩定韻征字之用”。但“初學之士仍苦其繁重”,周兆基再次刪節、修改,遂得《佩文詩韻釋要》,它“極為簡明方便,成為一部專供拈韻賦詩的詩韻書”。
筆者曾閱讀一部專為寫詩、作詩者服務的工具書,是《韻海大全·角山類腋》中的一部分,名叫《韻府精華》,由上海“鴻章書局石印”“上海文瑞樓發行”,線裝六卷(冊)一函。函箋為:《韻海大全·附角山樓類腋·上海棋盤街文瑞樓印行》。書中有類腋輯覽、詩學法程、韻府精華、韻府對偶等幾大部分。每個部分又分若干部。類腋輯覽分天部、地部、人部、物部;詩學法程分天文部、歲時部、地理部、帝治部、仕進部、德性部、文學部、文具部、武事部、武具部、禮制部等;韻府精華則按上平聲下平聲等排列。有趣的是,各大部分收錄的字、詞,不但釋義,舉例,還引用相關聯的古代詩文句子示范,直接教人如何參照應用。編排也有趣,由于本書是由上而下豎寫,從右向左排列,古人編排時,便將書頁橫分為三部分,上、中、下并排,便于學子檢索。如此書開篇第一頁,上排“類腋輯覽”天部之“天”,中排“韻府對偶”之“一東”,下排“韻府精華”上平聲之“一東”,為用者提供方便,古之出版界真是絞盡了腦汁。
此書之應用價值、學術價值,應該不低。這從該書的序中可以看出。曲園俞樾所寫序中道:“此韻本之遞興,亦詩懷之一助也。茲有仁壽室主人招集名流襄成雅事,偶因舊本別出裁,土飯塵羹則芟其蕪雜,謝華啟秀則萃其精英。集千腋之裘,因心作則;攬百年之帶,觸手成芬。數典爭奇,豈止珠船之一;選詞得偶,何難玉合之雙。運修月之斤,既玲瓏而散彩;揮凌云之筆,亦繚繞以成章。由是紅杏詞人、青蓮學士。”“但購一編常摩挲而不倦。”“右有左宣,更廣先生之胸筍;遙吟俯唱,頤開豪士之胸襟,能不秘為鴻寶,傳及溪林也哉?”(原文沒標點符號,此處標點乃引用者所加。文中之“斤”與“斧”通用。)
3 近代傳統文化出版的啟示
3.1 內容豐富,無與倫比
從現存的古代、近代出版的書籍看,內容之豐富,真是無與倫比。最大類是文學。先秦兩漢的文學著作出版,以詩經、楚辭、漢賦為主,包括詩、辭、賦的原創作品,以及對它們的注、釋、修訂、增補著作。魏晉南北朝的文學著作,側重于文選和個人詩文集,以及對詩文的評論著作。我國現存最早的著名文選就出在此時,即《昭明文選》。正是這本文選,將古老文學著作精華從古文獻中摘取出來,與史書中的經、史、子相區別,并賦予文學概念以基本內涵,曰:惟“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者[4],方可入籍文學。此時期重要文集,有《陶淵明集》《曹操集》《曹子建詩注》;重要文論有《二十四詩品》與《文心雕龍》。隋唐五代出版的文學作品,占古代文學著作的比重最大,主要是個人詩文集。宋代留下的文學著作以讀詞、散文為主。遼金元除詩詞外,增加了戲曲。明清文學出版的最大亮點是小說,我國的通俗小說四大名著均產于此時。
文學之后,出版物占比較大的是歷史書。與文學出版不同的是,各個朝代都很重視歷史著作的出版,造成出版數量比肩的盛況。看來,各朝統治者均注意以史為鑒,興利除敝。再往下,出版數量依次遞減的是哲學、宗教、政治、法律、軍事、語言文字、書畫、啟蒙讀物、地理、民族、醫學、科技等。由此可見,我國古代、近代出版是重文學而輕科技的。這正好與當時國家重文輕技的狀況相符。
3.2 形式多樣,便于查閱
由于古代、近代出版,主要靠刻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造成出版物只能以書籍的形式出現。如果書籍樣式單一,全是孤立的版本,我們想看一本書,堪比大海撈針。古人注意到這一點,將某些有聯系的著作歸類,因而有了總集、別集、文選、類書、叢書、辭書等。大型類書又按某種規律分成若干集,人們找書可以順藤(公認規律)摸瓜(書)。工具辭書則按部首排列,更方便查找某一字、詞。
3.3 編纂并非有文必錄
我國古代、近代出版的書籍,雖然浩如煙海,卻并不意味各個朝代編纂書籍有文必錄。古人是有選擇的,選擇的標準說法不一,歸納起來有以下幾條。
其一,有利于民族興盛。現存的許多書籍,至今有用, 活力四射,如《詩經》《楚辭》《文選》、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均功在千秋,利民萬代。
其二,允許學術爭論。古書中的學術爭論相當多。如《唐百家詩選》,北宋王安石編,故意不選李白、杜甫、王維、韋應物、韓愈、柳宗元等。這是因為王安石不喜歡他們的詩及學術之爭。又如《談龍錄》,清代趙執信撰[5],為批評王士禛而作。王士禛作詩,主張詩要有“神韻”[6]。趙執信不滿,批評其詩及“神韻”說,主張“詩以言志”“必使后人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
縱觀古代、近代出版的書籍,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現代出版條件極其先進的情況下,我們應當大幅度提高出版內容的豐富性,如出版種類的多樣化,以推動出版業持續發展繁榮,與偉大的時代相符。
第二,堅持利國利民的出版宗旨,花大力氣出好書,出對社會發展有用的書,追求功在千秋,福澤萬代,反對唯利而出版。
第三,提高編審人員素質,嚴格編審制度,盡可能減少差錯,做到精益求精。
第四,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創作、出版方針,兼顧不同流派、不同風格、不同角度的著作,以出版優秀書籍推動學術發展。
第五,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深入挖掘優質內容,積極探索傳播形式創新,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相適應、相協調。同時也需要關注當代社會的需求和話題,尋找與時俱進的選題[7]。
第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要注重形式的創新,以更好滿足廣大讀者需求。并且注重出版業與其他傳播形式的融合發展。出版是文化資源的集中載體,是文化傳播的基礎形態,更是文化產業的創意源頭。各大出版機構擁有豐富的文本、故事、資料、數據等資源優勢,需要充分挖掘和深度開發這些豐富而寶貴的文化資源,將文本化的傳統出版產品改編為影視、動漫、游戲、展覽、文旅等多元化的文化產品,推動出版業與相關文化產業進行跨界整合,促進“出版 +”文化新業態的繁榮發展[8]。
第七,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的博大氣象得益于中華文化自古以來開放的姿態、包容的胸懷。我們作為出版人,要積極推動豐富多彩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鑒。要通過版權國際合作與交流,更好地保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版權資源,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不斷提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9-10]。
4 結束語
出版業在深入挖掘傳統文化的內涵和精髓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通過尋找融合點,將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相結合,引導和推廣傳統文化作品,以及持續學習和更新知識,出版業可以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貢獻力量。進入新時代,我們更應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寶庫中挖掘優質精神產品,創新傳播形式以更好適應讀者需求,重視版權交流,與世界多種文明交流互鑒。努力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做出積極貢獻。我國出版業在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自身發展過程中,一定會越來越興旺。
參考文獻
[1] 雷丹露,李建軍.結合新的時代條件推動實現“兩創”[N].人民日報,2024-01-11(9).
[2] 劉洪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品的出版機制[J].中國編輯,2023(12):24-25.
[3] 陳雪云.明清官府書業述論[J].中州大學學報,2004(4):6-8.
[4] 王偉,倪超.含德與風教:蕭統推崇陶淵明之文化因由探析[J].中原文化研究,2022,10(2):68-75.
[5] 何夢潔.趙執信《談龍錄》中“崇尚真實”的詩學理論[J].黑河學刊,2015(10):20-21,24.
[6] 李柯楠.從《二家詩選》看王士禛的“神韻說”[J].青年文學家,2022(30):103-105.
[7] 楊翌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選題的新時代生產方向探索[J].編輯學刊,2023(6):116-120.
[8] 金韶,唐冰.從“Z世代”到“Z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的創新路徑[J].出版發行研究,2023(11):5-10.
[9] 張建春.版權賦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J].中國出版,2023(22):3-4.
[10]劉宇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轉化與繼承:實現古代智慧的現代價值[J].出版參考,2024(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