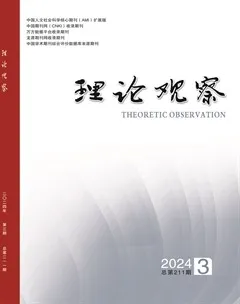從斯密、黑格爾到馬克思的勞動(dòng)觀的比較
馬靖涵
摘 要:勞動(dòng)作為人的生存方式一直是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哲學(xué)等學(xué)科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斯密從價(jià)值源泉的角度引入勞動(dòng),對(duì)勞動(dòng)的分析具有開(kāi)創(chuàng)性的作用;黑格爾則更多的是從法哲學(xué)角度出發(fā),但由于他只能看到抽象的精神勞動(dòng),而看不到現(xiàn)實(shí)的具體勞動(dòng),更看不到勞動(dòng)給人們帶來(lái)的苦難。而馬克思則繼承和發(fā)展了斯密和黑格爾的勞動(dòng)觀,通過(guò)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分析勞動(dòng)的現(xiàn)實(shí)意義,這些理論直至今天仍具有時(shí)代價(jià)值。
關(guān)鍵詞:資本;實(shí)踐;異化勞動(dòng);剩余價(jià)值論;雇傭勞動(dòng)
中圖分類(lèi)號(hào):B0-0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9 — 2234(2024)03 — 0040 — 05
一、亞當(dāng)·斯密的勞動(dòng)觀——價(jià)值的源泉
亞當(dāng)·斯密被譽(yù)為“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之父”,在其著作《國(guó)民財(cái)富的性質(zhì)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jiǎn)稱(chēng)《國(guó)富論》)中,明確指出勞動(dòng)是一切消費(fèi)的根源。在封建社會(huì)時(shí)期,人們普遍認(rèn)為財(cái)富是源于神的恩賜。然而,在15世紀(jì)的西歐,隨著封建主義的哀落和資本原始積累的出現(xiàn),新航路的開(kāi)辟帶動(dòng)了工商業(yè)的迅猛發(fā)展。一些西方國(guó)家開(kāi)始利用國(guó)家政策扶持資本主義的成長(zhǎng),逐步形成了重商主義的經(jīng)濟(jì)理念。在以英國(guó)為代表的重商主義中,“徹底實(shí)行分工之后,一人自己勞動(dòng)的產(chǎn)物,便僅能滿(mǎn)足自身隨時(shí)發(fā)生的需要的極小部分。其他大部分需要,必得仰賴(lài)他人勞動(dòng)產(chǎn)物來(lái)供給”[1]。法國(guó)重農(nóng)學(xué)派創(chuàng)始人弗朗索瓦·魁奈在法國(guó)從封建主義轉(zhuǎn)向資本主義的過(guò)程中,對(duì)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主張的大力發(fā)展工商業(yè)的重商政策不滿(mǎn),認(rèn)為他們嚴(yán)重破壞了農(nóng)業(yè)環(huán)境,從而提出重農(nóng)主義的政策;重農(nóng)主義相對(duì)于重商主義有一定的進(jìn)步,主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或某一類(lèi)的具體勞動(dòng)。但是斯密認(rèn)為在法國(guó)重農(nóng)主義背景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本質(zhì)上仍然是自給自足的經(jīng)濟(jì),是一種封閉的自然經(jīng)濟(jì)。并且斯密認(rèn)為,創(chuàng)造財(cái)富的不是這一種或那一種的勞動(dòng),而是抽象出的一般勞動(dòng)。重商主義和貨幣主義甚至認(rèn)為勞動(dòng)和財(cái)富無(wú)關(guān)。而斯密則認(rèn)為:“世間一切財(cái)富原來(lái)是用勞動(dòng)來(lái)購(gòu)買(mǎi),而不是用金銀來(lái)購(gòu)買(mǎi)的”[2] 。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馬克思對(duì)斯密高度評(píng)價(jià),稱(chēng)他為“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路德”,并稱(chēng)以斯密為代表的創(chuàng)立的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是啟蒙經(jīng)濟(jì)學(xué)。恩格斯曾在《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大綱》中對(duì)斯密的評(píng)價(jià)是“18世紀(jì)這個(gè)革命的世紀(jì)使經(jīng)濟(jì)學(xué)也發(fā)生了革命”[3],“一門(mén)完整的發(fā)財(cái)致富的科學(xué)代替了簡(jiǎn)單的不科學(xué)的生意經(jīng)”[4]。就像哈貝馬斯評(píng)價(jià)羅爾斯時(shí)指出《正義論》起到了實(shí)踐哲學(xué)的軸心式轉(zhuǎn)折點(diǎn)的作用,恩格斯的《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大綱》在馬克思思想轉(zhuǎn)向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的過(guò)程中也起到這樣的轉(zhuǎn)折點(diǎn)的作用。
在馬克思的理論視野中,亞當(dāng)·斯密所代表的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雖具開(kāi)創(chuàng)性,卻也存在概念的不徹底性。斯密指出勞動(dòng)是財(cái)富的源泉,而非神、金錢(qián)或是商業(yè)活動(dòng),并列入了一般勞動(dòng)顯示出理論的,“現(xiàn)代英國(guó)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也合乎邏輯的前進(jìn)一大步,它把勞動(dòng)提升為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唯一原則”[5]。然而,斯密在勞動(dòng)的價(jià)值上存在雙重維度“一方面他肯定勞動(dòng),另一方面,又聲稱(chēng)勞動(dòng)與自由無(wú)關(guān),甚至將勞動(dòng)視為痛苦和困擾。斯密這種對(duì)勞動(dòng)的矛盾性評(píng)價(jià),實(shí)質(zhì)上反映一種深刻的理論矛盾:在“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雖然從勞動(dòng)是生產(chǎn)的真正靈魂這一點(diǎn)出發(fā),但它沒(méi)有給勞動(dòng)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cái)產(chǎn)提供了一切”[6]。馬克思據(jù)此批判斯密的經(jīng)濟(jì)學(xué)不是辯證法,而是形而上學(xué)。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指出:“由經(jīng)濟(jì)思想史上觀察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派別,可分為三系,就是個(gè)人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與人道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7]。 其中個(gè)人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指的就是斯密、李嘉圖、穆勒這一系,是資產(chǎn)階級(jí)經(jīng)濟(jì)學(xué);而馬克思的經(jīng)濟(jì)學(xué)是社會(huì)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也稱(chēng)為“公經(jīng)濟(jì)學(xué)”。
在《國(guó)富論》中,斯密對(duì)資本的性質(zhì)進(jìn)行了分析,他使用了一個(gè)新的專(zhuān)業(yè)術(shù)語(yǔ):資財(cái),來(lái)描述個(gè)人或國(guó)家的全部財(cái)富。在他看來(lái),資產(chǎn)由兩部分構(gòu)成,一小部分供自身消費(fèi),另一部分繼續(xù)投資到市場(chǎng)賺取利潤(rùn),即馬克思所說(shuō)的資本。在這個(gè)意義上,馬克思認(rèn)為資本就是積累起來(lái)的勞動(dòng)。
馬克思的杰出貢獻(xiàn)在于,他超越了對(duì)物的關(guān)系的表層理解,深入揭示了人與物、人與人的深層關(guān)系。在《資本論》中,他對(duì)資本本質(zhì)的闡釋成為該書(shū)最卓越的成就,至今仍令很多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望其項(xiàng)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對(duì)此關(guān)系論述道:“這是一個(gè)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在這個(gè)世界里,資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為社會(huì)的人物,同時(shí)又直接作為單純的物,在興妖作怪”[8]。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者柯西克認(rèn)為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就是在論述這個(gè)物化的世界及其規(guī)律,而沒(méi)有說(shuō)明物的關(guān)系背后隱藏的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把物化的世界當(dāng)作了真正的人的世界,是一個(gè)顛倒的世界,這個(gè)世界也就是人的異化的世界。
在斯密眼中,每個(gè)人都在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勞動(dòng),這一點(diǎn)他是受了休謨的影響,認(rèn)為利己主義是人的本性;不論是為了滿(mǎn)足基本的生存條件還是獲得更好的生活,只要在不違反制度的情況下都可以選擇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勞動(dòng)。但看起來(lái)可以自由的選擇,實(shí)質(zhì)上也在無(wú)形中受到“看不見(jiàn)的手”的控制:“他受著一只看不見(jiàn)的手的指導(dǎo),去盡力達(dá)到一個(gè)并非他意想要達(dá)到的目的。也并不因?yàn)槭路浅鲇诒疽猓蛯?duì)社會(huì)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jìn)社會(huì)的利益”[9]。同時(shí),也正是斯密的這只“看不見(jiàn)的手”體現(xiàn)出了他在哲學(xué)上的邏輯,看到了在資本經(jīng)濟(jì)社會(huì)中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規(guī)律。
斯密的勞動(dòng)價(jià)值論揭示了交換背后的價(jià)值規(guī)律,這種規(guī)律體現(xiàn)了商品之間的等價(jià)交換原則,即以相等價(jià)值的物品相互交換滿(mǎn)足各自的需求。自原始社會(huì)末期,當(dāng)交換雙方都還有剩余產(chǎn)品時(shí),交換才得以偶然發(fā)生;隨著生產(chǎn)力的提升和分工的細(xì)化,物與物之間的交換逐漸變得頻繁,交換的種類(lèi)也不再局限于某個(gè)類(lèi)別,形成了一種擴(kuò)大了的物物交換;再到現(xiàn)在社會(huì)形成的普遍的物物交換,即從偶然的物物交換到擴(kuò)大的物物交換再到一般的物物交換,這時(shí)的物就成為了商品。馬克思曾說(shuō):“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huì)的財(cái)富,表現(xiàn)為‘龐大的商品堆積”[10],實(shí)質(zhì)就是對(duì)他人勞動(dòng)的占有。
二、黑格爾的勞動(dòng)觀——抽象的精神勞動(dòng)
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集大成者黑格爾對(duì)勞動(dòng)觀的闡述也對(duì)馬克思的勞動(dòng)觀提供了重要的啟發(fā)。黑格爾辯證法的偉大之處就是在于他把勞動(dòng)看作是人的本質(zhì),但是黑格爾只承認(rèn)有一種勞動(dòng)方式——抽象的精神勞動(dòng)。
黑格爾在自己的思想發(fā)展進(jìn)程中,三次集中地提到了“勞動(dòng)”。在耶拿演講中他指出,“勞動(dòng)不是本能,而是一種‘理性活動(dòng),是一種‘精神的方式”[11]。動(dòng)物是沒(méi)有自我意識(shí)的,而人的勞動(dòng)是一種精神和意識(shí)的體現(xiàn),人和動(dòng)物的本質(zhì)區(qū)別就是人有自我意識(shí)。在這里,黑格爾還把勞動(dòng)劃分成三種階層:農(nóng)民階層、手工業(yè)階層和商人階層。在《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中,黑格爾把勞動(dòng)視作一種“受阻礙的欲望”;指出勞動(dòng)者通過(guò)自己的勞動(dòng)來(lái)實(shí)現(xiàn)“自我確證”,“他通過(guò)在自己的勞動(dòng)對(duì)象中重新找到自我而獲得了一種特殊的、自我的感覺(jué),一種‘自己的感覺(jué),從而獲得了一種奴性?xún)?nèi)部的自由”[12]。奴隸通過(guò)自身的勞動(dòng)來(lái)滿(mǎn)足自己的生存所需,同時(shí),也滿(mǎn)足了他人的需求;主人對(duì)奴隸表面上只具有支配權(quán),但實(shí)際上主人的生存也離不開(kāi)奴隸的勞動(dòng)。從耶拿演講到《精神現(xiàn)象學(xué)》,黑格爾的勞動(dòng)觀實(shí)現(xiàn)了從哲學(xué)向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轉(zhuǎn)變。
在《法哲學(xué)原理》中,黑格爾與馬克思一樣,都是在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基礎(chǔ)上看待勞動(dòng)的:“在那里,他在哲學(xué)上就像除他之外只有馬克思做到的那樣,認(rèn)真的對(duì)待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13]。黑格爾說(shuō):“人在自己消費(fèi)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人的產(chǎn)品,而他所消費(fèi)的正是人的努力的成果…人通過(guò)流汗和勞動(dòng)而獲得滿(mǎn)足需要的手段”[14]。馬克思受黑格爾的影響不僅局限在辯證法上,在《法哲學(xué)原理》《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和《邏輯學(xué)》等著作中,尤其是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角度上,也給馬克思很多啟發(fā)。列寧在《哲學(xué)筆記》中指出:“不鉆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xué),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1章”[15]。
社會(huì)中的個(gè)人不孤立存在于他人及社會(huì)的關(guān)系往往通過(guò)物質(zhì)利益這一媒介體現(xiàn)。個(gè)體與他人的相互滿(mǎn)足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gè)社會(huì)需要的網(wǎng)絡(luò),即體現(xiàn)了每個(gè)人需要的特殊性,也包含著社會(huì)交換的普遍性。馬克思稱(chēng)黑格爾的哲學(xué)是一種非批判的唯心主義,因?yàn)楹诟駹栔豢吹搅藙趧?dòng)的積極性,卻沒(méi)有看到勞動(dòng)給人民帶來(lái)的苦難,因此沒(méi)有區(qū)分對(duì)象化和異化。因?yàn)楹诟駹柕漠惢^只能停留在思維中,在現(xiàn)實(shí)中沒(méi)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是“非批判”的。因?yàn)槿说纳娣绞绞侨说淖晕耶惢匀说膭趧?dòng)就是異化勞動(dòng)。黑格爾的異化觀被費(fèi)爾巴哈評(píng)價(jià)為“哲學(xué)同自身的矛盾”,否定神學(xué)之后又肯定了神學(xué),最終還是回到了絕對(duì)精神的領(lǐng)域。因此,在黑格爾的勞動(dòng)觀中,他只看到了人在勞動(dòng)中的自我實(shí)現(xiàn),而沒(méi)有看到人的自我異化。
黑格爾的全部哲學(xué)體系以絕對(duì)精神為核心,在《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中黑格爾與以往的哲學(xué)家不同的是他沒(méi)有使用理性,而是使用了精神這個(gè)概念來(lái)表示人的本性。當(dāng)這個(gè)精神超越自己之后就變?yōu)榻^對(duì)精神。因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以下簡(jiǎn)稱(chēng)《手稿》)中指出:他“唯一知道并承認(rèn)的勞動(dòng)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dòng)”[16]。在黑格爾的勞動(dòng)觀中,“現(xiàn)實(shí)的人”是勞動(dòng)的客體,而真正的勞動(dòng)主體是絕對(duì)精神,從此可知他顛倒了勞動(dòng)的主客體的二元關(guān)系。這種勞動(dòng)并不是能改變世界的現(xiàn)實(shí)勞動(dòng),不可避免地淪為絕對(duì)主體“在自身內(nèi)部的純粹的、不停息的旋轉(zhuǎn)[17]。
從這個(gè)意義上看,黑格爾對(duì)馬克思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馬克思早期閱讀黑格爾和費(fèi)爾巴哈文獻(xiàn)時(shí),想要用異化的思想實(shí)現(xiàn)人類(lèi)解放,在后期充分閱讀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之后,馬克思用“雇傭勞動(dòng)”代替了“異化勞動(dòng)”;在《手稿》中想要揚(yáng)棄異化到后期以《資本論》為代表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中的商品拜物教到貨幣拜物教再到資本拜物教的批判。這個(gè)過(guò)程也僅能證明馬克思使用詞語(yǔ)方式的變化,并不能證明他放棄了人類(lèi)解放的最初理想,因此,法國(guó)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家阿爾都塞提出的認(rèn)識(shí)論的斷裂的青年馬克思和老年馬克思的“兩個(gè)馬克思之爭(zhēng)”并不成立。
三、馬克思的勞動(dòng)觀——自由自覺(jué)的實(shí)踐活動(dòng)
馬克思批判了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和以黑格爾代表的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在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意義上,它們都是勞動(dòng)的形而上學(xué)。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青年黑格爾派自我意識(shí)時(shí)曾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實(shí)現(xiàn)什么東西。為了實(shí)現(xiàn)思想就要有使用實(shí)踐力量的人”[18]。自我意識(shí)不能創(chuàng)造任何現(xiàn)實(shí)的東西,而必須是現(xiàn)實(shí)的,哪怕是粗糙的物質(zhì)生產(chǎn),這時(shí)馬克思已經(jīng)初步形成唯物史觀。
馬克思認(rèn)為人與動(dòng)物正是在勞動(dòng)的意義上區(qū)別開(kāi)來(lái)的:“動(dòng)物只生產(chǎn)它自己或它的幼崽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dòng)物的生產(chǎn)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chǎn)是全面的……動(dòng)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gè)種的尺度和需要來(lái)構(gòu)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gè)種的尺度來(lái)進(jìn)行生產(chǎn),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yùn)用于對(duì)象”[19]。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的精神勞動(dòng),說(shuō)明勞動(dòng)不是精神的環(huán)節(jié),而精神是勞動(dòng)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勞動(dòng)看作是勞動(dòng)和增殖過(guò)程的統(tǒng)一。工人出賣(mài)自己的勞動(dòng)為資本家創(chuàng)造價(jià)值,把自己的體力勞動(dòng)和腦力勞動(dòng)體現(xiàn)在商品上,這個(gè)完整的勞動(dòng)過(guò)程就是“把它描述為它的簡(jiǎn)單的、抽象的要素來(lái)說(shuō),是制造使用價(jià)值的有目的的活動(dòng),是為了人類(lèi)的需要而對(duì)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lèi)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20];資本家購(gòu)買(mǎi)工人的勞動(dòng)力,在規(guī)定時(shí)間內(nèi)雇傭工人進(jìn)行生產(chǎn),為了獲得利潤(rùn),這個(gè)產(chǎn)品中不僅有生產(chǎn)資料和勞動(dòng)力的成本,還要有多出來(lái)的那個(gè)部分。勞動(dòng)力的價(jià)值和勞動(dòng)力在生產(chǎn)過(guò)程中實(shí)現(xiàn)的價(jià)值增殖,是兩個(gè)不同的量,資本家在購(gòu)買(mǎi)勞動(dòng)力時(shí)看中的就是這個(gè)價(jià)值差:“他不僅要生產(chǎn)使用價(jià)值,而且要生產(chǎn)商品,不僅要生產(chǎn)使用價(jià)值,而且要生產(chǎn)價(jià)值,不僅要生產(chǎn)價(jià)值,而且要生產(chǎn)剩余價(jià)值”[21]。這個(gè)論述不僅說(shuō)明了勞動(dòng)是二者的統(tǒng)一,同時(shí)也為他之后論述剩余價(jià)值奠定了基礎(chǔ)。
馬克思把勞動(dòng)二分為必要?jiǎng)趧?dòng)和自由勞動(dòng):“外在目的失掉了單純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觀,被看作個(gè)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實(shí)現(xiàn),主體的對(duì)象化, 也就是實(shí)在的自由——而這種自由見(jiàn)之于活動(dòng)恰恰就是勞動(dòng)——這也是亞當(dāng)·斯密料想不到的” 。阿倫特在其著作《人的境況》開(kāi)篇中就指出:“三種根本性的人類(lèi)活動(dòng):勞動(dòng)、工作和行動(dòng)。這三種活動(dòng)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yàn)樗鼈兠恳粋€(gè)都相應(yīng)于人在地球上被給定的生活的一種基本條件”[23]。
馬克思的勞動(dòng)價(jià)值論的目的不是揭示商品價(jià)值的來(lái)源問(wèn)題,而是要深層次地挖掘利潤(rùn)背后的秘密,進(jìn)而說(shuō)明工資和工人全部的勞動(dòng)成果并不是等價(jià)的。因此可以說(shuō)馬克思從勞動(dòng)價(jià)值論走向了剩余價(jià)值論。資本家們所購(gòu)買(mǎi)的不是勞動(dòng),而是勞動(dòng)力,勞動(dòng)力會(huì)生產(chǎn)出比自身價(jià)值更大的價(jià)值,而這一部分“差價(jià)”,就是剩余價(jià)值。勞動(dòng)力作為一個(gè)商品被資本家買(mǎi)賣(mài),從而獲利。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huà)》中高度評(píng)價(jià)了剩余價(jià)值論的發(fā)現(xiàn):“由于剩余價(jià)值的發(fā)現(xiàn),這里就豁然開(kāi)朗了,而先前無(wú)論資產(chǎn)階級(jí)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或者社會(huì)主義批評(píng)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馬克思一生最重大的兩大發(fā)現(xiàn):唯物史觀和剩余價(jià)值理論,其中唯物史觀說(shuō)明了人類(lèi)社會(huì)的一般規(guī)律,物質(zhì)生活的生產(chǎn)資料是人類(lèi)社會(huì)最基本的需要;剩余價(jià)值理論則說(shuō)明了資本主義社會(huì)發(fā)展的特殊規(guī)律。
馬克思的《資本論》被稱(chēng)為“工人階級(jí)的圣經(jīng)”,勞動(dòng)者意識(shí)到了自己的勞動(dòng)和工資的不等,但卻認(rèn)為是機(jī)器奪走了工作,以至于他們罷工,要求廢除機(jī)器。馬克思恩格斯通過(guò)《資本論》向工人說(shuō)明真正使他們失去自由的原因不是機(jī)器,而是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制度。隨著工業(yè)革命的興起,大量的機(jī)器進(jìn)入工廠,這種看起來(lái)能夠減輕勞動(dòng)者工作強(qiáng)度的工具實(shí)際上卻成為了工人的另一個(gè)“競(jìng)爭(zhēng)者”。
同時(shí),馬克思還用了一系列概念,把統(tǒng)一的勞動(dòng)劃分為對(duì)立的兩部分,從而更好地說(shuō)明勞動(dòng)是怎樣在生產(chǎn)過(guò)程中異化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guò)對(duì)商品的分析揭示了勞動(dòng)的二重性,即抽象勞動(dòng)和具體勞動(dòng)。在此之前他已經(jīng)得出了“勞動(dòng)創(chuàng)造價(jià)值”這一結(jié)論,創(chuàng)造價(jià)值的勞動(dòng)是凝結(jié)在商品中無(wú)差別的一般人類(lèi)勞動(dòng);而人們?cè)谏a(chǎn)過(guò)程中的具體形態(tài)的勞動(dòng)創(chuàng)造的是商品的使用價(jià)值。商品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價(jià)值不同是因?yàn)樵谏a(chǎn)活動(dòng)中的具體勞動(dòng)不同;而商品本身的價(jià)值是由抽象出來(lái)的無(wú)差別的一般勞動(dòng)決定的,商品的交換遵循的也是這樣一種等價(jià)原則。馬克思認(rèn)為“勞動(dòng)的二重性理論是理解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樞紐”[24]。 馬克思還運(yùn)用了“活勞動(dòng)”和“死勞動(dòng)”這兩個(gè)相對(duì)立的范疇揭示資本和勞動(dòng)之間的對(duì)抗關(guān)系。活勞動(dòng)作為一種處于流動(dòng)狀態(tài)下的勞動(dòng)時(shí)刻消耗著勞動(dòng)者的腦力勞動(dòng)和體力勞動(dòng),活勞動(dòng)創(chuàng)造價(jià)值;而死勞動(dòng)也稱(chēng)為物化勞動(dòng),是凝結(jié)在勞動(dòng)對(duì)象中的,其背后是人類(lèi)的一般勞動(dòng),最后表現(xiàn)為生產(chǎn)資料不能創(chuàng)造價(jià)值而只能轉(zhuǎn)移價(jià)值的勞動(dòng)。勞動(dòng)者通過(guò)勞動(dòng)工具創(chuàng)造出的產(chǎn)品在交換后獲得的價(jià)值,一部分歸于資本家所有,一部分繼續(xù)進(jìn)入下一個(gè)資本循環(huán)當(dāng)中。換言之,工人自己生產(chǎn)出的產(chǎn)品成了剝削自己的“主人”,其實(shí)質(zhì)就是工人自己的“死勞動(dòng)”對(duì)“活勞動(dòng)”的剝削,這也就是《手稿》中的勞動(dòng)者與自己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相對(duì)立:“勞動(dòng)所生產(chǎn)的對(duì)象,即勞動(dòng)的產(chǎn)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lài)于生產(chǎn)者的力量,同勞動(dòng)相對(duì)立”[25]。工人在工作中越努力,生產(chǎn)的價(jià)值越多,反而對(duì)自己的剝削和控制就越嚴(yán)重,這種異化勞動(dòng)成為真正禁錮勞動(dòng)者的枷鎖。
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指出:“整個(gè)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guò)人的勞動(dòng)而誕生的過(guò)程,是自然界對(duì)人來(lái)說(shuō)的生成過(guò)程”[26]。社會(huì)不同形態(tài)和形式的發(fā)展都是通過(guò)勞動(dòng)和實(shí)踐的推動(dòng)而前進(jìn)的。當(dāng)前,我國(guó)已經(jīng)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duì)貧困的問(wèn)題,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的全面勝利,標(biāo)志著黨在團(tuán)結(jié)帶領(lǐng)全體人民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實(shí)現(xiàn)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這些成就離不開(kāi)勞動(dòng)者雙手創(chuàng)造的勞動(dòng),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也曾在講話(huà)時(shí)提出:“必須牢固樹(shù)立勞動(dòng)最光榮、勞動(dòng)最崇高、勞動(dòng)最偉大、勞動(dòng)最美麗的觀念”[27]。馬克思的勞動(dòng)觀“勞動(dòng)創(chuàng)造價(jià)值”的價(jià)值觀對(duì)今天的中國(guó)的啟示仍有重要的實(shí)踐意義,“擼起袖子加油干”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馬克思一生不懈地追求人類(lèi)解放,自中學(xué)畢業(yè)至晚年,他始終致力于幫助最底層的勞動(dòng)人民擺脫苦難的生活。無(wú)產(chǎn)階級(jí)作為被徹底的鎖鏈?zhǔn)`著的階級(jí)想要獲得自身的解放就要解放全人類(lèi)。
〔參 考 文 獻(xiàn)〕
[1] [英]斯密.國(guó)民財(cái)富的性質(zhì)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亞楠,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72:252.
[2] [英]斯密.國(guó)民財(cái)富的性質(zhì)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亞楠,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72:25.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3.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6.
[7]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J].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hào).
[8]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40.
[9]斯密.國(guó)民財(cái)富的性質(zhì)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亞楠,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72:27.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
[11] [德]卡爾·洛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M].李秋零,譯.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6:358.
[12] [德]卡爾·洛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M].李秋零,譯.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6:359.
[13] [德]卡爾·洛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M].李秋零,譯.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6:365.
[14] [德]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M].范揚(yáng),張企泰,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6:209.
[15] [俄]列寧.哲學(xué)筆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51.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5.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8.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52.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163.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5.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8.
[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4.
[23][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M].王寅麗,譯.北京:人民出版,2009:1.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6.
[27]習(xí)近平.同全國(guó)模范勞動(dòng)代表座談時(shí)的講話(huà)[N].人民日?qǐng)?bào),2013-04-28.
〔責(zé)任編輯:侯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