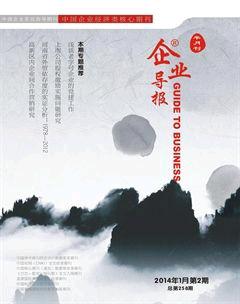探究創(chuàng)業(yè)能力維度的新要素:基于資源基礎(chǔ)觀視角
王國(guó)林
摘 要:家族中存在的“假性和諧”為家族企業(yè)發(fā)展帶來(lái)了極大的隱患。為了回應(yīng)理論和現(xiàn)實(shí)需要,借鑒組織理論,以家族凝聚力作為切入點(diǎn)經(jīng)過(guò)理論推理提出創(chuàng)業(yè)能力新要素——家族創(chuàng)業(yè)凝聚能力,并認(rèn)為它對(duì)于避免家族"不和諧"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
關(guān)鍵詞:創(chuàng)業(yè)能力;家族凝聚能力;資源基礎(chǔ)觀
一、問(wèn)題的提出
張正峰(2006)[1]在研究中指出,家族性資源在家族企業(yè)內(nèi)部發(fā)揮積極作用的同時(shí),也會(huì)給家族造成“假性和諧”,這是家族性資源的各種要素共同作用下制造的“漩渦”。他在研究中進(jìn)一步指出,這種隱患達(dá)到一定程度后打破家族的和諧氛圍,家族內(nèi)部出現(xiàn)混亂,導(dǎo)致家族企業(yè)潰于一旦,家族創(chuàng)業(yè)最終將會(huì)宣告失敗并有可能伴隨著家族分裂。家族企業(yè)是由家族系統(tǒng)和企業(yè)系統(tǒng)構(gòu)成的二元體,任何一個(gè)系統(tǒng)出現(xiàn)故障都會(huì)影響到整個(gè)家族企業(yè)的發(fā)展。
經(jīng)典文獻(xiàn)中學(xué)者對(duì)家族成員利他主義的絕對(duì)肯定造成了其他學(xué)者對(duì)家族和諧問(wèn)題的忽視,同時(shí)認(rèn)可了家族成員的利益一致性。然而現(xiàn)實(shí)中“兄弟分家”和“父子反目”等真實(shí)案例的頻繁發(fā)生對(duì)這些固有認(rèn)識(shí)提出了挑戰(zhàn)。遺憾的是,張正峰并未就他發(fā)現(xiàn)的問(wèn)題給出有針對(duì)性的建議。家族和諧是家族和企業(yè)獲得成長(zhǎng)的根本性保障,消除或避免破壞和諧的因素,其意義不言而喻。因此這成為本文的落腳點(diǎn),即尋求如何有效避免“假性和諧”的爆發(fā)。張正峰從資源基礎(chǔ)觀(RBV)的角度去探索影響家族企業(yè)成長(zhǎng)和發(fā)展的因素,而恰巧同時(shí)他發(fā)現(xiàn)了家族性資源也能產(chǎn)生“負(fù)面效應(yīng)”,為家族和諧帶來(lái)威脅。同樣地,本文將繼續(xù)遵循這種思路,試圖從資源基礎(chǔ)觀視角找到應(yīng)對(duì)之策。
二、創(chuàng)業(yè)能力新要素的探索
(一)RBV視角的家族企業(yè)研究
當(dāng)家族企業(yè)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當(dāng)中的地位日益突顯,理論界紛紛將研究目光從大型國(guó)企轉(zhuǎn)向這一特殊的企業(yè)形式。其特殊之處在于,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權(quán)和企業(yè)所有權(quán)都集中于家族當(dāng)中,這與非家族企業(yè)兩權(quán)分立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而后有相當(dāng)多的研究證實(shí),家族企業(yè)在企業(yè)績(jī)效方面優(yōu)于非家族企業(yè)。這種差異的存在吸引了更多的研究把目光聚焦于探索這種差異的原因。
資源基礎(chǔ)觀理論的代表學(xué)者Barney(1991)[2]指出,企業(yè)間的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差異源于其不同的資源,企業(yè)內(nèi)部的特定資源能夠使得企業(yè)具備獨(dú)一無(wú)二的優(yōu)勢(shì)。RBV理論為家族企業(yè)研究提供了借鑒方向,資源觀開(kāi)始逐漸滲透創(chuàng)業(yè)研究領(lǐng)域,家族性資源就是資源基礎(chǔ)觀引入家族企業(yè)研究的衍生概念。而筆者發(fā)現(xiàn),無(wú)論是Barney還是Penrose,他們從資源角度研究企業(yè)的理論中都指出,資源的獨(dú)特性產(chǎn)出形式為企業(yè)獨(dú)特的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是一種競(jìng)爭(zhēng)能力的表征。因此,本文認(rèn)為可以借助能力理論視角做進(jìn)一步探索。
我們的研究出發(fā)點(diǎn)在于如何消除家族內(nèi)部“假性和諧”,實(shí)現(xiàn)家族企業(yè)健康持續(xù)的發(fā)展。一般認(rèn)為,家族企業(yè)通過(guò)不斷的創(chuàng)業(yè)活動(dòng)獲得持續(xù)發(fā)展,而以家族性資源為支撐的創(chuàng)業(yè)能力直接決定了家族創(chuàng)業(yè)的成敗。據(jù)此,我們把家族性資源影響家族企業(yè)成敗的路徑理解為“家族性資源—能力—?jiǎng)?chuàng)業(yè)成功或失敗”。有學(xué)者也指出,能力作為資源和創(chuàng)業(yè)績(jī)效之間的中介要素,其作用不容忽視(葛寶山和董保寶,2009)[3]。循著這種路徑,我們決定從能力理論著手繼續(xù)分析。
創(chuàng)業(yè)能力能夠決定創(chuàng)業(yè)的成敗已成創(chuàng)業(yè)研究領(lǐng)域一個(gè)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而“和諧”的家族環(huán)境可以為家族創(chuàng)業(yè)保駕護(hù)航,提供持續(xù)的資源支撐。那么,當(dāng)“和諧”除了故障,創(chuàng)業(yè)能力能夠解決?或者說(shuō),創(chuàng)業(yè)能力能否避免“不和諧”的發(fā)生?
(二)創(chuàng)業(yè)能力
據(jù)此,我們將對(duì)創(chuàng)業(yè)能力維度是否能夠避免家族“不和諧”進(jìn)行下一步的分析。從上表直觀地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機(jī)會(huì)識(shí)別能力、戰(zhàn)略能力以及承諾能力與我們需要解決的問(wèn)題沒(méi)有直接的聯(lián)系。接下來(lái),我們將考察其余幾項(xiàng)能力維度。
從Man & Lau的定義看來(lái),關(guān)系能力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與個(gè)體之間、個(gè)體與組織之間的互動(dòng)聯(lián)系,是人際關(guān)系導(dǎo)向的一個(gè)能力指標(biāo)。但通過(guò)文獻(xiàn)我們進(jìn)一步發(fā)現(xiàn),Man & Lau提出的關(guān)系能力本義在于考察企業(yè)如何在其內(nèi)部利益群體(雇員)以及企業(yè)與外部利益關(guān)系群體(如供應(yīng)商、銀行、貿(mào)易伙伴以及政府等)中建立良好關(guān)系以獲取發(fā)展所需資源和信息的能力。其后的學(xué)者們也基本把關(guān)系研究限定在這兩個(gè)方面,然而企業(yè)需要建立的關(guān)系是以商業(yè)契約為基礎(chǔ)的,并且關(guān)系能力是一種尋求關(guān)系租金的網(wǎng)絡(luò)行為能力,因此也稱為網(wǎng)絡(luò)能力。雖然這種能力側(cè)重關(guān)系處理,但家族特殊信任體系下的關(guān)系顯然是不同的。因此它對(duì)給家族內(nèi)部關(guān)系的維系沒(méi)有直接的指導(dǎo)意義。概念能力是創(chuàng)業(yè)者個(gè)人對(duì)復(fù)雜問(wèn)題進(jìn)行概念化以降低復(fù)雜性的能力,是創(chuàng)業(yè)者個(gè)人思維能力方面的體現(xiàn)。Man & Lau認(rèn)為,擁有概念能力的創(chuàng)業(yè)者可以用新的思維思考創(chuàng)業(yè)過(guò)程中遇到的問(wèn)題,更多體現(xiàn)于個(gè)體在創(chuàng)業(yè)過(guò)程中解決不確定性問(wèn)題、作出決策并承擔(dān)風(fēng)險(xiǎn)的能力。創(chuàng)業(yè)是一項(xiàng)復(fù)雜的活動(dòng),涉及到許多的資源和要素。因此要求創(chuàng)業(yè)者在不同的職能領(lǐng)域切換,活動(dòng)涉及到企業(yè)人力、物力、財(cái)力和技術(shù)等方面的資源調(diào)配。這要求創(chuàng)業(yè)者具備全局觀,具備組織(管理)能力。
很顯然,概念能力和組織能力沒(méi)有涵蓋“關(guān)系職能”,并且這兩項(xiàng)能力并未細(xì)化到“關(guān)系”處理層面,創(chuàng)業(yè)能力學(xué)者們給出了關(guān)系能力履行創(chuàng)業(yè)過(guò)程中的“關(guān)系職能”。然而通過(guò)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關(guān)系能力所關(guān)注的“關(guān)系”是建立在商業(yè)契約基礎(chǔ)之上,而家族內(nèi)部關(guān)系則是建立在特殊信任基礎(chǔ)之上。因此,現(xiàn)有的創(chuàng)業(yè)能力并不能兼顧家族“不和諧”的發(fā)生與否。
(三)家族凝聚能力
Mullen & Copper(1994)[8]認(rèn)為凝聚力是良好的關(guān)系潤(rùn)滑劑,能夠極大地減輕組織中個(gè)體之間的摩擦,有效避免不“和諧”現(xiàn)象的發(fā)生。而家族和諧是家族企業(yè)獲得持續(xù)成長(zhǎng)的重要因素(Graves&Thomas,2008)[9]。賀小剛等人(2010)[10]指出,家族和諧對(duì)企業(yè)的影響復(fù)雜而重要。他們從家族權(quán)力配置視角,實(shí)證研究發(fā)現(xiàn)家族不和諧會(huì)阻礙家族企業(yè)的發(fā)展,家族和諧與家族企業(yè)持續(xù)成長(zhǎng)之間呈現(xiàn)非線性倒U型關(guān)系。
Festinger(1968)[11]用“吸引力”來(lái)簡(jiǎn)潔地闡述團(tuán)隊(duì)凝聚力。“吸引力”體現(xiàn)為個(gè)體相互吸引并愿意在一起工作的意愿程度(段萬(wàn)春、王云和李宏茜,2009)[12]。隨后,F(xiàn)estinger的定義得到普遍認(rèn)可,并在此基礎(chǔ)上有學(xué)者提出這種吸引力應(yīng)當(dāng)包括兩個(gè)方面,一是組織中個(gè)體之間的吸引力,二是組織對(duì)個(gè)體的吸引力(何虎,2005)[13]。孫美佳和崔勛(2013)[14]認(rèn)為凝聚力是一種歸屬性情緒體驗(yàn),它存在于員工與組織以及員工與員工之間。
凝聚力能夠產(chǎn)生或增強(qiáng)個(gè)體忠誠(chéng)、榮譽(yù)感和責(zé)任感(李樹(shù)祥等,2012)[15],從而把“不和諧”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因此,凝聚力對(duì)于組織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對(duì)于家族這樣的特殊組織來(lái)說(shuō)更是如此。因?yàn)榧易迳嫒肫髽I(yè)為家族企業(yè)帶來(lái)了復(fù)雜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其復(fù)雜程度遠(yuǎn)高于非家族企業(yè)。本文認(rèn)為家族內(nèi)部的“不和諧”源于因利益排斥導(dǎo)致成員彼此間的“吸引力”受到破壞。然而如何確保家族內(nèi)部能夠持續(xù)存在有益于家族和企業(yè)持續(xù)發(fā)展的凝聚力呢?賀小剛和李新春(2005)[16]結(jié)合問(wèn)卷調(diào)查通過(guò)因子分析發(fā)現(xiàn),關(guān)系能力被分解為兩個(gè)部分:政府關(guān)系能力和社會(huì)關(guān)系能力。我們可以理解為,不同關(guān)系的性質(zhì)需要具備相應(yīng)的能力。借鑒這種思路,本文在創(chuàng)業(yè)能力當(dāng)中加入家族凝聚能力要素,作為家族創(chuàng)業(yè)過(guò)程中需要適時(shí)調(diào)整和維護(hù)家族成員關(guān)系穩(wěn)定性的能力補(bǔ)充。
四、總結(jié)
張正峰在資源觀視角的研究中指出家族中存在“不和諧”現(xiàn)象而未給出應(yīng)對(duì)建議,這是本文研究興趣的來(lái)源。本文認(rèn)為,家族和諧對(duì)于家族和企業(yè)的持續(xù)發(fā)展而言,其重要性無(wú)可替代。立足于資源基礎(chǔ)觀視角,本文試圖從該視角中找到一些研究線索。而后通過(guò)分析發(fā)現(xiàn),能力理論可以為本文的進(jìn)一步研究提供思路。最后通過(guò)對(duì)家族創(chuàng)業(yè)能力的分析發(fā)現(xiàn),現(xiàn)有能力要素在家族特定背景中尚存在不足。本文認(rèn)為家族凝聚力能夠更好地解決家族“不和諧”,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創(chuàng)業(yè)能力的新要素—家族凝聚能力。然而鑒于本文完全是建立在理論推理基礎(chǔ)之上完成的,因此本文認(rèn)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在于探索這一新要素的維度劃分以及測(cè)量,希望能夠取得實(shí)證研究上的支持。
參考文獻(xiàn):
[1] 張正峰. 家族性資源與家族企業(yè)中的假性和諧[J]. 特區(qū)經(jīng)濟(jì),2006(11):98-99.
[2]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17(1):99-120.
[3] 葛寶山, 董保寶. 基于動(dòng)態(tài)能力中介作用的資源開(kāi)發(fā)過(guò)程與新創(chuàng)企業(yè)績(jī)效關(guān)系研究[J]. 管理學(xué)報(bào), 2009,6(4):520-526.
[4] Low M B, MacMillan I C. Entrepreneurship: Past research and future challeng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8,14(2):139-161.
[5] 唐靖, 姜彥福. 創(chuàng)業(yè)能力概念的理論構(gòu)建及實(shí)證檢驗(yàn)[J]. 科學(xué)學(xué)與科學(xué)技術(shù)管理, 2008,29(8): 52-57.
[6] Man T W Y, Lau T.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of SME owner/managers in the Hong Kong services sector: a qualitative analysis[J]. 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ulture, 2000,8(03):235-254.
[7] Shane S, Venkataraman S.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25(1):217-226.
[8] Mullen B, Copper C. The relation between group cohesiveness and performance: An integration[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4,115(2):210.
[9] Graves, C., & Thomas, J. Determinant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athways of family firms: An examination of family influence. Family Business Review,2008,21(2):151-167.
[10] 賀小剛, 連燕玲, 余冬蘭. 家族和諧與企業(yè)可持續(xù)成長(zhǎng)——基于家族權(quán)力配置的視角[J]. 經(jīng)濟(jì)管理, 2010, 32(1):50-60.
[11] Festinger L, White C W, ALLYN M R. Eye movements and decrement in the Muller-Lyer illusion[J]. 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 1968, Vol 3(5-B):376-382.
[12] 段萬(wàn)春, 王云, 李宏茜. 群體凝聚力與組織生產(chǎn)率關(guān)系深層分析[J]. 科學(xué)學(xué)與科學(xué)技術(shù)管理, 2009 (8): 131-135.
[13] 何虎. 淺析群體凝聚力的形成和強(qiáng)化[J]. 四川生殖衛(wèi)生學(xué)院學(xué)報(bào), 2005 (4): 26-29.
[14] 孫美佳,崔勛.組織公平與組織信任的文化特質(zhì)性及其對(duì)中國(guó)企業(yè)凝聚力形成的影響[J]. 管理學(xué)報(bào), 2013,10(10):1462-1469.
[15] 李樹(shù)祥, 梁巧轉(zhuǎn), 孟瑤. 團(tuán)隊(duì)多樣性氛圍, 團(tuán)隊(duì)凝聚力和團(tuán)隊(duì)創(chuàng)造能力的關(guān)系研究[J]. 軟科學(xué), 2012, 26(7): 91-95.
[16] 賀小剛, 李新春. 企業(yè)家能力與企業(yè)成長(zhǎng): 基于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的實(shí)證研究[J]. 經(jīng)濟(jì)研究, 2005, 10: 1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