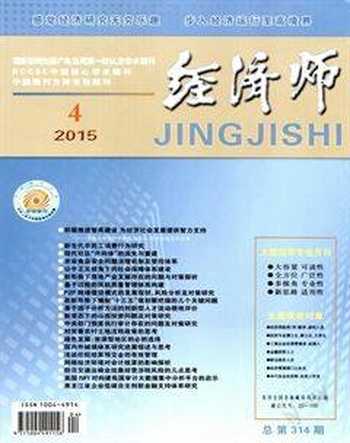國外稅收立法及其權限劃分的比較和啟示
劉軍
摘 要:通過對國外稅收立法及其權限劃分的基本做法,特別是對稅收基本問題的法律規定、稅收立法機關及立法程序的比較,分析了在借鑒西方國家稅收立法經驗時應注意的前提,提出了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充實憲法中有關稅收的內容并制定稅收基本法、盡快完成稅收正式立法的建議。
關鍵詞:稅收 立法 權限 比較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4-085-03
現代國家稅收的重要原則是稅收法定原則,即國家征收賦稅必須要有法律上的根據,稅源、稅種、稅率、征收方式、納稅義務人等均應由法律明確規定。凡不是依法律規定而要求公民履行的納稅義務,公民可以拒絕繳納;同時,除法律有例外規定,任何人不得免除納稅的義務,也不得任意增設或變更納稅的義務。此外,公民還可以對是否依法要求其納稅進行監督。稅收法定原則和罪刑法定原則,是現代國家保障公民權利的兩大手段,稅收法定目的是保障公民財產權,罪刑法定目的是保障公民人身權。中共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決定均強調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現代市場經濟和現代民主政治是人類文明共同的財富,借鑒國外特別是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稅收立法及其權限劃分的基本做法,對于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具有重要積極作用。
一、西方國家稅權劃分的理論基礎與實踐前提
現代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分權制衡理論基礎上的。英國啟蒙思想家洛克在契約論的基礎上,針對“王權神授”“主權在君”的理論,提出了分權學說,即國家的權力應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議會是掌握立法權的機關,政府是行使執行權的機關,對外權與執行權由國王和政府共同行使。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發展了洛克的分權理論,他認為,每個國家有三種權力,即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應分別由三個不同的部門掌握,立法權要實行代議制由人民來行使,行政權應當掌握在國王(政府)手中,司法權則由法院行使;三個部門應當互相牽制,以權力制約權力,從而防止權力的濫用,保障公民的自由。按照洛克、孟德斯鳩等人的理論設計,西方國家根據自己的歷史和實際狀況,形成了以三權分立為特征的政治體制。
與整個政治體制相適應,西方國家在稅收的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中職責范圍清晰,相互聯系、制約,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有效的運行機制。
二、對稅收基本問題的法律規定
關于稅收基本問題的法律規定,一般都在憲法中體現,也有的國家專門制訂了稅收基本法。
納稅是現代國家中公民的基本義務之一,對納稅義務的規定,是各國憲法的通例。最早可追溯到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第十二條對納稅義務的規定:“除下列三項稅金外,設無全國公意許可,將不征收任何免役稅與貢金。”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第十三條規定:“為了武裝力量的維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賦稅就成為必不可少的。”
在規定了公民納稅義務的各國憲法中,有些明確規定了納稅的原則。法國《人權宣言》(1789)第十三條規定:“賦稅應在全體公民之間按其能力作平等分攤。”意大利憲法(1947)第五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所有人均須根據其納稅能力,負擔公共開支。”希臘憲法(1975)第四條第五款規定:“希臘公民無例外地按其收入分擔公共開支。”巴林國憲法(1973)第十五條規定:“征課捐稅必須公平合理”,“法律規定對低收入者免征捐稅以使其能維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菲律賓憲法(1987)第二十八條規定:“稅則統一和公平。”科威特憲法(1962)第四十八條規定:“……為使維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法定收入微少的人免除納稅義務。”土耳其憲法(1982)第七十三條規定:“公平合理地分擔納稅義務是財政政策社會目標。”敘利亞憲法(1973)第十九條規定:“賦稅……,以實現平等和社會正義的原則。”
各國憲法對納稅義務具體內容的規定繁簡不一。多數國家的憲法只作原則性規定,條文的表述也簡明概括,如日本憲法(1946)第三十條規定:“國民有按照法律規定納稅義務。”也有一些國家憲法規定得比較具體,如菲律賓憲法(1987)規定了“累進制稅則”,敘利亞憲法(1973)第十九條規定:“賦稅按衡平法和累進制的原則征課。”比利時憲法規定得更為詳細,“國家稅必須通過立法才能規定。省、城市、市鎮聯合體和市鎮的地方稅,非經各自議會作出決議,不得征收。關于省、市、市鎮聯合體和市鎮可以不遵守上述規定而征收地方稅的例外情況,由法律規定。”“國家稅須每年投票通過。規定國家稅的法律,如不展期,其有效期僅為一年。”“在稅收方面,不得規定特權。免稅或減稅,只能由法律規定。”“除法律明文規定的例外情況,國民只繳納以國家、省、城市、市鎮聯合體或市鎮的名義征收的國家稅和地方稅。”
稅收法定原則在多數國家憲法中得以體現。這淵源于前述英國自由大憲章(1215)第十二條的規定,即“設無全國公民許可,將不征收任何免役稅與貢金。”法國《人權宣言》(1789)第十四條規定:“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由其代表來確定賦稅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認可,注意其用途、決定稅額、稅率、客體、征收方式和時期。”法國1793年憲法第二十條規定:“一切公民均有權協助賦稅的創設,監視其用途和了解其狀況。”日本憲法(1946)第八十四條規定:“新課租稅,或變更現行租稅,必須有法律或法律規定的條件依據。”新加坡憲法(1965)第八十二條規定:“除經法律或根據法律批準者外,不得由新加坡或為新加坡之用,征收任何國家稅和地方稅。”
大多數國家的憲法對納稅的立法權屬都明確規定由議會行使。如美國憲法(1787)第一條規定:“所有征稅議案應首先在眾議院提出,但參議院得像對其他議案一樣提出或同意修正案。”“國會有權課征直接稅、關稅、輸入稅和貨物稅,以償付國債,提供合眾國共同防務和公共福利,但一切關稅、輸入稅和貨物稅應全國統一。”第十六條修正案規定:“國會有權對任何來源的收入,課征所得稅,無須在各州按比例進行分配,也無須考慮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統計數。”法國在1791年憲法中的“賦稅”篇第一條和第四條規定:“賦稅應于每年由立法議會討論并決定之,如非明文規定繼續有效,即不得繼續存在到下一次會期最后一日以后。”“郡行政官及縣行政官不得創設任何賦稅,不得課派立法議會所規定時間和數額以外的賦稅。”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1958年)第三十四條規定,各種性質的賦稅的征收基礎、稅率和征收方式,由議會投票通過的法律加以確定。菲律賓憲法(1987)第二十八條規定:“非經國會會議議員過半數同意,不得通過準予免稅的法律。”
有些國家的憲法在稅收立法上不僅規定了議會與政府的權限劃分,而且規定了中央稅(聯邦稅)與地方稅的立法權限劃分。在議會行使稅收立法權的同時,可以通過委托立法授權政府制定某種稅制,或頒布有關的稅收條例。如瑞典1975年的政府組織法(該法為憲法的組成部分)第九條規定,政府可以根據法律授權以政令的形式頒布關于貨物進出口關稅的條例。菲律賓憲法(1987)第二十八條規定:“國會得立法授權總統在指定范圍內,并遵守國會所規定的限制和約束,制定關稅率、進口和出口限額、船舶的噸稅、碼頭稅以及在政府的全國發展計劃范圍內的其他稅或關稅。”土耳其憲法(1982)第七十三條規定:“得授權內閣根據法律規定的上限和下限,變更有關稅、捐、費和其他財產負擔的減免率和照顧率。”巴基斯坦憲法(1973)不僅將“征收、廢除、豁免、變更或調整任何稅”納入議會的立法程序,而且對“聯邦和各省之間的歲入分配,議會授權征收的所得稅(包括公司稅)、銷售和購買稅、總統規定的國產稅和其他稅、以及省議會或省政府無權制定的稅種”等都加以限制。
還有一些國家采用稅收基本法形式規定國家稅收基本制度,如德國、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和一些中東歐國家等。阿根廷中央與省的稅權劃分由憲法規定,其11683號法律則對納稅人、納稅、限定性條款、征管、納稅程序、罰則等做了一般性規定,起到了稅收基本法的作用。
概括說來,大陸法系國家,包括以法德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國家以及曾是法、西、荷、葡殖民地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在立法上大多采用法典形式,制訂各部門系統完整的法典;而英美法系國家,包括英、美以及曾是英國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一般不傾向于制訂成文法典,制定法大多以單行法律形式出現,這一特點也在稅收立法上體現出來。目前已制訂稅收基本法的國家一般均為大陸法系國家;英美法系國家中一些國家雖有稅收法典形式,如美國歲入法典,但只是法律匯編性質,而不同于系統化的規范性部門法典。
三、稅收立法機關及立法程序
現代國家的立法機關是通過選舉產生的議會。在各國立法機關與行政、司法機關的關系上,即立法機關的地位,從憲法和法律規定中體現出四種類型。
立法優越型。以英國為典型代表。它推崇議會主權原則,主張一切法律原則均由議會制訂;以立法機關為最高權力機關,以立法權為最高統治權,以法律為最高命令。在英國,議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內閣居于從屬地位,高等法院雖對行政機關是獨立的,但必須執行議會決議,受議會監督,貴族院本身即是最高裁判機關。內閣對立法機關雖有解散下院的制約權,但在法律上這一權力尚不足以抵消議會的優越地位。
三機關平列型。多數分權國家屬此種類型,最具代表性者當推美國。立法機關在國家政體中的法律地位與行政及司法機關基本上平行并列,各機關之間存有不同程度的制衡關系。在美國,立法權和財政監督權歸國會享有;總統掌握行政權,無直接立法權,但對國會通過的法案擁有否決權;聯邦最高法院擁有監督立法和解釋憲法的權力,可以通過行使司法審查權宣布總統法令和國會通過的法律違憲無效。
行政優越型。行政機關是國家權力的中心,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處于相對次要的地位。法國屬于此種類型。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1958年)大大強化了行政權,總統有權就一切涉及公共權力組織的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復決,有權要求議會重新審議其最后通過的法案,議會不得拒絕,總統掌握行政權而由內閣代為對國會負責,內閣總理擁有立法創議權,政府有權就法律草案和提案提出修正案,政府提出的法案在國會議程中優先討論。法國憲法在劃分法律事項和行政命令事項的范圍時,使法律事項受到限制,而命令事項卻有相當的自由度;對于命令事項,即使在法律上已有規定的情況下,也可根據總統命令進行修訂或廢除;關于法律事項,政府根據需要,可以要求國會在一定期限內承認根據命令所做出的規定;總統和議員都有法律提案權,但關于財政稅收法案,則不承認議員的提案權和修改權。
立法至上型。瑞士即為此種類型。瑞士憲法規定,作為立法機關的聯邦院和國民院的法律地位高居于行政機關之上,行政機關無條件服從立法機關,立法機關不僅掌有立法權,還有行政權、監督權與裁判權。對于聯邦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行政當局不得否決,法院亦不得宣布其違憲。一般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立法機關的法律地位,基本可劃歸立法至上型。
據對152個國家立法機關的構成統計,采用一院制的國家有107個,采用兩院制的國家有44個,采用三院制的國家只有1個(南非)。聯邦制國家一般采用兩院制,單一制國家既有采用一院制的,也有采用兩院制的。各國的立法程序很不相同,但大體均由行政機關或議員及議會專門委員會提出法案草案,經議會審議通過后,由國家元首簽署、公布。在有的國家中國家元首可以否決議會通過的法案。稅收法案一般由政府中的財政、稅務主管部門擬訂提出,或由議員及議會專門委員會提出。在實行兩院制的國家中,法案必須由兩院都審議通過后方可生效。一般認為,立法機關實行兩院制可以防止立法的草率與武斷,并緩和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沖突。但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實行一院制可以提高立法的效率。
在英美法系國家,判例法是其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官可以判例形式創制法律。
20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以后,世界各國出現了行政權強化、立法權弱化的趨勢,行政機關的地位不斷超乎立法機關之上,這種趨勢已成為當代政治發展主流。主要表現在行政機關的立法提案權擴張,立法機關通過的主要不是議員或議會委員會提出的法案;授權立法(委任立法)在現代立法中比例愈益增多;行政的立法否決權不斷增多等方面。
四、借鑒與啟示
在借鑒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稅收立法、執法、司法及其分工的經驗的時候,應當注意兩個前提。第一,西方國家稅收法治建設的理論基礎與實踐前提是分權制衡學說與三權分立體制;而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均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與三權分立體制具有根本區別。第二,以法的歷史傳統和法結構與法技術的特征為標準,西方各國可分為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我國在2000多年封建社會歷史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法系,20世紀初中華法系解體,民國時期法律制度基本屬于大陸法系,新中國成立后,形成了自己的法律制度體系,與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都有本質差別。
在明確以上兩個前提的同時,應當認識到,西方國家在稅收法治建設方面的做法,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而逐漸完善的,適應并促進了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我們應當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加以借鑒。
(一)充實憲法中有關稅收的內容并制定稅收基本法
我國現行的1982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這僅能說明公民的納稅義務要依據法律產生和履行,并未說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稅主體應依照法律的規定征稅,因而該規定無法全面體現稅收法定原則。所以應在憲法中直接明示稅收法定原則,規定“國家依照法律征稅。”在憲法規定公民納稅義務的同時,在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方面應更加明確,保障納稅人的合法權益。
一些國家對于稅收基本問題在憲法中做出了明確規定,但我國憲法具有集中性、原則性、概括性的特點,不可能將所有稅收基本問題都規定進去。因此,有必要制定稅收基本法,規定我國稅收制度、征管制度等,在整個稅收法律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決定國家全部稅收立法、執法、司法活動,規范政府與納稅人、中央與地方的稅收關系。當然,稅收基本法的規定如果過于原則、概括,則無實際意義;但如對一些敏感問題,特別是中央與地方稅收管理權限劃分等問題作出明確規定,則要以整個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革為前提,在當前尚未取得共識的情況下,在短期內不可能順利擬訂草案并獲通過,對此需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二)盡快完成稅收正式立法
立法法(2000年)第八條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第九條規定:以上“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2015年立法法第八條相關規定修改為:“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第十條增加了授權期限不得超過五年的規定。目前,我國只有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車船稅法和稅收征管法是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通過的,其他的大多數稅法淵源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制定的條例。1985年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制定暫行規定或者條例的決定,成為國務院制定稅收暫行條例的法律依據。由立法機關制訂的法律和授權行政機關制訂的條例,其立法層次、權威性和法律效力有所不同,特別是行政機關制訂條例的立法過程缺乏經濟社會主體的廣泛參與。因此,授權制定稅收條例數量不能過多,必須嚴格限制授權期限。
參考文獻:
[1] 李步云.憲法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
[2] 李林.關于立法權限劃分的理論與實踐.法學研究,1998(5)
[3] 劉磊.論稅收法律主義原則.涉外稅務,1999(1)
[4] 湯貢亮.中國財稅改革與法治研究(第二版).中國稅務出版社,2014
[5] 程雁雷.憲法中納稅義務規定之簡略比較.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5(9)
[6] 李林.西方各國立法機關地位比較探析.寧夏社會科學,1990(6)
(作者單位:首都醫科大學 北京 100069)
(責編:賈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