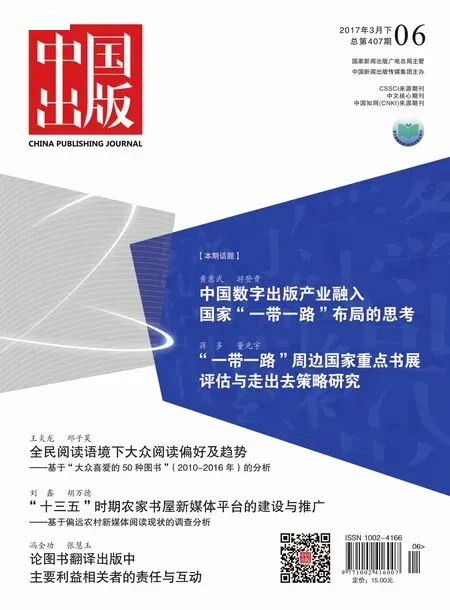把“故事”講好
——漫議營銷視角下的圖畫書閱讀推廣
□文│孫 薔
(作者單位:少年兒童出版社)
德國思想家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一文中遺憾地宣告:“講故事的藝術行將消亡”,因為現代技術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絕,褫奪了人們“交流經驗的能力”。在他看來,“口口相傳的經驗是所有講故事者都從中汲取靈思的源泉”,“講故事人的工作是以實在、實用和獨特的方式塑造經驗的原材料——自己和他人的經驗。”脫胎于1930年代歷史狀況的理論,在當今社會文化語境下仍散發智慧。
筆者認為,本雅明所謂的“講故事的藝術”正為目前出版業的閱讀推廣工作帶來了啟示。特別是圖畫書這種獨特的兒童文學形式,其自身的美學屬性、傳播特點,以及與新媒體時代的技術特征和人們的閱讀、交流、思維方式的變遷相結合,構建出了自成一體的營銷推廣模式。在這里,“口口相傳”得到鼓勵,意見的發表、“經驗”的交流成為可能。“講故事的藝術”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復興。可以說,圖畫書的閱讀推廣,就是要“講故事”。
那么,在現實的推廣活動中,“講故事的藝術”如何體現?“故事”的范疇、講故事的方式、“講故事的人”的身份等問題如何在本雅明的理論框架下得以詮釋,又呈現出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豐富多元?出版從業者的“講故事”活動如何得以展開?本文將基于這些問題展開思考。
一、圖畫書的豐富“故事”性:美學特點決定的多元闡釋空間
圖畫書,又稱繪本,它以圖畫為主,結合文字,共同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兒童文學的樂趣》的作者佩里·諾德曼認為一本圖畫書至少包含三種故事:文字說的故事,圖畫暗示的故事,及兩者結合后產生的故事。而其中,圖畫承擔了主要的敘事與表情達意功能,“無字書”更是將圖畫的功能推向極致。“日本繪本之父”松居直說:“真正的繪本體驗,是孩子在聽別人讀繪本的時候,自己進行的再創造。”這也揭示了圖畫書獨特的審美價值:在文與圖的配合與互動間,蘊含著開放的想象與可解讀空間。
《向日葵》是日本繪本作家和歌山靜子的圖畫書代表作,以簡潔粗壯的線條、高飽和度的色彩和“咚嘟咕咚”的音響效果來呈現,文字和圖畫的大量留白是為讀者留下的想象空間。讀者則生發出了多元的閱讀感受:孩子們被強烈的視覺沖擊和新奇的聲音所吸引,認知了向日葵的生長過程;成人讀到了周而復始的自然規律,讀出了親子關系的微妙變化、生命的循環,感悟了哲思。對于一本圖畫書,每個讀者的心中都有一個與自我經歷、情感相關聯的獨一無二的故事。這些不同的“故事”就促成了人們可交流的“經驗”。
在文化研究學者斯圖亞特·霍爾看來,傳播過程是一種編碼-解碼的“復雜結構”。傳播者“以一個有意義的話語的形式生成已編碼的信息”,而這一信息要通過解碼“產生非常復雜的感知、認知、情感、意識形態或者行為結果。”如果說作家的創作是通過編碼進行的意義生產,那么讀者的閱讀以及閱讀后產生的“結果”,則是一場解碼實踐。而編碼與解碼之間的不對等性、創作與閱讀之間的張力就構成了豐富的“故事”性。
之于圖畫書,讀者的“解碼”還不止于對一本書內容的多元闡釋。各類圖畫書延伸活動如創意美術、創意手工、親子游戲、繪本劇表演、紙偶劇編排、電臺聽書等受到了孩子和家長的歡迎;而圖畫書與幼兒園主題化教學相結合,與小學語文創意讀寫相結合已經成為教學實踐的新亮點。圖畫書的“故事”在更深、更廣的層面上講述。
二、講“故事”給大人聽:面向目標受眾的閱讀推廣
以營銷的視角看圖畫書的閱讀推廣,推廣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銷售。圖畫書是“大人講給孩子聽的書”,具有購買力的成人應該成為閱讀推廣精準的目標受眾。
本雅明認為“講故事者是一個對讀者有所指教的人”,而“指教是對一個剛剛鋪展的故事如何繼續演繹的建議。”其實,圖畫書的閱讀推廣就是通過各種方式的“指教”,講述圖畫書的各種“故事”,使“聽故事的人”——成人讀者,從認識、喜愛圖畫書到購買、閱讀圖畫書,并把自己的“經驗”傳播出去。圖畫書的推廣又可表述為:講“故事”給大人聽。
目前,圖畫書并不必然是大多數父母為孩子首選的親子讀物,甚至親子閱讀的理念尚未成為他們的“共識”。那么,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如何給大人“講故事”呢?也即,如何對他們進行“指教”呢?
1.“講故事”最直接的方式——面對面講述
傳播學家施拉姆認為:傳播效果最好的是面對面的人際傳播。國內學者郭慶光說:“人際傳播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社會交際,同時也是為了交流信息、交換意見和相互影響。”本雅明對“講故事”的口頭傳統極盡褒揚,從傳播學意義上說,口耳相傳就是人際傳播。“講故事”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便是面對面。
“親子故事會”讓家長和孩子一起聽故事,家長自己閱讀到了一個好故事,更感受到了圖畫書給孩子帶來的快樂,對圖畫書的魅力有了感性認識。而要向大人們“講故事”,還有公益閱讀講座、作家見面會及作品分享會、讀書會、沙龍、家長課堂等多種形式。所講述的“故事”則包括:圖畫書理論及閱讀理念,圖畫書中蘊含的豐富“營養元素”、深層次的內涵,圖畫書應該怎么選、怎么讀等關于圖畫書的理性認識。
蒲蒲蘭繪本館的主題故事會已成為業界的“樣板”;面向家長的講座、讀書會、沙龍活動定期開展,培養了讀者的品牌忠誠度;策劃組織的繪本作家宮西達也、小林豐的全國巡回活動也突破了作家簽售這種傳統形式,將讀者見面及簽售會、親子活動、家長講座、專業人士工作坊相結合,為作者活動樹立了“標桿”。
在這里,讀者們與“講故事的人”——活動中的表演者、作家、演講專家等實現了面對面,與通過媒介的轉述相比,更利于情感的共鳴、意見的交流,也更容易被“說中”,被“指教”,從而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
2.“講故事”的新方式——社群傳播
面對面“講故事”是在有限的時間、空間內的講述,“聽故事的人”畢竟有限,而互聯網新媒體則為“講故事”的時空提供了無限拓展的可能。
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說:“媒介即信息”,“任何媒介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以“開放、平等、協作、分享”為精神內核的互聯網,體現出技術形塑價值取向的魅力,傳播的社交性、交流的便捷性得到彰顯。與此同時,當今社會個人日益原子化,社會化新媒體提供的“人際網絡”恰恰與人們渴望交流、尋求認同和精神慰藉的心理機制相遇合。互聯網傳播的重心正向社會化媒體轉移,傳播活動面對的不是個人。人們以“社群”中一員的身份表征自己,社群傳播成為目前閱讀推廣最鮮活的方式。
在新媒體時代,出于對閱讀的關注,對育兒、親子教養的興趣和對現實操作指導的需求,媽媽們集合成了數量龐大的QQ群、微信群,以及自媒體的粉絲群。這也構成了圖畫書閱讀推廣中“聽故事的人”的主體。群分享及信息發布是出版社編輯進行線上推廣的重要手段,加之其成本低、效率高、涉及范圍廣,業已成為重要的日常推廣方式。
在一個個虛擬社區,聽故事的人可以向主講者提問,可以自由發表觀點,可以相互交流意見,而大家的發言都呈現為“可見”,社群內部儼然構成了一個可循環的人際傳播系統,再造了本雅明所謂的“口口相傳”。“故事”在分享者的“指教”和社群成員“經驗交流”的過程中得以傳播和講述。
如果把面對面傳播的閱讀推廣活動視為“線下故事會”,社群傳播則締造了“線上故事會”。二者存在著廣泛的彼此互動與結合,通過線上平臺為線下活動進行信息發布與人員招募;把線下故事會的內容通過線上平臺再次講述,這有利于維護社群關系,增強用戶黏性,也實踐著“O2O”的當代商業模式。
目前,社群傳播的經濟屬性已然凸顯,通過團購、微商城、淘寶店等銷售形式,“故事”講述后是現實購買,其推廣的現實效果遠遠大于線下活動。如:2015年6月中信出版社的《世界上最大的蛋糕》通過童書出版媽媽三川玲、凱叔講故事等第三方垂直社群平臺,以及媽媽類QQ群、微信群,上市一周首印1.2萬冊全部售罄,15天內加印到3.5萬冊,顛覆了出版社傳統的分銷模式。2014年12月正式上線的大V店,定位為媽媽社群電商,已擁有百萬級媽媽精準用戶。推廣上通過線上分享、圖書講座、圖書漂流、微課堂、線下故事會、讀書會等方式拉動圖書銷售。激發起社群分享的營銷潛能,使媽媽們具有了分享者、消費者、分銷商的多重角色,構建了童書推廣與銷售的新模式。
3.尋找“會講故事的人”——意見領袖
三川玲、凱叔是自媒體平臺的建立者和“招牌”,讀者出于信任、對他們所講故事的興趣而成為“粉絲”“聽故事的人”,繼而參與其平臺的各類活動,成為意義和現實經濟層面的消費者。從傳播學角度來說,如三川玲、凱叔這樣的自媒體擁有者便具有了群體傳播中“意見領袖”的特質。“意見領袖”是活躍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觀點或者建議并對他人施加個人影響的人物。他們是傳播過程的關鍵節點,是“會講故事的人”。
目前,閱讀推廣活動以各種豐富多彩的面貌呈現,讀圖畫書、講圖畫書、推廣圖畫書理念的聲音迅速增加。“意見領袖”的構成也更加多元。主要包括:專家學者,作家、畫家、翻譯,出版社編輯,圖書館館長/管理員,繪本館館長,幼兒園、小學教師,民間閱讀推廣人等,而目前火爆的各自媒體平臺創建者大多具有這其中的一種或幾種身份。而縱觀各類媽媽群、公益閱讀推廣群也大多由這些人所創立和運營。
這些“意見領袖”都有各自的社群與圈子、粉絲群和擁躉,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講述著關于圖畫書的各色“故事”。一旦他們的“故事”被“聽故事的人”所認同接受,特別是在社會化媒體上,會造成“病毒式”傳播,受眾“鏈式反應”的口耳相傳也會不斷放大傳播的效果。借助這些“意見領袖”的強大號召力和影響力,通過他們來講述“故事”,是相比于出版社直接發聲的“二次傳播”,它削弱了受眾對于商業機構營銷目的的警惕,也會讓“故事”的講述更加自然優美。
三、不斷積累“經驗”,把“故事”講好
本雅明說:“講故事總是重述故事的藝術”。不論是面對面的“線下故事會”,還是依托于新媒體社群的“線上故事會”,抑或是通過意見領袖“講故事”,“故事”都將會被不斷“重述”。因為“講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的親歷或道聽途說的經驗,然后把這種經驗轉化為聽故事的人的經驗。”所以,故事在不斷被重述中,在人們“經驗”的不斷交流中,將具有無限的開放性。
作為有意識的圖畫書營銷推廣活動,出版社或者說編輯是傳播的起點,應該成為第一個“講故事的人”,并且應通過各種“重述”將“故事”的內容不斷更新,不斷豐富。
1.深挖圖畫書的“故事性”,做有心的“講故事的人”
編輯選擇出版某本圖畫書,既有被故事所打動的個人因素,更有從文圖關系、精神意蘊、藝術風格出發的專業判斷。“講故事”首先就要把關于這本書“如何好”的諸種表達作為素材。而關于作家、畫家介紹,創作背景,如果是引進版則還要關注國外的讀者反饋、媒體報道,說到底是關于這本書的一切細節都應該搜集和積累。此外還有:約請書評、導讀、名家推薦,為讀者提供理解的視角;通過讀者試讀反饋第一手信息;設計一份詳細全面的“閱讀指導”(除卻涵蓋以上內容,在家庭、繪本館或圖書館如何開展親子活動、集體閱讀活動等都可囊括)。策劃一份如何講述這本書“故事”的營銷推廣方案,也將成為編輯需要考慮的。
在這個過程中,以讀者(購買者)的需求為中心的思維方式應該貫穿始終。“推介的不是圖書,而是讀者購買的理由”,把講述的“故事”“轉換、改造成讀者愿意接受、可以接受并有意義的形式”等被廣為認可的營銷法則,也給我們帶來了啟發。
2.連接一切,促進“故事”的“重述”與“經驗”的交流
麥克盧漢所謂“媒介即信息”的精神主旨在于:技術革命帶來的不僅是傳播手段的變革,更是人們感受、認識、思考世界方式的改變。在我們身處的“互聯網+”時代,“連接一切”成為對時代生態的最新表征。人們思維的開放性、分享的熱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張揚,于是,把“故事”講給更多人聽,開展廣泛的與機構、媒介的合作與資源共享,多種“講故事”方式齊頭并進,促進“故事”的“重述”與“經驗”的交流,就成為圖畫書閱讀推廣的現實選擇,也是對“講故事”進程的有意推進。
2015年,北京蒲蒲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簡稱蒲蒲蘭)出品的原創繪本《妖怪山》,通過自己官方微信、大V店、親子閱讀微群和QQ群以及全國巡回作家見面簽售會、落地故事會等多層次逐級擴散,五個月累計銷售4萬冊,打破了蒲蒲蘭十年來原創繪本的銷售紀錄。除此之外,蒲蒲蘭還通過原創繪本論壇、畫展、閱讀沙龍等多種形式繼續推高《妖怪山》的市場熱度。把這個關于《妖怪山》的“故事”不斷更新地講給讀者聽,其后,讀者的故事“重述”則順理成章地鋪展開來。目前在圖畫書推廣領域,各種創新的“講故事”方式屢見不鮮。以至于打破慣性思維的“跨界”合作,如與婦嬰保健院合作親子閱讀推廣講座和新生兒禮包,與各大企業工會合作閱讀推廣親子活動等不斷開拓的新思路都存在著轉化為現實的可能。
3.“聽故事的人”可以轉化為“講故事的人”
在本雅明的意義上,“講故事”是通過口口相傳的人際傳播一代代流傳下去的。在新媒體時代的傳播體系內,讀者既是內容的消費者,又是生產者,是“生產性受眾”。這里的生產不僅指讀者在“聽故事”之后的個人感悟與情感共鳴的意義生產,而且他們積極的意見發表與感受分享,將成為實實在在的“經驗”交流。如:新書試讀活動獲得的讀者反饋、各類故事會中讀者的互動表達、對某一本書的精彩評論,都往往超越“講故事的人”的“經驗”。當讀者把他充滿個性化表達的“經驗”交流出去時,他就成為了新的“講故事的人”,他的“重述”為故事賦予了新的內涵,并為最初的那個“講故事的人”——出版社/編輯帶來新的資源。他們的故事可以被吸納、編織進整個的“故事”大體系之中,為進一步的閱讀推廣提供源源不斷的素材。作為編輯,應該有意識地去發現、積累這些素材,不斷完善自己的“故事”,令“故事”更有厚度。
四、結語
本雅明認為,“故事”如同歷史沉淀的藝術品,講述沒有終點。閱讀推廣這種“講故事”活動同樣如此,它是“故事”內涵的不斷豐富,是眾多“經驗”的不斷疊加,是各種“重述”的相互作用,還是多元講述方式和多種“講故事的人”的彼此聯合,是“故事”的逐漸豐滿與廣為流傳。圖畫書的內在屬性,以及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媒介傳播特點、大眾社會心理、出版業的行業現實交織在一起,在當下,使閱讀推廣活動具備了“講故事的藝術”的特點。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分析、闡釋和解決問題的思想資源,讓我們更深刻地去理解閱讀推廣;而作為出版從業者,探索如何把“故事”講好的意義更在于,激發我們在實實在在的閱讀推廣中不斷去實踐、去創造。
(作者單位:少年兒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