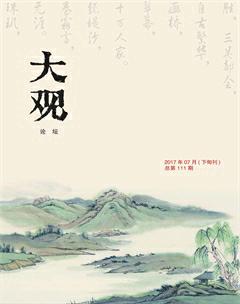淺析古希臘文學中的理性精神
摘要:古希臘是一個崇尚個性主義和理性精神的智慧民族,那個時期的人們思想活躍、宗教信仰自由,文化、道德和人格純正,對于社會和政治、自然和英雄有著大膽而合理的追求。古希臘是一個擁有燦爛文明的海洋民族,獨特的地理環境和資源賦予了他們敢于冒險的精神和奇幻瑰麗的想象。在這樣的環境下形成了激情洶涌、昂揚樂觀的個人主義文化價值觀,并創造出涉及政治、藝術、文學、哲理等豐富而又璀璨的文化,對世界文學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古希臘文學;理性精神;個性主義
希臘是最先以理性為生活主導的民族,他們創建了一個以平等法律服人的城邦制社會。同時希臘人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文主義精神,在文學中表達他們獨特的個性主義和理性精神。由此所形成的早期文學雖與宗教有著密切聯系,主要以神和英雄為描寫中心,但意識超越了宗教和神。里面的神袛卻有著與人一樣的個性,有情欲、有善惡,被稱為人神“同形同性”。古希臘長期生存在土壤貧瘠、丘陵遍布的島嶼,他們天生自由奔放,喜愛冒險,有一種外向開拓的野性精神。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認識水平的提高,古希臘文學逐漸擺脫宗教影響,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文學體系,既擁有史上保存最完好的神話之一,也產生了史詩、戲劇、散文等文學形式并擁有非常高的藝術成就。古希臘神話和史詩與民間口頭文學有著密切的聯系,帶有一種純樸、粗狂的氣息,體現了希臘人崇尚自由的個性主義和與命運斗爭的樂觀精神。后來產生了新的以悲劇、喜劇為主的文學形式,展現了智慧的古希臘民族在面對無奈的命運主宰下理性地生活。而且文學所描繪的英雄,他們熱愛生命、積極地追尋個人價值,與不公的命運抗爭,體現一種個人主義高于一切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
古希臘通過不同的文學形式傳播作品里所表現的人性主義思想和理性精神,表達他對自然、對社會、對人的看法。人文主義在古希臘語中指人和學說,在文學中蘊含著原始形態的“人”,注重人的利益與進步,探索人的世界的同時探求自然世界。在古希臘的社會里,人們的思想超越了神的權威,開始思考人自身的行為,人與社會、自然是什么關系。他們站在自身的立場、理性的高度,思考文學,思考藝術,思考人生,他們認為一切都應該經過觀察,經過質疑,對于思想,不能規定界限,思想高于一切,這種精神深刻地影響了希臘人的文學創作。
在非理性占據著重要作用的原始社會,古希臘民族就崇尚理性,在早期文學就有一種個人主義思想。他們通過想像豐富、富于哲理的希臘神話和規模宏大、內容精彩的荷馬史詩等文學探求事物的終極真理,思考人類與內部社會、外界自然的關系,精密而又充滿熱情地研究一切未知的事物。但是由于認識水平的限制,他們理性的思考并不能回答出一切事物運行的規律,只能歸咎命運。不論是早期的神話和英雄故事,還是后來的喜劇和悲劇,都有一種人與命運在相互矛盾和沖突下產生的悲劇情感。這種悲劇精神源于他們對生命的熱愛、對人生價值和個體意識的追尋,這種情感是人的理性和自然感性永遠處于沖突之中,并沒有任何歸結點的藝術表現,像酒神狄奧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羅之間永無歸結點的運動和碰撞。
在文學作品中,他們一方面舉著“人文主義”的旗幟,高唱著人性解放和自由奔放,超越宗教的意識,主張“人是萬物的尺度”,肯定人的個性和權威。同時另一方面,人應該理性地思考,關注人的倫理和道德,思考人與命運的關系,探索命運奧秘、悲劇地與抗爭命運。在悲劇色彩的影響下,文學作品更注重個人主義的彰顯,展現他們英勇無畏地抗爭,而這種個性彰顯正是古希臘人在認識、征服自然的過程中與命運抗爭的無奈精神體現。人的意識與現實產生矛盾,而一切矛盾、沖突的根源是一個既不依存于人、也不依存于神的因素——命運,命運是不可戰勝的,神也是如此。古希臘文學中貫穿著“人與命運的沖突”,無論神有多么強大的力量,人有怎樣的智慧、高尚的品質,像神話中宙斯和普羅米修斯、史詩中的阿喀琉斯和奧德修斯、悲劇中的阿伽門農,他們都被命運主宰,他們總逃不掉被安排的定命。但他們都有明顯的英雄主義,雖然擺脫不了命運的安排,卻仍理性面對,積極樂觀、不屈不饒地與命運作斗爭,盡展他們的英雄主義與個人價值。古希臘強調人的自由意志和斗爭精神,認為人應該去與命運進行抗爭,不管結果如何,這種抗爭精神正反映了古希臘人們對命運的否定、對神的詛咒和反抗及對自由的向往。這種精神是古希臘留給后人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也向后人昭示了勇敢堅定,蔑視命運的戰斗精神,而且他們能夠充分地實現個人價值。更能征服自然、戰勝自己的命運。
希臘神話更具有“神人同人同性”的特點:神具有人的體魄、弱點、需求,它們不再是高高在上、冷漠無情的神,而是一些極富人情味的生靈,并且自由地混在凡人中間,神被降到了人的地位。取材于神話的悲劇表達的也是一種理性的直覺:主宰人事的是法則而不是神或機會。悲劇中的英雄人物不是一個任命運擺布的犧牲者,他是一個思考著的人。他需要理解自身,分析自己的情感,對自己的行為和決定負責。被西方稱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是以理性眼光看待歷史的第一人。他同以往的神話歷史家最大的不同是他清楚地認識到歷史不是以神為中心的神話傳說,而是一門以人為中心、研究人類活動的科學。在分析希波戰爭中雅典取勝的原因時,他摒棄了神秘主義的解釋,完全歸之于人的因素;希臘軍隊紀律嚴明,作戰勇敢,裝備精良。盡管在希羅多德的作品中有理性思想的萌芽,然而他并不是一個徹底的理性主義者,在他的歷史書中偶而也陷入超自然的解釋,有預兆、神諭、靈驗之類的神定論、宿命論思想。后來的修昔底德在史學思想和史學方法上則遠比希羅多德成熟得多。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學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實態度的史學家。他首先否認神靈參與歷史的說法,將神靈從史書中完全驅趕出去。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從未出現過神靈征兆應驗之類的東西,也未出現神對人類事務的干預,力戒用超自然的力量去解釋歷史,而是用自然原因去說明各種自然現象。這種將人類歷史獨立于神靈之外的歷史觀點,恰恰是建立科學的歷史學的基礎。因此,休謨說:“真正的歷史學是從修昔底德的著作開始的”。至此,希臘史學家確立了以理性為基礎的歷史批判方法,奠定了西方史學的基石。
理性主義是古希臘文化的精髓,它是古希臘對西方文化的重大貢獻,并深深地積淀在西方人的心中,對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歷史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在古希臘時期,人們思考他們能否征服自然、超越宗教和神、戰勝命運,這個思考成為了一代又一代古希臘人思索、探尋、叩問的主題,更成為文學中不可避免的思想。他們將對生活的理性、人的自由、倫理道德寫入文學,將對人性的思考、對神和自然的思考、對命運的抗爭寫入文學,智慧的思考、理性的人文主義思想使古希臘文學在世界古代文學中獨樹一幟。古希臘文學中人文主義成為后來中世紀文藝復興的中心思想,其中的理性精神影響后世的文藝啟蒙運動,古希臘崇尚理性精神、注重以人為本的觀念對后來西方的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
作者簡介:石小卉(1992-),女,蒙古族,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