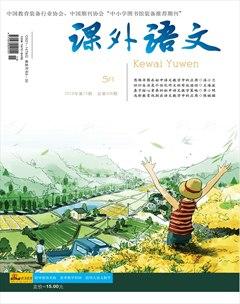創造性使用古詩文教材例談
【摘要】在高中古詩文教學中,創造性地使用教材,多進行比較性閱讀或群文閱讀,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古詩文閱讀興趣,提高學生的古詩文閱讀思考能力;打破凡教照搬教參的教材處理方式,多在文本閱讀中進行邏輯關聯等方面的自主性思考,對學生讀懂古詩文文本、形成自己的思維能力有很大助益。
【關鍵詞】比較性閱讀;群文閱讀;邏輯關聯;自主性思考
【中圖分類號】G633 【文獻標識碼】A
按照教材的編排順序,逐篇逐篇地介紹作者及寫作背景,然后進行語言障礙的處理即字詞句段的翻譯,再然后是文本內容乃至寫作手法的分析講解。一成不變的這種教材處理方式,固然也有一定的教學實效,但總是不能盡如人意。更有甚者,好端端的一個文本不教還可以,一教反而讓學生產生厭倦情緒。這其中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但筆者以為,這與按部就班地使用教材不無關系。既然如此,為什么不轉換一下思維,創造性地盤活并使用教材,讓學生喜讀樂讀并產生自主探究的欲望以增加教學實效呢?
一、打破文本編排順序,多進行比較性閱讀或群文閱讀教學
比較性閱讀是群文閱讀的一種重要形式。群文閱讀是近年來在我國悄然興起的一種具有突破性的閱讀教學實踐。具體地講,即教師和學生圍繞著一個或多個議題選擇一組文章,而后圍繞議題進行閱讀和集體建構直至最終達成共識的過程。它在教材使用上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要根據需要打破教材原有的編排順序,適當地重組教材,讓學生在比較中激發閱讀興趣、產生探究欲望,進而以高級思維的方式尋找到文本內容乃至寫作手法上的異同,這樣有利于提高學生的閱讀思考能力。
比如,《出師表》是初中的經典課文,《陳情表》是高中必修5的經典課文,《祭十二郎文》是高中選修教材《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的經典課文。作為文學史上的經典名篇,三篇課文所寫都感人至深,誠如宋代學者趙與時在《賓退錄》中說的,“讀諸葛孔明《出師表》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亦即被后世所稱的“讀《出師表》不哭者不忠,讀《陳情表》不哭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如果我們在教《祭十二郎文》時,能聯系初中所學的《出師表》、高中必修五所學的《陳情表》進行比較性閱讀,勢必能引起學生產生更強烈的情感共鳴,同時由于忠、孝、慈的不同,也會加深學生對三個文本的閱讀理解,既溫故又知新。
由于不同學段有不同學段的教學任務,以上三個文本的比較性閱讀或群文閱讀,自然應該是在溫故的基礎上才能比較順利地進行。但如果不受學段任務的制約,則不妨大膽嘗試。比如,高中語文必修二第二單元,課文的編排順序依次為:《〈詩經〉兩首》,包括《氓》和《采薇》;《離騷》;《孔雀東南飛》;《詩三首》,包括《涉江采芙蓉》《短歌行》和《歸園田居(其一)》。其中,《氓》《孔雀東南飛》《涉江采芙蓉》均涉及愛情或婚姻題材。把這三首詩放在一起教學,就有許許多多的比較點。比如,三個文本中的男女主人公對待愛情的態度及其表現出來的各自行為哪些是值得贊許的?哪些是可以體諒的?哪些是不能容忍的?三個愛情故事是否都帶有悲劇色彩?如果有,悲劇的深淺度及其造成的原因各有什么不同?……這樣一比較,無疑可以較大限度地點燃學生學習探究的欲望之火,然后加以引導,讓學生在討論交流中自行得出結論。這樣的教學,效果豈不更好?
打破教材編排順序,進行比較性閱讀或群文閱讀可能會受學段任務的制約。但受學段任務的制約有受學段任務制約的處理辦法,不受學段任務制約有不受學段任務制約的處理辦法,終歸會給閱讀教學帶來不一樣的驚喜。
二、打破凡教照搬教參的教材處理習慣,多在文本閱讀中進行邏輯關聯等方面的自主性思考
人教版高中課程標準語文教師教學用書(以下簡稱“教參”)極具權威性,在課文研討、教學建議等方面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但一味依賴教參、凡教照搬教參,教參提到的才講,沒有提到的就不講或不敢講,勢必使古詩文教材的解讀走向狹隘化,不利于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與拓展。相反,如果我們打破凡教依賴教參、死搬教參的教材處理習慣,多注重每個文本內在的各種邏輯關聯的自主性思考,對學生讀懂文本、形成自己的思維能力一定有所幫助。
比如《庖丁解牛》,開頭段是場景描寫,余下三段則是對話描寫。其中文惠君的兩處對話極其精簡,卻關聯起全文的所有內容。第一處對話既關聯起第一段的內容,也關聯起第三段的內容。“嘻,善哉!”是對庖丁解牛情景的由衷贊賞,也是對庖丁精湛技藝的側面烘托。那么,庖丁解牛是否真的如文惠君由衷贊賞的那樣“善哉”?如果以此作為處理教材的切入點進行設問,自然會引起學生閱讀的興趣和探究的欲望,再讓學生回過頭來感知或進一步感知第一段的相關描寫,學生一般也會與文惠君產生同樣的情感共鳴。而“技蓋至此乎?”則是文惠君的發問,庖丁當然要作回答,那么庖丁會怎樣回答呢?這就自然地引出第三段的內容,也會引起學生繼續往下讀的興趣。第二處對話與第三段內容相關聯。文惠君為什么能“得養生焉”,自然是由于庖丁的解牛之道給他帶來的啟發,這就容易引起學生回過頭來對第三段內容進行反復感知,進而達到讀懂文本的目的。如果再把文惠君的兩處對話關聯起來,我們還會看到一位率真、好奇、有求知欲又有很強領悟力的君主形象,這是教參所沒有涉及的。如果再進一步,讓學生聯想想象,也描寫一個屠宰場面,然后與課文相對比,不僅可以加深學生對課文內容的理解,還有助于學生思維能力的拓展性培養。
《庖丁解牛》還有很多關聯點,比如“技經肯綮”與社會矛盾的關聯,“以無厚入有間”與規避或化解社會矛盾的關聯等等。事實證明,在古詩文教材處理中,如果我們敢于打破凡教照搬教參、凡照搬教參必依行文順序逐句逐段分析的習慣,盡量多地把握文本內部的邏輯關聯點并靈活地把它們作為教學的切入點,古詩文的教學效果一定會是另一番模樣。
如何創造性地使用古詩文教材,遠不止以上所述方法。比如對于文本中的不足,敢于提出質疑或批判,盡管教材大都是經典名篇,但畢竟白璧也會有微瑕;對于優秀作品中存在的空 白,不僅僅要引導學生去“填”,還要通過暗示啟發,從空白處引導學生積極地交流、比較、反思、選擇,從而達到培養學生再造形象能力、創造性想象能力的目的。只要能創造性地使用教材,就有可能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進而把學生對古詩文的閱讀引向深入。
作者簡介:劉節約,1963年生,福建南安人,本科學歷,高級職稱,研究方向為高中語文教學。
(編輯:龍賢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