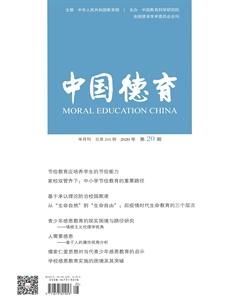基于承認理論防治校園欺凌
摘要 從霍耐特承認理論的角度解釋校園欺凌問題,學生的承認關系因為不當的教養方式和不良的教育環境而遭到破壞,從而產生了被蔑視的心理體驗,這種蔑視體驗促使他們以欺凌弱小的方式表達其渴望被承認的訴求,而這種不恰當的尋求承認的方式又進一步破壞了受害者的承認關系。基于此,防治校園欺凌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創設包容的學校文化,促進對每一個學生的承認;修復受害者的承認關系,最大限度地減輕欺凌帶來的傷害;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尋求承認的渠道,并堅守尋求承認的原則。
關鍵詞 校園欺凌;霍耐特承認理論;為承認而斗爭
作者簡介 劉慶龍,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近年來,校園欺凌問題逐漸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2015年PISA對我國京滬粵蘇四省市的調查顯示,22.5%的中學生在過去一個月里曾多次遭受欺凌,這一比例高于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18.65%)。各級政府部門已經陸續制定相關政策以應對校園欺凌問題,而政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準確地把握了欺凌發生的成因,并對癥下藥。目前,解釋欺凌行為的理論很多,但少有研究對這些理論本身進行梳理。本研究在梳理這些理論的基礎之上,嘗試為校園欺凌問題的討論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一、為什么要用承認理論解釋欺凌問題
根據歐維(Olweus)的定義,欺凌指的是有意地、持續性地對他人身體或心靈造成傷害的行為。本文的校園欺凌指的是發生在中小學生群體中的欺凌行為。目前,學術界針對校園欺凌的理論解釋可大體分為個體的和社會的這兩種取向。
個體取向的欺凌理論主要包括權力的視角和發展心理學的視角。權力的視角即橫向地從學生與他人之間權力關系的角度解釋欺凌行為,其核心觀點是視欺凌的實質為權力主體之間的不對等關系。從權力的視角出發,欺凌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欺凌者希望通過欺凌顯示、保持或提高自己的地位,以確保自己在群體間占優勢的權力關系。發展心理學的視角則縱向地從學生成長軌跡的角度分析欺凌何以發生。在這一理論中,欺凌被視為一種持續穩定的行為傾向,且可以從欺凌者的早期經歷找到源頭。這一取向的缺陷在于只將關注點放在個體身上,而忽視了環境對個體的影響,解釋的力度比較有限。
社會取向的欺凌理論側重于將校園欺凌視為一種社會失范現象加以解釋。“緊張理論”認為,當外界造成的壓力累積到一定程度時,會促使個體產生憤怒和沮喪等負面情緒,排解這些負面情緒的方式可能是對他人實施攻擊性行為。“挫折-攻擊假設”認為,當學生遭遇挫折時會產生焦慮情緒,而欺凌是為了排解這種焦慮情緒的一種心理防御機制。“社會信息加工理論”則認為,學生之所以會實施欺凌行為是因為他們對社會信息的解讀與常人不一致,欺凌只是那些有社交技能缺陷的學生與他人“特殊”的相處方式。社會取向的欺凌理論有助于從整體上把握欺凌問題,但其關注欺凌的社會根源勝過個體的心理動因,導致理論在解釋具體的欺凌事件時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總的來說,個體取向和社會取向的欺凌理論在提供了解釋框架的同時也各有缺陷。要想從更為全面的角度理解欺凌,既需要將欺凌視為一種由某些心理問題導致的個體行為,又需要將欺凌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而霍耐特的“為承認而斗爭”理論(以下簡稱“承認理論”)為欺凌成因兩種取向的整合奠定了基礎。
“承認”最初作為一個社會概念出現在康德的論述中。康德認為人的自由應當建立在承認他人自由的基礎之上,應該“使你的任性的自由應用能夠與任何人根據一個普遍法則的自由共存”。費希特將這一觀點背后的承認意蘊進一步概念化,明確提出將承認當作自由得以可能的先在條件。隨后,黑格爾用承認這一概念解釋社會沖突,他認為人與人之間之所以會發生沖突是因為主體沒有被其他主體所承認,因此必須采用斗爭的方式實現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承認。
霍耐特借用米德的社會心理學理論揭示出“為承認而斗爭”的心理機制,從而讓承認這一概念有了心理層面的含義。霍耐特認為,當人感受到自己不被承認時會產生憤怒、懊惱、沮喪等負面情緒,這些被蔑視的體驗是個體參與斗爭的直接動力。他將承認分為愛、法權和團結三種形式,并將這些形式與個體的心理狀態聯系起來:對愛的承認使人自信,對法權的承認使人自尊,對團結的承認使人自重。如果承認關系被破壞,個體的心理狀態也會受到相應的影響。如此一來,承認概念就具有了社會層面和個體心理層面的雙重屬性。
將承認理論引入校園欺凌問題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可行性在于,欺凌與斗爭可以理解為不同形式的社會沖突,而霍耐特的“為承認而斗爭”正是用來解釋社會沖突的。其核心觀點可總結為:未被承認或未得到足夠的承認是社會沖突發生的根源,斗爭是爭取被承認的基本形式。理論上說,所有的社會沖突,其中包括欺凌問題,都可以從承認理論的角度來解釋。必要性在于,“承認”既是一個社會概念,又是一個心理概念,這種雙重屬性決定了承認理論有可能將欺凌問題的社會視角和個體視角整合在一起,從而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欺凌現象。
二、承認理論下的欺凌本質是什么
一次完整的欺凌事件由欺凌者、受害者以及欺凌行為這三個要素構成,因此分析欺凌問題時也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人手。
(一)欺凌者背后的承認缺失
從承認理論的視角看,欺凌者是一個承認缺失的群體。從某種程度上說,欺凌者的身份是被不良的家庭或學校環境所形塑的。
第一,欺凌者與父母的關系往往是疏離的或對抗的。有研究表明,欺凌者的父母對孩子往往表現出冷漠,拒絕他們的請求。如果青少年在童年時期缺乏父母的關愛,他們在長大以后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出現攻擊性行為。另外,留守兒童的欺凌行為顯著多于非留守兒童。
第二,欺凌者群體普遍缺乏法權意識,這導致他們比其他人更輕易侵犯他人的法權。缺乏法權意識源于欺凌者在其成長過程中沒有感受到足夠的自主權,父母習慣于以獨斷專制的方式管理子女,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可能實施欺凌。
第三,欺凌者往往是其所在團體中被孤立起來的人,是被主流教育價值體系所排斥的那部分學生。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實施欺凌之前就已經被外界貼上了“壞學生”的標簽,產生了消極的自我概念。這種消極的自我概念導致這部分學生比其他學生更可能實施欺凌行為,甚至是欺凌行為最重要的預測因素之一。
(二)受害者遭受的承認破壞
需要澄清的是,欺凌者在其成長歷程中不被承認的經歷并不是為欺凌者開脫的理由,也不能改變欺凌行為本身的惡劣本質。欺凌行為之惡劣性的核心在于傷害了受害者的三類承認關系。
第一,欺凌破壞了受害者愛的承認關系。霍耐特承認理論中的愛指的是主體間相互理解、承認、支持、關懷的關系。黑格爾也曾說過,愛的本質是主體在他者身上獲得了他者對自己的承認,是主體情感需要在他者中的自我實現。對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而言,欺凌者對受害者的嘲諷、侮辱、毆打與愛的承認背道而馳。有研究證明,那些曾被欺凌過的學生往往會產生孤獨、恐懼、被遺棄的感覺,在人際交往中也會存在困難,這些都是愛的承認遭到破壞后的表現。
第二,在欺凌事件中受害者的法權被強制剝奪。欺凌者以一種違背受害者主觀意愿的方式給受害者帶來身體或心理上的傷害,受害者在這一過程中會感覺自己的身體和意志是不獨立、不自由的,是可以被人隨意侮辱和踐踏的,因此其自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更有甚者,他們可能因為被欺凌的經歷而認為自己是失敗的、無能的、不重要的,這些消極的自我認知會使受害者陷入更深的自責中。
第三,欺凌將受害者排除在價值共同體之外,是對受害者個人價值的否認。霍耐特認為,團結的本質是一種因主體彼此對等重視而互相同情不同生活方式的互動關系。受害者往往是群體中的邊緣人,他們在群體中的價值是被忽略或否定的。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那些成績好、受到老師重視的學生不太可能受欺負,而不受老師重視且性格懦弱的學生更可能成為欺凌者瞄準的對象。
(三)欺凌行為是“為承認而斗爭”的異化
從承認理論看,那些不被他者所承認的主體總是要為爭取承認而斗爭。但是問題在于,為什么欺凌者會以欺凌這一形式爭取承認呢?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欺凌之所以成為尋求承認的一種渠道,關鍵在于欺凌行為的某些特征暗合了學生渴望得到承認的心態。第一,雖然欺凌行為可能會給欺凌者帶來來自學校或家庭的懲罰,但同時也可以為他們贏得教師與家長的關注。盡管這是一種負面的關注,但欺凌者反而可能從這樣的關注中得到一種類似報復教師或家長的快感。第二,從權力的角度看,欺凌體現為強者對弱者的傾軋。如果欺凌者在其成長過程中的法權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他們就會通過其他渠道來彌補缺失的權力感,而欺凌中的支配成分恰好滿足了這種心理需求。有研究表明,女孩之間的關系欺凌正是為了爭取一種掌控他人的權力感。第三,由于欺凌者往往被主流教育價值所排斥,他們可能會自發地形成與學校或班級主流價值體系相對抗的小團體。這些小團體內部形成了一種“逃離文化”,以嘲笑、作弄那些努力學習、跟上學校教育運作的學生為樂,并且認為如果自己不能融入這種文化,就不能很好地在班級和學校里生存。
其次需要說明的是,欺凌行為本質上是“為承認而斗爭”發生異化的結果。欺凌者為了彌補被損害的承認關系,采用了一種極端的傷害他人身心健康的方式。其實,中小學生的承認獲得主要依賴于家庭和學校,因此按常理來說,當一個人的承認關系被破壞后,其尋求承認的對象理應直接指向家長或教師。然而現實背景下學生不太可能將消極情緒直接發泄到父母或老師的身上,但他們又不得不為自己的情緒釋放找一個出口,于是斗爭的矛頭就轉向同齡人或更為弱勢的群體,通過欺凌他人得到一種變態而扭曲的心理滿足,欺凌行為成了“為承認而斗爭”的廉價替代品。
最后需要補充的是,本文并不是要在個體承認與欺凌行為這兩者之間建立直接的因果聯系,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欺凌行為的背后必然與學生的某種承認形式被否定有關系,因為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自信、自尊和自重的人會以欺凌他人為樂。在這一點上,有一類被稱為“欺凌-受害者”的角色是很好的例證。這類群體的承認關系在遭遇欺凌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犯,并由此產生了被蔑視的心理體驗。他們通過把自己塑造成新的欺凌者,欺辱比他們更弱小的人,以掩蓋自己曾經被欺凌的事實,試圖彌補由欺凌造成的心理創傷。這再一次說明欺凌的本質是承認結構被破壞的“惡”的延續。
三、基于承認理論,如何防治校園欺凌
承認理論將校園欺凌的本質理解為欺凌者用一種不恰當的尋求承認的方式損害了受害者的承認關系。基于這一理解,本文從欺凌者、受害者以及欺凌行為三方面提出防治建議。
(一)創設包容的學校文化,促進對每一個學生的承認
從我國教育的現實情況看,阻礙學生獲得承認的最主要因素是以學業成績為評價依據的“一刀切”的教育價值取向和鼓勵競爭、缺乏包容的教育文化。在應試教育環境下,成績排名往往與學生的個體價值、人格、權利、受歡迎程度都捆綁在一起,導致成績靠后的學生往往被蔑視或排擠。在競爭文化的影響下,當學生看到他人比自己更優秀的部分時,嫉妒多于欣賞;當學生看到他人不如自己的部分時,嘲笑多于同情;當學生遇到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時,排斥多于包容,導致一部分學生成為群體中的邊緣人,成為潛在的欺凌者或受害者。因此,預防校園欺凌的途徑之一是鼓勵包容與促進個體承認的校園文化,其核心在于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差異化。平等意味著學校和教師要承認與尊重每個學生的獨立人格,不因學生的家庭背景以及生理與性格特征而違背這一原則,尤其是不能將考試成績的意義泛化至對學生其他方面的評價中。差異化則意味著以包容的心態看待學生之間的差異,在不妨礙他人自由與權益的前提下,尊重學生多方面的性格特點、興趣追求、個人志向,讓每個學生都獲得一種被他者所承認的感受,從而減少校園欺凌的發生。
(二)修復對受害者的承認,最大限度地減輕欺凌帶來的傷害
欺凌對受害者的傷害主要體現為對三類承認關系的破壞。因此,學校對欺凌事件中受害者的干預,也應以對其承認關系的修復為核心。一方面,通過恢復受害者的承認可以提升其自信、自尊與自重,這些積極心理資本可以降低受害者再次被欺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學校對受害者的疏導和保護可以減緩受害者因被欺凌而產生的屈辱感、憤怒感和自責感,防止這些負面情緒累積成攻擊他人的動力,降低這些受害者轉化為新的欺凌者的可能性。以學校對受害者干預行動中的參與主體分類,學校至少可以采取以下三類行動修復受害者的承認關系。
第一,學校可以成立相關支持團隊,主動了解受害者的心理健康狀況,為其提供專業的心理咨詢服務。比如,團隊教師可以講述自己在學生時代被欺凌的經歷,使受害者產生共情和被陪伴的感受;也可以讓受害者傾訴被欺凌的經歷,表達對受害者的支持和協助制止欺凌事件再次發生的意愿,給予受害者被關照和支持的安全感。第二,欺凌者是受害者承認關系的直接破壞者,在對受害者的心理修復中,欺凌者也可以成為一種重要的資源。如果學校能夠引導欺凌者自我反思從而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并向受害者道歉,受害者可以獲得被重新承認的心理體驗。這一思路在澳大利亞的反欺凌行動中已得到了廣泛實踐,如組織欺凌者與受害者共同對話并消除分歧、通過受害者的闡述激發欺凌者的同理心,繼而勇于承擔責任并向受害者致歉。美國的一些學校也會在適當的情況下組織欺凌者與受害者會面與反思,以修復因欺凌而受損的人際關系。第三,欺凌事件中旁觀者的冷漠、圍觀,甚至嘲笑也可能給受害者帶來被集體所排斥和拋棄的感覺,只有受害者感受到自己被集體重新接納,才能恢復其健康的承認關系。比如,在芬蘭的“向欺凌抗衡”項目中,教師邀請2~4名在班級有威望的學生鼓勵受害者,為受害者提供幫助。我國的“新教育”實驗也間接證明,通過讓受害者重新融入集體以找回對學校與班級的歸屬感,可以有效防止其再一次遭受欺凌。
(三)豐富尋求承認的渠道,堅守尋求承認的原則
如果將欺凌視為一種錯誤的尋求承認的方式,那么從理論上說,只要為學生提供足夠的尋求承認的渠道,發生校園欺凌的概率自然就會降低。循著這一思路,防治欺凌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為學生提供豐富且適合的有助于其尋求承認的渠道。
一方面,學校可以創設有助于完善學生承認關系的機構和活動,以此作為欺凌的替代品。一部分欺凌行為的動機是意圖顯示自己不被承認的法權或找回自己失落的權力感。為此,學校可以開展能讓學生獲得自主權、體驗自主感的活動,比如賦予學生參與學校管理和班級管理的機會,鼓勵學生在學校和班級公共事務中表達自己的聲音。還有一部分欺凌行為可能是欺凌者對其負面情緒的一種發泄,針對這部分潛在的欺凌者,學校要設立專業的心理咨詢服務機構,讓這部分學生能夠及時處理超出自己能力范圍的情緒難題。
另一方面,無論學生選擇怎樣的渠道爭取承認,這些渠道必須遵循一條原則,即不能妨害他人的承認關系,否則就成了欺凌的變體,因此學校教育需要培養學生對他者承認關系的尊重。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讓學生形成完整的法權概念。對法權的承認總是包含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一是在法權之內學生是自由的,即可以做什么;二是法權的邊界在于不傷害他人,即不能做什么。為了讓學生對這一點有清晰的認識,學校可從三個層面做起:第一,通過觀看欺凌視頻、模擬相關情景等方式激發學生的同理心,使其感受到受害者的消極心理體驗,從而在情感上抗拒欺凌;第二,通過對欺凌者的懲罰措施使學生明白如果侵犯了他者的法權,自己的法權也不能得到承認;第三,從規章制度的層面保障每一個學生的法權,并通過營造民主透明的校園環境和友好完善的舉報機制,為受害者提供便于求助的窗口,防止其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將欺凌問題擴大化。
責任編輯 何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