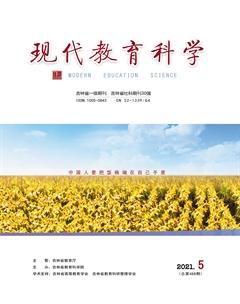我國就近入學政策的價值取向、失真與回歸
蘇海 蒲大勇



[摘 要]“就近入學”是我國義務教育的一項重要政策,其基本價值取向在于促進教育公平。片面追求政策落實導致學校布局不合理、經濟成為就近入學的決定因素、加速社會階層結構分化和固化、違反教育規律的“反向不公正”是就近入學政策價值失真的現實表現。要實現就近入學政策的價值回歸,促進義務教育走向公平,需要采取“弱勢補償”措施,鼓勵學校特色發展,完善“就近入學”政策,建構“二元化”監督機制。
[關鍵詞]就近入學;政策;價值失真;教育公平
[中圖分類號]G6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21)05-0091-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5.015
“就近入學”是我國義務教育的一項重要政策,對保障義務教育的順利實施和教育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把促進教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2014年教育部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小學升入初中免試就近入學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學校劃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學”,基本實現了教育機會公平。但是,現階段人民群眾對教育的需求已經從“機會公平”轉向“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因此,本文通過對就近入學政策的文本分析重申其價值取向,找出價值失真的現實偏差,進而從現實偏差出發提出就近入學政策,實現其價值追求的回歸路徑,使就近入學政策更加完善,促進義務教育由“形式公平”走向“實質公平”。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近入學”政策價值取向的歷史演繹
(一)歷史演進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勝利召開,標志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全面的撥亂反正,為了解決“上學難”的問題,全面提高國民素質,大力實施九年義務普及教育,“就近入學”政策開始在各種政策法規中出現。隨著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口的不斷發展,針對不同國情,“就近入學”政策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側重點,在保障義務教育公平發展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雙軌并行階段(1978-1992):提供充足教育機會。改革開放初期,世界上已有156個國家和地區實行義務教育,經濟發達的國家不僅已經普及了小學教育,而且開始普及中等教育[1]。而我國還在大量產生新文盲,小學入學率雖然在形式上有90%以上,但是真正小學畢業的只有30%。一方面,我國義務教育發展嚴重落后,全國范圍內還存在著“上學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各類知識型的專業人才奇缺。為了提高國民素質,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國家頒發了一系列政策法規(見表1),對義務教育采用“兩手抓”,即重點中學政策和“就近入學”政策同時進行,既通過建立示范學校、重點學校為國家培養優質人才,帶動全國教育發展,又保障義務教育階段人人享受平等教育機會的權利,努力為廣大人民提供充足的教育機會。
2.規范入學秩序階段(1993-2000年):治理擇校熱。在“重點中學”和城鄉二元結構政策的影響下,義務教育的教育資源向“重點學校”和城市聚集,引發了區域、城鄉和校際間教育水平差距擴大的不平衡現象。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2]。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階層分化嚴重,進而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加劇,出現了“以錢擇校”和“以權擇校”的現象。為了治理“擇校熱”問題,國家頒布的一系列文件中強調義務教育階段必須嚴格遵守“就近入學”政策(見表2)。這一時期就近入學政策成為規范入學秩序,推進義務教育機會公平的重要手段。
3.資源均衡配置階段(2001年至今):促進教育公平。我國義務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取得矚目的成就,解決了“上學難”問題,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實現了質的飛躍。但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導致區域、城鄉和校際之間義務教育嚴重失衡,而21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教育是獲得成功的必要途徑。義務教育屬于國家公共資源,因此,追求教育公平、資源均衡配置是義務教育的時代熱點。國家頒布了一系列文件(見表3),投入了大量經費,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通過“就近入學”政策,把現有資源的空間分配格局進行合理配置,是走向教育資源合理配置和教育公平的有力保障。
(二)價值取向
“就近入學”政策作為義務教育政策的重要部分,其價值取向直接影響義務教育的辦學性質、發展方向以及社會公正程度。教育政策的價值選擇是教育政策主體和利益主體在自身價值判斷的基礎上所做出的集體選擇[3]。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近入學”政策的價值分析,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不斷發展,“就近入學”政策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大力推進九年義務教育,解決“上學難”的問題,“就近入學”政策旨在提供充足的教育機會,保障適齡兒童上學機會公平;20世紀90年代,社會上利用錢、權爭奪優質教育資源的不正之風愈演愈烈,“就近入學”政策旨在規范入學秩序,治理擇校問題;2001年至今,經過長期發展,義務教育已經形成了城鄉、區域和校際教育質量差距懸殊的不均衡現象,在“就近入學”政策下,以免試就近入學代替了應試升學,緩解學生的學業負擔,各所學校均可以招收到同等質量的生源,激發各個學校辦學熱情。辦好每一所學校,就近入學的核心訴求明確指向教育公平。從我國“就近入學”政策三個階段的價值取向來看,雖然每個階段的側重點不同,但都是圍繞著促進教育公平這個根本出發點來制定的。
二、就近入學政策的價值失真表征
改革開放以來,在適齡兒童“上學難”的歷史背景下,“就近入學”政策在推進普及義務教育的進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保障了適齡兒童上學機會公平的權利。但是,現階段義務教育實現了所有適齡兒童上學機會充足的基本公平之后,人們的教育需求從“有學上”轉向“上好學”。“就近入學”政策強制適齡兒童劃定學區入學,而現實是教育資源特別是教師資源分布不均衡,校際、城鄉、區域教育質量差距較大,“就近入學”政策價值失真限制了人們自由選擇優質教育資源的正當權利,加大了義務教育的不公平。
(一)片面追求政策落實導致學校布局不合理
通過對“就近入學”政策的歷史演進進行分析,很容易發現其價值追求存在著潛在的內在邏輯,即學校合理布局—就近入學—平等接受義務教育[4]。很顯然,“就近入學”政策的初衷是在學校合理布局的基礎之上遵循“就近入學”原則,從而達到義務教育的實質性公平。學校合理布局是必要前提,“就近入學”是實施手段,公平接受義務教育是最終目的。當學校合理布局之后,學校教育質量相對均衡,在每個學校均能接受優質教育,學生家長對于擇校的目的將不再是對優質教育資源的獲取,而是對學生的個性化需求。但是在執行過程中片面追求政策落實而忽略了學校的合理布局,把原本是實施手段的“就近入學”政策直接作為最終目的來進行落實,最終結果就是“就近入學”政策的落實較好,而學校布局不合理,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從而產生“就近入學”政策的落實與學生家長對優質教育資源的追求之間的矛盾,加劇了義務教育的不公平。
(二)經濟成為就近入學的決定因素
現階段,我國“就近入學”政策的大力推進源于我國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區域、城鄉、校際間的教育質量相差較大。民眾的擇校觀不是對教育個性化和多樣化的需求,而是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以權擇校”和“以錢擇校”的“暗箱操作”加劇了教育的不公平,在以錢、權、分數擇校為主流方式之中,出現了學校“以權招生”和“以錢招生”的畸形現象。有錢、有權的家庭可以選擇去優質學校接受好的教育,而無錢無權的家庭只能去相對薄弱的學校。在知識經濟時代,教育是很多貧困家庭走上主流社會的通道,因此,為了阻斷貧困代際相傳,促進教育相對公平是必然選擇。“就近入學”政策的大力實施從表面上打破了以“錢權擇校”的暗箱操作,但是卻成就了“以房擇校”,近年來優質學校的學區房“熱”,只有有錢有權的家庭承擔得起。把“錢權擇校”的“暗箱操作”轉變為實質上的“明面操縱”,普通家庭望而卻步。“錢、權、分”擇校背景下貧困家庭的學生還可以通過優異成績進入優質學校接受良好教育,而“就近入學”政策把貧困家庭學生阻擋在優質學校圍墻之外。國家應當保障所有孩子都有機會獲得成功,首先決定他們成功的應該是自身才華和努力程度,而不是讓經濟成為獲得優質教育資源的決定因素。
(三)就近入學政策成為社會階層結構分化和固化的“催化劑”
我國教育資源分布的實際情況是社會階層越高的社區配套的學校越好,相應的教育質量越好。同時,學校在空間區域的層級化分布促進著社會相應層級的同質性聚集[5]。優質學校所在的社區往往吸引著中上層群體的聚集,而導致下層群體被迫擠出,薄弱學校所在的社區往往沒有吸引力,下層群體主動涌入。在“就近入學”政策下出身在底層家庭的學生由于家庭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讓他們去優質學校或者跨學區就讀,導致他們只能按照“就近入學”去薄弱學校接受弱質的教育。在知識經濟時代背景下底層家庭本身在知識資本方面就比較缺乏,學生在學校和家庭均得不到優質教育,根本無法和接受優質教育的中上層家庭的學生進行競爭,底層家庭的學生在通過教育涌入上層社會的軌道之前就已經被淘汰。由此可見,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本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不正常現象,而國家通過“就近入學”政策來強迫不同階層的學生到相應質量的學校接受教育,迫使底層群體被“二次剝削”。通過教育使社會階層結構固化,導致底層階級仍然處于社會底層,“就近入學”政策在實施過程中起著底層階級再生產的功能,對社會階級分化和固化起著“催化劑”的作用。
(四)“就近入學”政策造成違反教育規律的“反向不公正”
“就近入學”政策要求所有適齡兒童劃片入學,根據統一標準入學表面上看起來很公平,實則從教育發展規律的角度來看卻暗含“反向不公正”[6]。“就近入學”政策忽視了教育的因材施教原則,忽視了適齡兒童自身多樣性發展的需求,而是按照與兒童自身發展狀況無關的住房就近入學。一方面,對優質學生而言,按照“就近入學”政策進入薄弱學校學習,學生所接受的學習內容、難度、進度和環境等都不太適應其本身的發展,不利于自身的成才。另一方面,對基礎薄弱的學生而言,按照“就近入學”政策進入優質學校學習,學生很難跟上教師教學的進度、掌握學習內容,從而產生厭學情緒,不利于其身心健康發展。總之,不同學生在自身基礎、興趣、特長等方面有著多樣化的需求,同時不同學校有著不同的特色和文化,學生需要選擇適合自身實際的教育才能達到最好的發展。因此,“就近入學”政策“一刀切”阻礙了學生對自身發展的正當追求,不能滿足學生的多樣化需求和個性化發展。
三、多措并舉讓“就近入學”政策回歸教育公平
(一)采取“弱勢補償”措施,促進教育資源均衡分配
根據羅爾斯的公平正義原則,“社會價值都應該被平等的分配,不能平等分配的利用差別原則向最少受惠者提供最大利益”[7],那么國家應當采取措施對“弱勢階層”及時給予補助和救濟。這里所指的“弱勢階層”包括兩部分,即薄弱學校和底層學生。一方面,國家通過政策實施向薄弱學校傾斜,加速薄弱學校發展,促進義務教育學校教育質量均衡分布。要加大薄弱學校的財政支持,給予薄弱學校在教師隊伍、教學教研、培訓交流等軟件設施和教學設備、教育資源、多媒體等硬件設施建設的財政保障;要合理規劃學區學校布局,以學區教育質量均衡為標準進行多校劃區,規劃學區內學校在數量和質量上的相對均衡,即按照“就近”原則進行重新劃分,在偏遠且弱質學區通過建名校分校的方式,保證每個學區均有優質學校;要實行教師區域流動,在每個學區教育質量均衡的前提下實行教師“無校籍管理”,教師屬于“學區人”,不設重點學校、重點班,擴大名校和名師的雙重輻射,促進薄弱學校及其教師優質發展。另一方面,底層學生獲得的教育資源和機會相對較少,為保證底層學生中的優秀學生能夠得到相應的優質教育,可以通過劃定學區優質學校名額的方式,給予優秀學生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保障他們能夠得到高質量發展。
(二)促進義務教育質量均衡,鼓勵學校特色發展
義務教育質量均衡發展是“就近入學”政策實施的必要前提,解決區域、城鄉和校際間教育質量不均衡,才是解決擇校問題的根本措施,才能滿足學生家長對優質教育的需求。而教育質量均衡問題實則是師資配置均衡的問題。《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統籌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實行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和校長教師交換輪流,不設重點學校重點班,破解擇校難題[8]。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實施校長、教師輪崗交流,優質學校的校長到薄弱學校輪崗任職至少兩屆,優質學校的骨干教師到薄弱學校任教至少3年以上,薄弱學校的教師同比例到優質學校學習交流。特別說明的是,義務教育學校均衡發展并非“同質性”發展,如果所有學校朝著同一個方向發展仍然滿足不了學生家長對教育的多樣化需求,教育部門應當重視學校的多樣性發展,鼓勵學校特色發展。學校可以根據自身優勢,由資深優質教師作為“學科帶頭人”組建學科性質的教研組進行校本研發,形成學校特色優勢學科,吸引對這方面有需求的學生來校就讀,理性的、科學的引導學生家長的擇校觀。
(三)以學生發展為核心,“科學入學”保障教育質量
學校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就近入學”政策的價值取向是教育公平,那么作為公共資源的義務教育更是應當以學生發展為核心,保證所有適齡兒童都能夠接受優質的教育,而不應該是本著完成“就近入學”這項工作的目的進行。這里所指的優質教育是指適合學生個性化發展的教育。那么,適齡兒童應該去怎樣的學校接受怎樣的教育才是優質教育?教育部門應當重視這個問題,并且采取“科學入學”的方式保障學生接受公平而優質的學校教育。地方教育部門可以成立“學生校籍規劃部門”,在學校開學半年前對所有適齡兒童的學習習慣、興趣、基礎、天賦、特長等進行測試和深入研究,建立學生的個人檔案袋,根據學生實際情況在學區內科學選擇適合其本身發展的學校就讀。如果學區內沒有適合的學校,在以“適應性原則”進行擇校的前提下,保證“就近入學”原則。這樣不僅可以為學生提供適合本身個性化發展的學校教育,也滿足了為學生提供方便、安全的“就近入學”政策的要求。
(四)完善“就近入學”政策,建構“二元化”監督機制
為了加強“就近入學”政策的可行性與科學性,應當完善“就近入學”的實施細則。首先,由于我國區域差別較大,“就近入學”政策不能“一刀切”,應該對“特殊學區”實行照顧政策,而“特殊學區”必須要經過教育部門的考察是否真正需要照顧政策。比如,邊緣地帶學校教育質量非常低,可以允許優秀學生申請去其他優質學區入學,遵循自愿原則和“相對就近原則”;對其他學區加大實施力度,不搞“曖昧”關系,保障所有適齡兒童公平入學的權利。其次,對“就近入學”政策中“就近”和“以戶籍所在地”這兩個概念進行明確界定,避免因為標準模糊造成“鉆空子”的不公平現象。最后,應當強化監督機制,建立獎懲機制。在“就近入學”政策實施過程中實行教育部門內部監督,社會、學校、家長、學生等外部監督的“二元化”監督機制,把學區是否合理布局和入學的公開、公平、公正作為考察重點,對積極響應并且規劃布局合理的學區進行獎勵,對不合規范的學校給予處罰。堅決按照規定落實“就近入學”政策,回歸義務教育階段“就近入學”政策對教育公平的價值訴求。
參考文獻:
[1]張健.認真研究適合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的教育計劃和教育體制[J].人民教育,1980(08):15-19.
[2]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J].求是,2004(19):3-13.
[3]劉復興.教育政策的價值分析[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
[4]劉國華.“就近入學”政策的認識誤區及未來走向[J].教學與管理,2019(06):24-26.
[5]李濤.中國教育公平亟待深度范式轉型——“就近入學”政策背后的社會學觀察[J].教育發展研究,2015(06):10-13+57.
[6]寧本濤.“就近入學”政策實施的產權困境及改進策略[J].基礎教育,2017(06):39-44.
[7]李東宏,榮利穎.“就近入學”政策中的補償平等研究[J].教學與管理,2016(30):43-46.
[8]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3-11-16.
(責任編輯:勞麗麗)
The Value Orientation, Distortion and Return of the Policy of Nearby Enrollment in China
SU Hai1, PU Dayong2
(1 Chengd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Industry, Chengdu, Sichuan 610218, China;
2? Education Science Laboratory in Jialing District of Nanchong city, Nanchong, Sichuan 637500, China)
Abstract: “Nearby Enrollment” is an important policy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ts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i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equity. One sided pursui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leads to unreasonable school layout, economy becomes the decisive factor of nearby enrollment, accelerate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of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 and violates the “reverse injustice” of educational law, which is the realistic manifestation of the value distortion of nearby enrollment polic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eturn of the value of the nearby enrollment policy and promote the fairnes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we need to take “weak compensation” measures,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characteristics, improve the “Nearby Enrollment” policy and construct “dualiz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Key words:? Nearby Enrollment; policy; value distortion; education equity
[收稿日期]2021-03-19
[基金項目]全國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2016年度國家一般課題“西部農村特崗教師發展狀況和生態機制研究”(項目編號:BGA160033);四川省教育廳資助金重點課題“新時代鄉村教師專業發展生態機制研究”(項目編號:川教函〔2019〕514號);四川省教育廳資助金重大課題“教育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狀況和保障機制研究”(項目編號:川教函〔2018〕495號);四川省教師教育研究中心課題“雙師型教師評價體系構建研究”(項目編號:TER2018-035)。
[作者簡介]蘇海(1995-),男,四川南充人,碩士,成都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建筑工程學院輔導員;主要研究方向:教師教育、中小學教師發展。
蒲大勇(1974-),男,四川南充人,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區教育科學研究室主任,中小學正高級教師(三級);主要研究方向: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