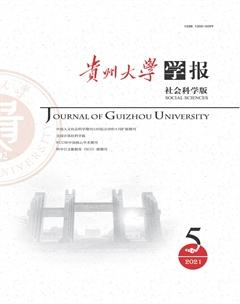元宇宙中的“孤兒們”?
摘要:關于游戲和學習之間的關系,向來存在著兩個針鋒相對的立場。大眾輿論對游戲的負面效應口誅筆伐,但新興的游戲化學習潮流又將游戲奉為學習的真正未來。本文不擬對二者進行倉促的論斷,而是首先試圖回歸哲學史上對于游戲的精神性界定,再由此反思、衡量游戲化學習的利弊得失。游戲化雖然全方位提升了學習的環境和體驗,但“重外而輕內”這個根本癥結使得它無法真正實現李普曼所追尋的兒童哲學的終極理念,也即引導孩子們對自身的生存意義進行主動積極的探尋。元宇宙的到來似乎實現了這一變革的契機。一方面,它極大地克服了游戲化平臺的種種缺陷,進而將哲學化生存和游戲化學習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真正敞開了以一種哲學為核心來重構教育的可能途徑。但另一方面,元宇宙又并非完美無缺;正相反,升級的監控、人的全面數據化,乃至“媒介被動性”的不平等狀態,這些都是擺在未來兒童哲學教育者面前的問題和挑戰。
關鍵詞:精神; 游戲化; 元宇宙; 兒童哲學; 敘事
中圖分類號:B-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21)05-0021-09
柏拉圖(Plato)在《法律篇》中鄭重其事地指出,“我認為,對于嚴肅的事情應當保持嚴肅的態度,…… 那么,我們正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一個人應當在‘游戲中度過一生……我們撫養的那些孩子也必須本著同樣的精神開始”[1]。顯然,在哲學王的眼中,游戲并非是無足輕重、瑣屑無聊的,反倒對于人類的生活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認真對待游戲,也就是認真對待生活。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游戲(Paidia)由此就與兒童的教育(Paideia)產生了本質而密切的關系[2]。那么,為何晚近以來,對電子游戲的批判聲總是不絕于耳,甚至其中不乏頗有建樹的哲學大家呢(比如法國的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如今的電子游戲其實徒有游戲之名,而全然喪失了“精神”這個理應具有的追求。借用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經典概括:“游戲給不完美的世界和混亂的生活帶來一種暫時的、有局限性的完美。游戲要求一種絕對而至上的秩序。”[3]由此看來,當托波(Greg Toppo)和保羅·吉(James Paul Gee)這樣的學者大力鼓吹游戲化(Gamification)作為未來學習的終極平臺之時,他們大概也忽視乃至無視了“學習”本身的精神向度。那就讓我們由此入手,進而展開對游戲和學習(尤其哲學學習)的深入思辨。
一、元宇宙(Metaverse)與兒童哲學的本意
學習關乎的是“精神”,而并非僅僅是“智力”或“智能”。何謂精神?借用黑格爾(G.W.F.Hegel)在《精神現象學》里的經典概括,那正是“全人類行動的一個不可動搖和不可瓦解的根據和出發點,是全人類的目的和目標,是全部自我意識的處于思想中的自在體”[4]。由此,我們可以清晰概括出精神的三個特性:第一,它是一個自我反思、自我發現、自我實現的運動;第二,這個運動的最本質環節和紐帶正是思想;第三,由此最終實現的是人類的共同體。因此,學習的基本方法是理性思考,學習的基本途徑是精神成長,而學習的基本宗旨則是個體之間的精神互通。
而游戲化學習不僅不符合這個精神的定義,更是時時處處與之相忤逆。游戲化的基本方法絕非理性思考,而只是更靈活開放地遵守、利用規則;游戲化的進程也談不上有什么精神的成長和成熟,而只能說是技藝的不斷純熟而已。因而,即便游戲化能實現孩子們之間的某種精神維系,那也是極為脆弱而短暫的,甚至可以說只是隨聚隨散的群落而已:“網絡的數字居民并不聚集……他們組成的是一個‘匯集而不聚集的特殊形式,……沒有靈魂,亦無思想。”[5]但元宇宙,“虛擬世界”(Virtual Worlds)或“3D互聯網”(Web 3D)的出現似乎正在深刻改變數字群聚的格局。首先,元宇宙不再僅是現實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日益演變成一個龐大的平行獨立的世界,甚至進而將現實世界吞并于自身之中。由此看來,它確實展現出一個從“實在世界”向“虛擬世界”的明確轉化的方向和目的,而這同樣也是人的精神本身的一個根本、徹底的轉變過程。雖然這個過程未必就是黑格爾所謂的精神回歸自身的運動,但至少包含著這樣一種可能,無論此種可能性是怎樣的微弱,它總是值得人類付出努力去追求、去實現。其次,元宇宙因為它的巨大的開放性、多元性、復雜性,也就使得其中的“公民”們不能僅滿足于遵守規則,而往往更需要動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來創造新的規則。元宇宙不是現有世界的簡單拓展或復制;相反,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全新世界,包含著無邊無際的難以想象的可能性,因而也就為人類思想的自由創造敞開了巨大的空間[6]113。 同樣,元宇宙也為個體之間的凝聚提供了切實的紐帶和平臺,因為它那巧奪天工的3D技術得以讓所有個體體驗到無比真實而強烈的沉浸感和在場感。
最后這一點也正是元宇宙的真正的變革性意義所在。根據朱利安·倫巴第(Julian Lombardi)和瑪麗蓮·倫巴第(Marilyn Lombardi)的清晰梳理,大致可以將互聯網的發展概括為三個階段。首先是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它有著涇渭分明的邊界和“成員獨享”(Members-only)[6]116的封閉性。而到了互聯網(Web)這第二個階段,雖然已經盡最大可能地實現了用戶之間的開放多元的連接,進而展現出更為豐富而動態的視聽要素,但仍然還存在著一個難以克服的缺陷,即網頁本身畢竟還是一個二維的、平面的介質,這就使得它始終無法完全真實地還原現實世界中的在場體驗。元宇宙的出現顯然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它具有了空前“提升的視覺化和擬真能力”[6]114,由此它能夠制造出“宛若眼前”“活靈活現”的在場體驗。我們在元宇宙中所體驗到的并非僅僅是視覺的圖像或各種符號化的表征(文字符號、情感符號、動作符號等),而就是和我們同在一個三維空間之中的“共同在場”的個體(Contextualized Copresence)[6]114。簡言之,人和人之間不再是隔著屏幕,彼此通過平面網頁相互傳遞想法和情感;如今,在元宇宙之中,我們彼此之間抽去了所有的界面和中間環節,還原到了日常生活里的初始、基本的狀態,那正是面對面的直接對話和互動。我們并不只是在傳遞信息,而是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真實、直接地作用著、改變著周圍的環境[6]119。 一句話,如果說互聯網還只是嵌入現實世界之中的溝通工具,那么元宇宙簡直就確乎越來越接近于一個真實、完整的“宇宙”了。我們“用”互聯網來“做”各種各樣的事情,但我們是“在”元宇宙“之中”做各種各樣的事情。這是一個明顯的巨大變革,對此理應進行深入的考察和反思。
元宇宙雖然也存在著顯見的技術瓶頸(比如服務器成本、資源耗用等)[6]119-120,但它絕對是朝向未來的一個雖非唯一但卻主導的趨勢。它正在波及整個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就學習和教育這個本文所關注的主題而言,它也對方興未艾的游戲化學習進行了實質性的拓展和提升,尤其是極大地補充和增強了“精神”這個其向來薄弱乃至缺失的重要環節。這就明確引向了“兒童哲學的教與學”這個下文亟待展開的核心主題。
歸根結底,進入元宇宙的階段之后,游戲化及游戲化學習所發生的一個最為根本的轉變正是從“娛樂”(Entertainment)轉向“嚴肅”(Serious)[7],從心流(Flow)的體驗轉向精神的歷練。固然,元宇宙的起點和基準平臺毫無疑問就是電子游戲,甚至絕大多數學者都會將元宇宙創生的元年直接明確地指向《第二人生》(Second Life)這部影響至巨的游戲。然而,簡單地就將元宇宙視作是既有的電子游戲的某種拓展和衍生形式,這顯然是表面甚至膚淺的見解。從根本上說,元宇宙脫胎于電子游戲,但又反過來對游戲本身進行著脫胎換骨式的改造。元宇宙中的游戲,從形態、功能、方法、目的等各個方面都在、都將發生著翻天覆地式的變化,變得越來越“嚴肅”,越來越具有思想性和精神性。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曾說,除了娛樂之外,電子游戲本就可以(且已經)在生活之中“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而康查克(Lars Konzack)則進一步強調,“做哲學”就是電子游戲能做的一件相當嚴肅和重要的事情[8]33-34。進入元宇宙階段之后,游戲化作為“哲學實驗”越來越展現出其前所未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甚至可以說,做哲學是出生、成長于元宇宙中的作為“原住民”的孩子們的最基本的學習方式、生存方式,乃至精神成長的方式。
做出如此極端大膽的“假設”,當然還要給出扎實細致的“求證”。所幸的是,即便康查克所倡導和暢想的“哲學性游戲設計”目前仍處于草創的階段,但就兒童哲學這個領域而言,哲學與兒童乃至整個教育體系之間的本質性關系早已被先行者、奠基人馬修·李普曼(Matthew Lipman)所明確強調。針對當下的教育系統所存在的種種明顯弊端,他不僅倡導通過引入哲學這個重要環節來進行修正,更是明確提出了“哲學探索作為教育范式”(the Model of Education)[9]15這個核心理念。“范式”(Model)這個關鍵詞就提示我們,哲學并非僅僅是現行教育系統中的一個缺環,如果只是這樣的話,那么只要增加一些哲學類的課程也就足矣。正相反,李普曼的論點看似要極端得多,他甚至認為要以哲學為核心和“原型”來對整個教育機制進行全面的重構。這當然會引人質疑。在高等教育之中,強調哲學學科的基礎和核心地位或許還可以理解,但在初等教育甚至學齡前階段,真的有必要引入哲學這么“高深晦澀”的思辨來“干擾”兒童的正常的心靈成長嗎?比如,皮亞杰(Jean Piaget)就曾明確指出,10到12歲以下的兒童根本沒有進行理性思考的能力[10]。只不過,他的這個論斷至少存在兩個明顯缺陷。首先是低估了理性思考的復雜性,即僅將其限定于某些既定的模式和規律,而沒有看到理性思考本身就具有相當程度的開放性和靈活性。進行合乎邏輯法則的推理和論證顯然是理性思考,但天馬行空的假設和思辨(to Speculate Imaginatively)[11]26又何嘗不是?從具體事例上升到抽象普遍的概念是理性思考,但巧妙運用圖像和隱喻來陳說道理又何嘗不是?如果不能、不應對理性思考進行狹隘局限的理解,那么對兒童教育本身也理應抱一個更為開放的胸懷和眼光。
那么,如何以哲學來重構教育呢?首先,李普曼不無尖銳地點出當今的教育系統普遍存在的兩個根本弊病,一是將孩子們當成是“繼承人”而非創造者[11]6,二是更注重知識的“傳授”而非真理的“探索”(Discovery)。針對這兩個頑疾,他給出的對治之道也非常簡潔清晰,大致可概括為層層遞進的三個追問及由之引出的三個基本命題。首先,什么是教育?并非僅僅是知識的傳授,也并非只局限于校園的圍墻之內;相反,“任何能幫助我們發現人生意義的活動都是教育”[11]6。這里的“意義”顯然并非僅限于人生里面的點點滴滴,而更是具有一種根本性的生存論含義:孩子們所“渴求的意義”必定與他們的生命息息相關,指向那些不得不追問,甚至不追問就會覺得寢食難安的焦慮和困惑[11]17。由此,我們得以回應那個根本的追問:哲學為什么理應甚至必須成為兒童教育的核心和原型?那正是因為與其他那些以教授某種具體技能和知識的學科相比,唯有哲學才能真正滿足、實現、推進教育的終極本質,即探問、追尋人生的意義。哲學的教育引導孩子們關注自己的生存,激勵他們對根本問題發問,并培養他們有效而良好的提問、思考、回答、質疑等方面的基本方法和素養。亦唯有哲學能讓孩子始終保有一顆充滿好奇(Wonder)的心靈[11]32,而不是在一輪輪的知識灌輸之中被催眠甚至麻痹,進而喪失追問的渴求乃至能力。
因此,我們就觸及李普曼的兒童哲學的第三個關鍵要點,即如何探問意義。他給出了七個具體的方法,但歸結到底無非一句話:“發現意義,就是發現連接(to Discover Connections)。”[11]67連接,既是將現有的知識貫穿在一起,但同樣是向著未知的方向敞開別樣的、不同的思路。哲學的思考作為連接,這在哲學史上是一個基本趨勢,從柏拉圖的辯證法,到康德(Immanuel Kant)的先天綜合判斷,再到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 的“根莖”,皆為明證。正因此,哲學能夠有效解決當下教育中的一個最棘手的頑疾,那正是“碎片化”(Fragmentation)。李普曼在他的幾本著作之中反復突出了這個亟待解決的難點。今天的學科設置是碎片化的,不同的課程背后沒有一以貫之的整體理念;課堂內的時間設置是碎片化的,學生們根本無法體會到一個連貫的心靈成長的過程;甚至連學校的空間規劃也是碎片化的,讓孩子們覺得學習就是在一個個封閉的空間里進行的活動,跟“外面”的廣闊生活世界毫無關系。那么,哲學何以是療治這個碎片化之頑癥的關鍵乃至唯一良方呢?首先,哲學追問的是根本問題,沉思的是終極意義,由此當然可以將不同的分立的學科貫穿在一起,凝聚為一個有機的總體[11]27;其次,哲學說到底就是孩子對自身的關切(“Souci de Soi”),它始于好奇,展開、落實于不斷的、深入的追問,由此就將學習的時間和生命的時間密不可分地連接在一起,共同展現為一個精神成長、成熟的過程;最后,哲學不只是沉思,同樣也是踐行,整個生活世界乃至天地宇宙都是哲學的舞臺,因此它當然不可能局限于條塊分割的時空邊界之內,而一定要保持自身的開放、流變、靈動。由此,哲學不僅連接起不同的學科,也同樣連接起自我和世界、時間和空間、內在和外在。這也呼應著李普曼所明確區分的兒童哲學教育的兩個相關面向,從狹義上來說,它是對現有的支離破碎的學科體系的整體性連接和重構,但從廣義上來看,它理應指向未來的生活和實踐的形式[9]17。
二、從互聯網到元宇宙,從游戲化到“哲學化”
雖然李普曼的批判鞭辟入里,他的理念也堪稱振奮人心,但落實到種種具體的教學實踐,卻總讓人感覺差強人意。他給出的各種具體的課堂教學和討論方法,多少還是讓人覺得僅專注于種種思維技能的培養,并未展現出多少“生存的意義”,遑論精神的成長。同樣,他詳細制定的教學大綱和規劃,除了突出綜合性、整體性這些特征之外,似乎也只是又在課表上多出了幾門課而已,并沒有體現出多少激發好奇和思考的潛能。甚至連他的兩本代表作的標題也明顯與其基本理念相互抵牾,既然哲學本身就是不斷地建立連接、逾越邊界、開放場域,那又為何一定要強調讓它“去上學”(goes to School),“在教室里”(in the Classroom)呢?既然李普曼心目中的哲學教育的理想方式就是蘇格拉底那種在生活情境之中展開的、面對面的活生生的“對話”,那又為何一定要用一套大綱式的條條框框來作繭自縛呢?
對這個顯見矛盾的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自然是,李普曼的前沿理念無法在當時的教育環境之中和平臺之上真正得以實現。韋伯(Max Weber)早已批判過教育的“科層分化”,福柯(Michel Foucault)亦早已深入剖析過學校之中的各種時空乃至身心的“規訓”機制。因此,想要從這些幾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傳統和束縛之中解脫出來,這不是僅靠理念和情懷就能實現的,必須還要有切實的技術和媒介的變革作為基本的支撐。由此可以說,晚近以來的游戲化學習的潮流,甚至從互聯網到元宇宙的轉變,都在一步步實現著李普曼的那些遠領先于時代的洞見和預言。互聯網突破了教室和學校的時空邊界,游戲化增強了學生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社交網絡又將孩子們更為緊密的凝聚在一起。所有這些都一步步、一點點落實著李普曼所構想的“發現連接作為發現意義”的基本教育理念,由此逐步導向他的“將教室轉化為探究之社群”(Communities of Inquiry)[9]19這個終極理想。
然而,誠如前文所述,互聯網階段的游戲化還是主要集中在“技能”培訓這個方面,鮮有涉及哲學這個更為整體性的理念,只有進入到元宇宙階段之后,“哲學化”(Philosophizing)教育才逐漸被提上明確的日程。這其實和游戲本身的發展也是頗為一致的,如“哲學化”設計、元游戲、游戲生態學等更具哲學意謂的形態也是在相當晚近的階段才成為核心議題。關于這個轉變的過程,在此無法詳述,不妨僅結合一個關鍵要點,解釋從游戲化到哲學化的內在線索。那正是保羅·吉很早就提出的“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原則:“人類的學習并不僅僅是發生在頭腦中的活動,而是被徹底嵌入在(或置于)一個物質的、社會的、文化的世界中。”[12]89他在《游戲改變學習》中所列舉的多達三十六項具體方法之中,這個原理足以起到總括和貫穿的作用。
實際上,這個原理從根本上觸及內與外之區分這個核心主題。這又可以進一步區分出表面和深層這兩個面向。表面上看,誠如保羅·吉在書中所言,它首先涉及的正是游戲本身的“內部設計語法”(內容語法)和“外部設計語法”(社會實踐及身份的語法)[12]89。簡單說,游戲遠不止是一個被內在規則和操作所限定的封閉系統,它理應而且已經與外部廣闊的社會場域發生著復雜密切的關系。游戲本就有各種不同的“玩法”乃至“用法”,手冊和攻略上所明確寫出來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從更深層次來看,內外之分又涉及心靈和世界之間的根本關系。這一要點,后來在拉卡薩(Pilar Lacasa)全面深入研究虛擬世界中的學習的專著之中得到進一步闡發,書中的“內部表征”(Internal Representation)所指的已經不是游戲內部的規則,而更是人類思考的內在(即“內稟”【Inherent】、“與生俱來”)媒介,尤其是語言文字[13];而相對的,外部表征則指向著更為廣闊的被“發明”出來的、后天附加上去的物質性、技術性的媒介。從傳統上說,一般會認為人的思考是(主要)發生于內在的心靈之中,雖然同時也需要外部的各種工具、媒介、環境條件來提供輔助和促進,但根本上說還是以內在為主導和統領的。比如,要計算一道稍微復雜一些的數學題,只靠心算肯定不行,還一定至少要動用筆和紙、鍵盤和屏幕。但所有這些物質性的技術工具都只是心靈能力的拓展和配合,不能認為它們由此就越俎代庖,甚至開始指揮大腦和心靈,除非是異想天開的科幻小說情節。事實上,思維的形態越復雜,抽象程度越高,涉及領域越廣,心靈的那種根本性的主導作用就越是明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提出的“舵手”隱喻和“哲學王”之理想皆是此意。無論技術怎樣發達,畢竟還是要由心靈及其理念來統領大局、規劃方案,進而克服障礙和困難。
實際上,保羅·吉所深入闡釋的情境化認知也并未超越這個“內外有別,但內部主導”的基本預設。比如,雖然“人類的思考深度扎根于生活中的具體經驗”[12]132,但這至多只是把具體經驗作為思考的起點,而絕不是作為決定性的因素。正相反,它們只有在被大腦經過抽象化的方式進行編碼之后才能在認知過程之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再比如,雖然游戲化學習大量動用了文字這個傳統的主流媒介之外的各種多樣的“模態”(圖像、文字、標識、互動、抽象設計、聲音等)[12]177,但所有這些都只是輔助和配合,因為最終起到貫穿主導作用的仍然是心靈之中的觀念運作規律,而絕非是圖像化甚至聲音化的思維。同樣,無論怎樣強調“需要在行動中進行思考”,也絕不意味著要以盲目的行動來指揮思考,而只是強調思考應更貼近現實的復雜性,善于在具體情境之中調整策略,檢驗、發展、修正現有的理論。也正因如此,保羅·吉明確強調了“自覺地、明確地反思”[12]160這個主體性的向度。誠然,無論游戲化的技術和媒介平臺怎樣先進和拓展,它畢竟只是用來為人服務的工具,是實現人的目的的手段,是用來輔助人類心靈思考的“外部”條件。
既然如此,我們想當然地就會以為,游戲化學習的宗旨肯定是借助更為豐富、發達、開放的外部技術網絡和媒介平臺來不斷回歸和深化人類心靈的內在思想世界。但是,實情卻恰恰相反。游戲化確實在“自內至外”的拓展這個維度上做足了功夫,情景化、多模態、多路徑、遷移、分布,忙得不亦樂乎。但這也讓它日漸沉浸、迷失于外部維度之中,而忽視了內在思想乃至精神這個要旨所在。由此看來,游戲化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教學的手段,開闊了學習的環境,激發了學生的興趣,但并未從根本上對李普曼所遺留下來的兒童哲學教育中的難題有所回應和實質性的推進。這尤其體現在兩個明顯的方面。一方面,雖然保羅·吉屢屢強調如“批判性思維”“元級別思考”“自知原則”[12]305-306等看似具有鮮明哲學意味的維度,但這些大多只是運用于具體問題的解決、具體思維能力的培養之中,而鮮有上升到“元”維度去思索那些“大問題”,更不必說對人類思維本身的既有框架和模式進行通盤的反思、創造、變革[李普曼自己也強調,真正的批判性思維應該是“對思考本身進行思考”(Thinking about Thinking),或者說“對自身的思想活動有所反思,進而能夠使它從熟悉的環境轉向不熟悉的環境”(李普曼的《教育中的思考》(Thinking in Education)[14])。]。就此而言,游戲化學習顯然未能達到李普曼所強調的那種開放性的“想象式思辨”的更高境界,它只是在學習“使用”工具,而尚未真正開始嘗試“檢驗”現有工具,進而“發明”新的工具;它只能提升孩子的智力水平,但卻并未完全展現出更高層次的精神力量。或許游戲化學習真的能讓孩子更“聰明”(Smart),但卻不會更“智慧”[參見羅斯(W.D.Ross)對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智慧”概念的六點概括,轉引自汪子嵩,范明生,陳村富等的《希臘哲學史》[15]。]。說到底,它最終還是將孩子們塑造成了知識的“接受者、吸納者”(即便往往是主動的、積極的接受者),而遠未將他們引向“思想的創造者、發明者”這個更高的目的。
另一方面,由此就產生出游戲化學習與李普曼的教育理念之間的最明顯分歧,那就是前者幾乎全然運作于自然科學或同樣具有鮮明實證性的社會科學的教與學的領域,而鮮有真正涉及、關心孩子們對“生存意義”的反思、質疑乃至創造。在保羅·吉和托波的著作之中,我們能發現大量的物理學和數學的學習場景,但卻從未發現在蘇格拉底的哲學對話和李普曼的哲學課堂上經常會出現的那些直面生命本身的追問:“正義、美、自由是什么?”甚至“你為什么要上學”[11]94這樣直指人心的探問。可以說,哲學這個關鍵維度的缺失,是日漸興盛的游戲化學習潮流的最大隱憂。李普曼曾批評當時的教育體系沒有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沒有讓孩子更深刻、更有效、更不同地思考,進而更切近自己的生存而思考。但所有這些弊病,在當下的游戲化的平臺之上也并未真正得到有針對性的反思和有效的診療,甚至連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都逐漸被遮蔽和遺忘了。就此而言,李普曼所提出的“將哲學探究作為教育范式”的基本理念,仍然是擺在當今所有教育者面前的核心議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游戲化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它甚至連最根本的問題都還沒有觸及。
但元宇宙的到來多少讓深陷困頓之中的兒童教育向前跳躍了一大步。它的3D沉浸世界所增加的并非僅僅是空間的深度,而更是精神的深度,因為它創造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環境,得以讓孩子們在其中真正以“關切自身”的方式來進行開放性的“哲學實驗”。關于哲學實驗,當然有各種不同的理解,但我們在這里僅強調一個要點,即它并非僅是接受、學習、理解、運用某個(某些)既有的哲學理論,而更是要去檢驗、質疑、挑戰現有的概念和理論[8]36,甚至創造出自己獨特的、全新的哲學思考,并由此不斷地反躬自問,在世界之中去探尋生存的意義,來連接彼此的心靈。哲學化和精神化,似乎正是元宇宙為游戲化所帶來的實質性提升乃至深刻變革。
但這個變革當然不是驟然間實現的,其萌芽已然蘊藏于游戲化學習自身之中,那正是身份和敘事這兩個要點。之所以游戲化會呈現出“重外而輕內”的失衡式發展,身份的錯位乃至焦慮顯然是一個根本的癥結。在傳統的學習環境之中,自我作為主體顯然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面對書本以及各種學習資料和工具,自我吸納知識、提出問題、探尋答案,在這個過程之中,自我始終伴隨著或明或暗的反思或自知的意識:“我”正是學習的主體,面對各種對象化的知識素材,“我”不應只是消極被動的接收者,而更應該主動地去探尋和綜合,將知識“內化”于自身之中,提升自我的能力,走向精神的覺醒乃至成熟。但正是這個自明且自知的“自我”在游戲化學習的全新環境之下卻變成了一個極為棘手的難題。游戲化學習與傳統學習之間的差異,根本就在于前者更突出了“互動性”。這個互動性并非僅僅強調主客之間的相互作用,因為這種程度的互動性顯然在傳統學習過程之中也普遍存在。電子游戲的互動性更展現出鮮明的沉浸性和在場感。簡言之,游戲化并非僅僅是將自我的內在能力向外進行拓展和實現,它更進一步將自我“投射”向外部,進入到各種虛擬世界的場景之中,成為一個個分化的“化身”(Avatar)。自我外化到屏幕之上,分化為不同的分身,甚至遷移于不同的環境之中。這既是游戲化的最明顯強項,同時又是最根本的短板。強項自不待言,因為代入式的沉浸感能夠極大激發孩子們的主動參與和學習的積極性,交互性的學習方式能夠增添學習過程之中的持續樂趣,組團、聯網的學習方式又能將孩子們緊密地凝聚在一起。但是,短板和瓶頸似乎亦同樣明顯甚至難以克服。如果自我始終在不斷外化、分化、衍化,那么到底哪一個自我才是真正的自我?哪一個自我才能起到真正的主導作用?學習的過程到底和哪個自我真正相關?這總會導向那個李普曼式的追問:學習,到底在何種意義上是必須、理應由自我承擔起來的心靈的主動探尋的過程?當自我及其化身之間圓融無礙、流暢轉換之際,這些根本性的質疑肯定不會出現。但遺憾的是,在游戲化的環境之中,二者之間的矛盾、隔膜乃至沖突的情形也不在少數。保羅·吉將游戲化中存在的自我的諸形態區分為“虛擬的身份”“真實世界的身份”及“投射的身份”這三種[12]104-106,這為學界普遍認同。顯然,這個三元的區分只是基本和初始的形態,因為完全有可能衍生出更為復雜交織的變化,如虛擬的身份又可以進一步分化衍生,而真實世界的身份本來也具有多元性,這就使得二者之間的“投射”和“轉換”關系愈發復雜糾結。但哪怕僅局限在最簡單的情形之中,當一個真實的我坐在電腦前面對著屏幕之上的那個虛擬的我之時,二者之間往往并不是相安無事、和平共處的,保羅·吉自述的那個真實的他自己和虛擬的珠珠之間的愛恨糾葛正是如此。或許最終他還是在心中感覺到了一種“為自己感到驕傲”[12]110的自知和反思的意識,但這一切跟屏幕上的珠珠到底有何種本質性的關聯呢?“她”難道僅僅是我手中操控的傀儡?她難道不也同樣和我相似,只不過是在另一個、那一個世界之中行動和抉擇的主體?
或許正是出于自我之分化乃至分裂所引發的困惑和焦慮,才會最終導致游戲化學習之中所普遍存在的內外失衡現象。游戲化在自我的外化、分化和衍生方面極盡所能,但它恰恰無力甚至無意去思考的正是“我是誰”這個終極的主體性問題。而如果無法最終化解自我在外化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的異化乃至裂化的危機[誠如很多學者指出的,虛擬世界中的“去身化的自我”(Disembodied Self)和真實世界中的“具身化的自我”(Embodied Self)之間的“不連續性”始終是一個根本難題,參見羅賓·泰格蘭德(Robin Teigland)和多米尼克·鮑爾(Dominic Power)的《沉浸式網絡》(The Immersive Internet)[16]33-34。],那么很顯然,游戲化除了在學習環境、學習方法、學習技術等“外圍”的方面大做文章之外,確乎始終無法真正接近、觸及李普曼的教育理念的最內在核心,那正是學習作為自我對于自身的主動反思、探尋和培育。亦或許正因此,關切自我的哲學追問從來都不會、也不能成為游戲化學習的主題,甚至可以說游戲化的環境本身就是對哲學思維的相當大程度的阻礙乃至破壞。
但是,這一切在進入元宇宙階段之后顯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和改觀。游戲化和哲學化的結合,令元宇宙之中的學習過程和形態都發生了根本變化。這里僅關注一個要點,那正是敘事。通過講故事來引導孩子一點點進入哲學思考和對話的境界,這亦是兒童哲學教育中的一個普遍手法。這背后的緣由,李普曼曾有過一個相當深刻的解釋。在孩子那里,“科學的解釋”“象征的解釋”(Symbolic Interpretation)和“哲學的解釋”這三種學習進路往往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11]33-36。簡言之,孩子們的心靈還保持著相當程度的融合性和開放性,并沒有陷入到學科分化乃至對立的人為格局之中。以生動的形象和豐富的隱喻來帶入知識的學習和哲理的思辨,這向來都是一個極為有效的進路。游戲化學習當然也是如此,憑借著強大的交互性和沉浸性的游戲環境,它將“講故事”這個學習的好方法帶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傳統的課堂和班級里,師生之間還只是停留于“講故事”“聽故事”,進而“討論”和“分享”領悟和心得;但進入游戲的虛擬學習空間之后,孩子更可以“進入”故事,甚至可以改編、創造故事。我們看到,游戲化環境實現了之前不可能存在的學習方式,那正是主動的、“親身”的體驗。如果說在課堂里面,我們只是故事的講述者和反思者,那么在游戲之中,我們進一步化身為“劇中人”,這無疑是對學習和自我這兩個方面的雙重強化,進而將二者更為緊密地維系在一起:那不僅是一個“別人”的故事,那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故事;那不僅是講出來的故事,那更是我自己“演出來”甚至“活出來”的故事。保羅·吉曾將體驗作為“主動學習”的首要特征[12]65,而在林(K.Y.T.Lim)所總結出來的虛擬空間的游戲化學習的六大法則之中,“以存在的方式學習”(Learning by Being)也是關鍵的一環[16]135,這些都是明證。
即便如此,誠如前文所述,自我的異化和裂化仍然是一個突出而棘手的難題。我們盡可以將“以存在的方式學習”作為一個根本的原則,但隨之總會導向一系列難解之謎:“誰的存在?”“哪個存在?”甚至“為何存在?”而元宇宙則從自我和學習這雙重方面克服了游戲化的先天頑疾。首先,元宇宙中的自我不是外化的、分化的、投射的;正相反,它和真實自我之間最終是“同一”的關系,并不存在任何的分裂和沖突。簡言之,在游戲化環境之中,自我及其分身“同時”處于不同的空間乃至世界之中,但在元宇宙之中,自我只有一個,世界也只有一個,自我并沒有分裂,而是在經歷一個“轉化”,也即不斷告別自己的真實肉身,進而不斷“進入”到那唯一一個元宇宙之中。游戲化之中始終糾結的內外之分在元宇宙之中根本就不會出現,因為所有的一切都已經,或即將進入到元宇宙之“內”,它是至大無“外”的。要深刻理解這一點,首先必然要明確一個基本的事實:元宇宙絕非另外一個平行宇宙,它不是現實世界之外的另一個虛擬世界;相反,它就是人類即將進入的下一個世界,唯一的完整世界。它不是與現實世界平行,而是注定將“取代”現實世界,成為下一個人類生存于其中的真實世界。這個取代過程背后的強大的技術動力引擎,不妨借用東浩紀(Azuma)所概括的“增強現實系統”的三個重大變革來理解。首先,3D互聯網的沉浸技術將逐步模糊乃至抹除虛擬和現實之間的邊界;其次,虛擬世界之中的交互和溝通變得越來越實時、順暢和“平滑”;最后,大數據技術正在將人的從身到心的所有方面皆轉化為數據,進行存儲、處理和流通[17]103。在游戲化環境之中,我們是通過界面來和化身與數據彼此互動;但在元宇宙之中,我們是在真實的場景之中和一個個真實的個體相互溝通。這里,既不存在分身的問題,也根本沒有自我異化的困境。因此,關于元宇宙的本性,我們既不認為它僅僅是“增強版的現實”,也不認為它是現實之外的另一個平行的宇宙[6]282,而更傾向于認為它其實是對當下現實的全面、整體、徹底的“取代”(Replacement)[6]279。
由此亦深刻改變了敘事的學習場景,并將其鮮明導向了哲學化這個重要方向。在游戲化的環境之中,孩子們雖然從講述者和聆聽者升級、增強為參與者和體驗者,但由此亦陷入自我分裂乃至異化的困境之中。而在元宇宙之中,自我的不同形態和維度都實現了一種最終的統一,成為“在世界之中”的生存者。然而,元宇宙中的生存者與之前的物理世界之中的存在者之間至少存在著兩個根本差異。首先,后者仍然是以人的肉身為存在的基礎、核心和背景,但前者則更傾向于以數據為核心來建構全新的人格系統。簡言之,如果說后者是“肉身之存在”(Being in Body),則前者顯然可以說是“數據之人格”(Digital Person)。在元宇宙之中,不能說物質和肉身的維度就徹底被抹除,但確實越來越弱化和邊緣化。其次,由此就引申出另一個根本性的差異。肉身的存在是有限的,即有一個從生到死的“演歷”過程;但數據人則正相反,它的存在方式越來越掙脫了自然生命的束縛,進而愈發接近數字化身(Avatar)的形態,可存儲、可修復,甚至可改寫、可抹除。說它是“永生的”(Immortal)亦不甚恰當,因為它已經完全不在生死之間的自然節律之中。就此而言,元宇宙中的游戲和學習,乃至學習和生活之間是全無邊界的:它本來就脫胎于游戲化的平臺,因而先天地具有一整套的游戲化學習的模式;但同時,它又超越了游戲化的“內外分裂、自我迷失”的困境,更為直接地將學習跟自我的生存緊密結合在一起。在元宇宙中,學習、吸納任何知識都變得輕而易舉、唾手可得,根本不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由此,唯一真正的學習和教育就恰恰將順理成章地邁向李普曼心目中的那個終極理念,即關注自己的生存。甚而,元宇宙中的孩子們還不僅是“關注”自己的生存,更是能夠改寫自己的人格、重寫自己的人生,甚至重啟自己的生命。因為,一切都是游戲,一切都是生存本身的游戲,而生存本身的游戲,就將是元宇宙中的學習和教育的終極旨歸。在這個意義上,元宇宙中的生存化學習正是名副其實的哲學實驗,因為孩子們唯一的終極關注正是“我為什么活著”“我為什么這樣活著”“我如果換一個人格、換一種活法又會怎樣呢”。由此,在這些根本的哲學問題的引導之下,他們亦無時無處不在進行著人生的實驗,選擇不同的道路,權衡不同的結果,斟酌不同的意義。元宇宙中的生存,無疑就是哲學化的,而且是前所未有地實現了古希臘以來的那個“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終極理想。不妨借用卡斯特羅諾瓦(Edward Castronova)的詩意概括:“元宇宙就是我們的生存藝術。它是一場戲劇,而我們都是演員。它是一本關于我們的書,而我們也在以自己的人生書寫著它。”[16]13
三、結語:元宇宙及其不滿
在直觀上,元宇宙真的有幾分近似人類歷史的終點,甚至一個無限完美的數字天國。但它到底是極樂仙境,還是冷酷盡頭?目前還無法給出定論。或者說,給出定論本身就不是一個明智之舉。面對元宇宙的未來,真正明智的做法或許并非是貿然給出一個是或否、善或惡的判定,而更應該切實地去“做”、去行動。介入到錯綜復雜的現實之中,卷入到彼此紛爭的力量場域之中,展開德勒茲式的“批評與診斷”(Critique et Clinique),進而將那個(些)未來保持在敞開、未知、可能的狀態。把未來留給未來,把對未來的判斷留給未來的孩子吧!
不過,我們似乎仍有必要針對元宇宙給出幾點批判性的反思。實際上,當尼爾·史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名作《雪崩》(Snow Crash,1992)之中給出“元宇宙”的原初構想時,在這個氣象宏偉的未來景觀之下,字里行間其實已經透露出揮之不去的灰暗氣息和絕望情緒。可以說,他以幻想之眼所預測的三個基本特征——全球性互聯網、化身式生存、沉浸式環境[18]150——都已經或正在成為元宇宙的現實和本質的形態。或許正因此,當我們從今天的現實回望早年的文本之時,或許更能從中讀出幾分警示乃至警醒的意味。誠然,互聯網正在超越生死的自然大限,生存正在逐步變成無限重啟的游戲,但這是最完美的未來了嗎?或許并不是。元宇宙最令我們焦慮不安之處,正在于它同樣將對人的全面監控和操控推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如今,我們所有人都越來越像是“從魚缸中向往張望的魚”(Inside the Fishbowl Looking Around)[18]151,因為留給我們的“外部”空間及其可能已經越來越小,甚至接近消失。建構元宇宙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技術前提恰恰是對人的全面的、巨細無遺的數據化,而這當然也就必然需要在物理世界之中布下無數的“嵌入式傳感器”(Embedded Sensors)[17]125,來捕捉人的一舉一動,甚至一念一息。這美其名曰是為了增進對人的了解,但實實在在就是對人的全面操控。而且借助著強大的沉浸式技術,元宇宙的操控更展現出近乎無形乃至無痕的面貌,逐步遮蔽、抹除現實和虛擬之間的每一條邊界,漸次清除侵入到元宇宙的平滑自洽的網絡之中的每一種“外部”因素,這就是技術發展的最為重要的未來趨勢,因為“最為深刻的技術正是那些能讓自己隱形的技術”[17]111。誠如《雪崩》所描述的觸目驚心的場景:技術正在全面改變人的生命套件(Bioware),甚至從最深層改變著人的“大腦回路”(Deep Structures)[18]153-154。再度借用卡斯特羅諾瓦的尖銳批判,恰可以說,元宇宙也許最大限度、最徹底地消除了人類身上的各種不平等(地位、身份、性別等),但卻仍然保留了一個根本性的不平等,那正是控制—被控制,或者說主動—被動之間的不平等。元宇宙就是一場盛大的、無休無止甚至無限循環的生存游戲,而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是游戲玩家。但是否每一個人就真的都在進行積極主動的哲學探索,甚至都能、都想成為哲學家呢?不盡然。或許,事實正相反。真正進行著主動思考的其實只是金字塔尖上的寥寥無幾的幾個人[16]17,而那些龐大的“基數”人群其實都處于深重的、難以掙脫亦難以改變的“媒介被動性”(Media Passivity)[16]20的狀態。元宇宙真的是哲學化學習和教育的理想空間?在其中真的能夠實現哲學化生存的美好愿景?我們當然是有理由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但即便如此,仍不必就此對未來放棄希望。元宇宙本來就是一個實驗和游戲之地,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承擔起哲學思考的責任和使命。在這里,雖然我們暫且無力或無意給出全面的診斷和療治方案,但至少可以提及一個值得關注的要點,那正是斯蒂格勒在《什么讓生活有價值?》(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一書中所借用的英國精神分析學家溫尼科特(D.W.Winnicott)的“過渡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理論。它本來指的是在母親和幼童之間的那個既非“內在心理現實”又非“外部世界”的中間過渡地帶[19]69,但其實完全可以且理應具有更為廣泛的社會意義。斯蒂格勒就由此倡議我們以過渡性客體來重建人和人之間的“愛的維系”[20],由此療治技術空間之中日益蔓延的無情、均質、怠惰等精神的消極被動癥狀。但他恰恰忽視了游戲這個關鍵要點,畢竟溫尼科特曾反復明確地將過渡對象運作的空間稱作一個“游戲場”(Playground)[19]64。那么,在游戲化學習和哲學化生存的元宇宙之中,又何以真正建立起人和人之間的那種充滿關切和愛意的過渡性中間場域?也許教育者正是這個關鍵角色。當元宇宙深刻改變了學習和游戲的傳統狀態之后,它同樣也對教育者們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使命。如何讓元宇宙不再淪為技術霸權的操練場和頭腦精英的跑馬場,而是真正成為人與人之間平等而親密交互的游戲場,這將是未來教育者義不容辭的使命。讓教育變成一種生存的關切,讓孩子們在學習過程之中學會關切自身,讓人和人之間在學習的過程之中學會彼此關切,這將是未來教師最核心的探索主題。
參考文獻:
[1]柏拉圖.柏拉圖全集:下卷[M].增訂版.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06-207.
[2]STRAUSS L.The Argument and the Action of Platos Laws[M].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105.
[3]約翰·赫伊津哈.游戲的人:文化中游戲成分的研究[M].何道寬,譯.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12.
[4]黑格爾.精神現象學[M].先剛,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6.
[5]韓炳哲.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M].程巍,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9.
[6]BAINBRIDGE W S.Online Worlds: convergence of the Real and the Virtual[M].London: Springer-Verlag,2010.
[7]KIM S,SONG K,LOCKEE B.Gamification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enjoy Learning Like Gaming[M].Berlin:Springer,2017:26.
[8]PERRON B,WOLF M J.P.The Video Game Theory Reader 2[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9.
[9]LIPMAN M.Philosophy Goes to School[M].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8.
[10]TOPPING K J,TRICKEY S,CLEGHORN P.A Teachers Guide to Philosophy for Children[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19:24.
[11]LIPMAN M,SHARP A M,OSCANYAN F S.Philosophy in the Classroom[M].second edition.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0.
[12]詹姆斯·保羅·吉.游戲改變學習:游戲素養、批判性思維與未來教育[M].孫靜,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13]LACASA P.Learning in Real and Virtual Worlds[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61.
[14]LIPMAN M.Thinking in Education[M].second ed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57.
[15]汪子嵩,范明生,陳村富,等.希臘哲學史:第三卷[M].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33-534.
[16]TEIGLAND R,POWER D.The Immersive Internet[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
[17]SONVILLA-WEISS S.(IN)VISIBLE: Learing to Act in the Metaverse[M].New York: Springer-Verlag/Wien,2008.
[18]STEPHAN M.Defining Literary Postmodern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9.
[19]WINNICOTT D.W.Playing and Realit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
[20]STIEGLER B.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M].trans., ROSS D.Cambridge:Polity Press,2013:2-3.
(責任編輯:張 婭)
收稿日期:2021-07-20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當代法國哲學的審美維度研究”(17BZ015)。
作者簡介:
姜宇輝,男,上海人,博士,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當代法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