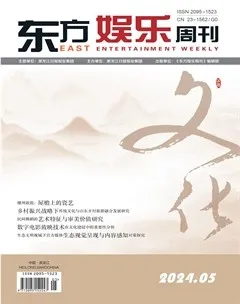新媒體寫作平臺的情感傳播機制研究
董佳文
[ 摘要] 在信息化時代,新媒體技術已日益廣泛地滲入人類社會生活,越來越多的新媒體平臺以滿足用戶情感需求為中心,形成情感傳播。基于此,文章以微信公眾號“我從新疆來”為例,探究新媒體寫作平臺的情感傳播機制,分析新媒體寫作平臺在情感傳播中所呈現出的特點、方式及產生的作用。
[ 關鍵詞] 新媒體;情感傳播;寫作
在信息化時代,新媒體寫作平臺已成為內容生產的重要媒介,是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平臺。因其獨特的傳播優勢,以及寫作主體和寫作受體高度互動的特性,新媒體平臺也為大眾寫作提供了發布媒介——微信公眾號。微信公眾號具有傳播迅速、內容豐富、緊貼生活的特征,以及公眾號內容的情感化傾向,加強了受眾的情感體驗和情感認同,承擔著滿足情感需求、實現情感傳播的重要作用。本文以微信公眾號“我從新疆來”為例,探討新媒體寫作平臺在情感傳播中所呈現出的特點、方式及產生的作用。
微信公眾號“我從新疆來”于2016 年12 月5 日正式面世,由全球各地大學生志愿者團隊自主運營。截至2022 年8 月,公眾號已發表原創文章2220 篇,其中部分文章被《環球時報》英文版、新華社等主流媒體轉載報道,是新疆話題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矩陣之一。公眾號中設有人物故事、一眼新疆、新疆滋味、跡憶新疆、生活研究所、聊撩好書、疆來電臺等7 個版塊,成為書寫新疆圖景、建構新疆形象的極具影響力的新媒體平臺。
一、人物故事的情感化敘事
情感是人際關系的維持者,是對宏觀社會結構及其文化生成的承擔者,也是一種能夠分裂社會的力量[1]。情感作為人際聯系的樞紐,能產生相應的傳播作用,情感傳播的主體以情感為基礎,利用情感邏輯構建傳播方式,通過情感過程影響傳播受眾,與受眾形成交流互動和情感共享,以便達到自己的傳播目的和效果[2]。“我從新疆來”中的人物故事正以其強烈的情感化敘事建立起文本與受眾之間的連接,并通過審美主體的情感表達、輕悅化的敘事方式及真實細膩的語言風格滿足讀者的信息需求,觸動讀者的內心,實現情感傳播。
“我從新疆來”人物故事集中收錄了大量真實、勵志、溫暖的平凡故事,也是整個寫作平臺聚焦情感內核的主要部分。故事的展開以深度采訪為基礎,作者對審美對象進行情感式探索,深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添以文學的寫作手法,呈現出文本情感化的敘事形式。比如,《孫嘉陽丨我想把新疆色彩“畫”在臉上》講述了主人公以新疆獨特的地域元素為基底,創立原創彩妝品牌的真誠之旅。據了解,采寫孫嘉陽的作者,在了解其堅持繪畫的求學旅程、敢想敢拼的創業經歷后,也聯想到了自己曾經為熱愛付出的過程。在這樣惺惺相惜的氛圍下,寫作對象也更愿意吐露心聲。類似的情感體驗也引起了作者極大的創作熱情,使得一篇勵志故事獲得了與讀者更多的情感聯結。同時,在《俞敏洪對話李娟:年輕的生命很少有絕望》中,作者以“偽人物采訪”與文學批評相結合的方式再現了俞敏洪對話李娟的直播內容,字句間流露出對作家李娟的綿長情誼,道出了廣大讀者心中對李娟老師及其文字的真切喜愛。這種粉絲寫偶像的審美創造,也不斷強化了平臺與用戶之間的情感連接。人物故事集中像這樣講述新疆榜樣的例子也有很多,如《阿不都沙拉木丨中國男籃23 號,他回來了》《連續主持春晚八年的尼格買提,真的是寶藏男孩》《劉曉玲丨叫我怎能不愛你,我的新疆孩子們》等,還有很多平凡人的非凡故事,如《蘇比努爾丨從新疆大學到東京藝術大學,我把留學當做修行》等。寫作主體都充分調動自己所體驗過的思想和情感,字里行間透露著對采寫人物用心解讀后的情感聚集,寫出了真實人物的血肉之魂,感染了每一位讀者,形成情感互動,實現情感傳播。
“我從新疆來”人物故事集中的日常化敘事同樣為讀者帶來了很強的畫面感和在場感,從而建構起溝通情感的要道。新媒體平臺相比傳統媒體,在敘事表達上往往更加輕松活潑[3]。人物故事集中很少見到悲傷基調的文章,大多數文章都以輕松、日常化的表達呈現出人物的故事。比如,《這位神秘畫家筆下的少數民族插畫太酷了!》介紹了自由設計人“神秘配電箱”的插畫之路,語言靈活。其中談到藝名的由來,則是在扔垃圾時看到了陽光高照下的配電箱,在白色的墻壁上尤為突出,以旁觀者的敘事視角敘述出生活的細節。同時,用心設置的小標題在介紹人物經歷時,既增加了文章的層次感,也靈動地展現了在特定時空中的人物活動。比如,《納迪拉丨從克拉瑪依到“北方哈佛”麥吉爾》分別以“穿越逆境,抵達繁星”“當她飛向屬于她的山”“考驗只會讓我變得更堅強”“未來亦漫長、未來皆可期”四個簡短的小標題概括出了主人公不同的成長階段和她對自己的期許,在個性化色彩鮮明的敘述中鉤沉出生活的精彩鮮活。再如,《帕孜麗婭丨成為前進的小帕小姐》以第一人稱視角展現了主人公求學生涯中對寫作、生命的探賾索隱。口述式的娓娓道來既拉近了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又富含生活氣息,營造出強有力的在場感,讓讀者在短時間內真切體會到情緒和溫度。
“我從新疆來”人物故事集極大地發揮了情感化敘事的功用,作者以原生態的情感積累建構起與寫作對象之間的情感體驗,在日常化的敘事表達中立足生活情境,繞過過于宏大的主題,僅用溫暖的文字沉潛在平凡人的非凡生活和內心情感中,在情感共鳴中增加了文章情感傳播的深度。
二、情感連接的符號化呈現
符號之接受,必然以有意義為前提,意義使符號成為可能[4]。在新媒體平臺,公眾帶著個人情感走進虛擬公共空間,參與公共事件討論并表達訴求[5]。微信公眾號“我從新疆來”在一眼新疆、新疆滋味、跡憶新疆等版塊中,利用新疆的美景、美食、美跡等極具新疆地域特色的符號加強與讀者的情感聯系,同時結合音視頻、直播對話等多種方式,為讀者帶來既好看又好玩的情感體驗。
在美食篇章中,列舉了眾多的新疆美食名片,從大盤雞、椒麻雞到酸奶制品,展現了新疆獨特的飲食文化,以鮮艷誘人的圖片、視頻呈現,沖擊著新疆人的胃,產生了極強的熟悉感,調動了讀者參與話題的積極性。比如,閱讀量超過10 萬的推文《來新疆必吃的50 種美食,你pick 哪一款》中,推介了新疆各地的特色食物,如巴楚烤魚、伊犁手工冰淇淋、昌吉九碗三行子、天潤酸奶等,讀者在留言評論區激烈討論,身在新疆的人表示自豪,遠離家鄉的人直呼想念,來過新疆的人再次懷念。這些圖片已不再是簡單的畫面,而更多地代表了新疆形象在人們心中的樣子。再如,《春天來一碗新疆丸子湯,絕了》這篇文章將昌吉丸子湯與徐州丸子湯做橫向比較,也讓讀者從材料、制作、配菜等多個方面認識到新疆丸子湯的特別之處,加深了人們對新疆的了解。
新疆有著獨具特色的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景觀,雪山、牛羊、巴扎等都是新疆的景觀名片,這些縱橫在新疆廣袤土地上的各類風景,滋養著新疆人民,支撐著他們的精神世界,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成為連通平臺與用戶之間最直觀的情感媒介。微信公眾號“我從新疆來”將新疆奇特的自然景觀符號用人性化的表述方式加以呈現,傳達出對自然、土地的情感。比如,《除了伽師瓜,你對伽師一無所知》介紹了鹽堿地與美麗共存的奇跡——伽師,講述了勤勞和堅守的故事,雖沒有景觀描述,但鮮活地展現了伽師的美麗,不少讀者紛紛留言“最愛伽師”。再如,文章《巴扎丨最顯新疆鄉村的人間煙火氣》寫出了介于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新疆巴扎對于新疆人的特殊意義,既展現了暖暖真情下巴扎生活的具象含義,也表達了作為重要社交方式的巴扎帶來情感疏導的抽象意義,與受眾形成情感共享。另外,《和田很遠,但我還是想去》《你們博樂人做的夢都是藍色的吧?》等文章借助人文化操作,將美麗的新疆景觀形象符號進行完美展示,充分實現了自然形象的審美意義,也達成了與受眾之間的情感互動,形成了情感傳播的功能化效果。
因此,微信公眾號“我從新疆來”充分挖掘了能夠連接受眾情感的新疆地域特色元素,以富有情感的個性化表達和多樣化的形式引起受眾的情感共鳴,有效地促進了情感傳播。
三、情感價值的正能量傳播
媒介在向公眾傳播信息時,要遵循法律法規和社會倫理規范的限制,要傳播能夠提升公眾文化品位、有教育意義和人文價值的信息,這是媒體社會責任論的觀點[6]。微信公眾號“我從新疆來”關注新疆人、新疆事、新疆景,雖沒有選擇“家國情懷”“民族團結”等宏大敘事,但以小人物命運融入社會背景的表達方式,以紀實的手法講述了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新疆人在各地工作生活的故事,展現了人們為夢想拼搏、為熱愛堅守的勇氣。這種深入群眾中尋找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題故事,符合當代社會的主旋律,更能引起讀者的認同和共鳴,并讓讀者感知到健康的情感價值導向,獲得情感上的正能量。
“我從新疆來”主題團隊深入基層,挖掘真實生活中勵志、感人的故事。其中不僅有家喻戶曉的名人故事,也包括很多普通百姓的追夢歷程。比如,有尼格買提的夢想舞臺,有艾克熱木江醫生步履不停的鉆研之路,也有大膽開啟北京之旅的迪麗努爾,還有從內地旅居新疆找尋自己的慢慢姑娘,他們都在自己的人生軌跡中展現出自我價值,體現出對生活的熱愛及對美好未來的無限期待。不難發現,這些傳播內容中大多以成長和努力為主要線索,充滿熱情的主人公們與這個時代的所有普通人一樣,在通往夢想的道路上前進。這些緊貼生活、真實溫暖的成長體驗和情感經歷,通過創作者正向的情感表達,可以傳遞社會正能量,幫助受眾獲得健康的情感價值導向,發揮積極的情感歸位作用。另外,這些真實的故事也引起了讀者的情感共鳴,獲得大量讀者的積極反饋。比如,《我是在與病魔作斗爭,也在為新人送祝福的熱依拉》一文的留言區,廣大讀者既震撼于熱依拉與病魔斗爭的經歷,也從中獲得了永不放棄的精神鼓舞,由衷希望主人公早日康復。社會中的個體都不可避免地會與人或環境打交道,形成情感交流,每個人都會從中獲得情感的動力。“我從新疆來”利用新媒體寫作平臺,創作具有情感正能量的作品,突出主流價值引領,完成媒介在傳播信息時的社會責任。
微信公眾號“我從新疆來”在選題內容方面關注社會熱點,建構了美麗的新疆形象,也通過專題介紹的方式向讀者推介中華經典作品或時下優秀文藝作品,實現社會情感的正向發展。在“聊撩好書”合集中,平臺選取優秀的文藝作品并與讀者共享,滿足受眾的情感需求。比如,《一個要自殺的男人,教會了我如何愛上生活!》將瑞典冠軍小說拆解為小故事,著重說明生活的美好。另外,《豆瓣9.1,治好我精神內耗的神仙綜藝》向讀者推介慢綜《我在島嶼讀書》,運用節目片段解答了關于閱讀、經典作品、生活本質的很多問題,細心整理出節目中老師推薦的書目,鼓勵讀者用閱讀尋找自己。
“我從新疆來”這一新媒體寫作平臺聚焦當代社會問題,并非博人眼球地編寫內容,而是在潛移默化中引導社會情感走向正能量方向;很少以悲情苦難的故事賺足淚水,而是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主旋律作為其真正的精神內核,以充滿正能量的社會情感影響受眾群體。
四、結語
新媒體寫作平臺通過自身強大的文化傳播力發揮著情感傳播、價值引領的重要作用。微信公眾號“我從新疆來”則立足人物故事的情感化敘事、情感連接的符號化呈現、情感價值的正能量傳播,不斷建立起創作平臺與用戶之間的良好情感連接,傳遞真善美的作品,提升文化傳播力,促進新媒體行業的良性發展,也為當前環境下新媒體寫作平臺的運營提供了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
[1] 特納,斯戴茲.情感社會學[M].孫俊才,文軍,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 李建軍,馬瑞雪,周普元.論情感傳播的特點和原則[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05):100-106,192.
[3] 盛芳,彭婷.新媒體內容生產的情感敘事策略與意義建構:基于人物傳播類微信公眾號實踐的分析[J].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18,39(02):147-151.
[4] 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M].2 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5] 李宏.講好警察故事:新媒體平臺上的內容特點與傳播效果——以中國警察網新浪微博為例[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8(06):119-130.
[6] 金丹陽.自媒體的情感呈現與傳播:以微信公眾號為例[D].吉林大學,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