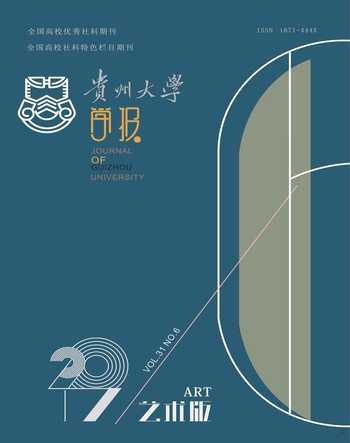影像中的生態、本土知識及生計策略
邴波
摘 要: 新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為綠洲生態系統與草原生態系統的比較研究提供了足夠有力的證據,通過影像內容不僅可以展示出它們在各自文化模塑下的整體性特征,清晰地認識兩種系統演進過程中的文化、精神邏輯,而且還可以利用本土知識、生計方式等方面進行自然調節,進一步展示生態與新疆少數民族民族文化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
關鍵詞: 生態人類學;新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生態系統;本土知識;生計方式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444X(2017)06-0027-06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ysb.2017.06.004
將生態學與人類學融合,將人類、環境及文化之間復雜的關系所做的多樣化研究納入人類學的知識體系是生態人類學的主要方向。伴隨人類社會的生態轉型,對人類的文化、生理及環境適應的知識和行為體系進行文化闡釋的生態人類學,[1]已經發展成為一種以生態環境來探討解決人的生存模式與生命狀態的意識形態,它以環境透視文化,以微觀透視整體,注重系統性、整體性,追蹤生態系統背后的世界觀及價值觀,從而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保存記憶。正如米爾頓所言:“生態學研究能夠確定什么樣的人類實踐對環境有利,什么有害,而人類學的分析則足以揭示是些什么樣的世界觀支持良性的或有害的做法,而且又轉而為后者所支持。所以人類學有助于我們理解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是什么,不僅弄清楚應該怎樣對待環境,而且弄清楚什么樣的價值觀、信仰、親屬結構、政治意識形態以及儀式傳統會支持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行為。”[2]
生態人類學理論關于人類、文化和生態環境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模式對研究新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意義深遠,它既可以幫助我們從生態學的角度觀察電影中民族社會的形成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而將人類社會和文化視為特定條件下適應和改造環境的產物,同時也促使我們關注文化的意義。因為處在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文化既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前提條件,也是人類應對生態的重要機制。鑒于此,借助文化來認識、利用和改造生態抑或是利用生態影響文化的形成與變化是研究生態人類學與新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關系的出發點。
新疆的生態系統從其存在的形態來看,以天山為界大致形成基于自然生態環境制約的兩個系統——南面是以塔里木盆地綠洲為中心的綠洲生態系統,形成以農耕為主畜牧為輔的文化;西面北面是以伊犁草原、阿勒泰草原為中心的草原生態系統,形成以畜牧為主農耕為輔的文化。為適應生態變化及社會變遷,兩種系統在各自的文化模塑下不僅具有了整體性的特征,而且還通過社會結構、人口分布、風俗信仰、本土知識、生計方式等方面進行自然調節。新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為兩個系統的比較研究提供了足夠的、有力的證據,通過影像內容的展現,可以清晰地認識兩種文化演進的邏輯,展示生態與新疆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依存。
一、綠洲與精神
綠洲是處在干旱半干旱區的新疆特有的生態系統,主要依靠水資源的分布與控制而形成新疆人民賴以生存的具有自動調節和自組織功能的最重要的生活區域。在這個區域中,借助文化,一方面,人與綠洲會形成特殊的關系——或適應或抗爭,并且會對綠洲生態系統會產生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成熟的綠洲生態系統又影響著文化進而作用于人。所以,人與綠洲的自然共生關系是綠洲生態文化的精華所在,在電影中則往往通過水資源的利用、葡萄文化的展示及胡楊文化的保護得到充分表現。
水資源是綠洲生態系統穩定的根本要素,對它的開發和利用是影響綠洲經濟、文化系統的重要指標。人類學家一般認為“在干旱地區人類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管理和利用水資源。”[3]“尋找水源”自然成為新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特殊主旨之一。《沙漠里的戰斗》(1956)是最先反映新疆少數民族地區水利勘探的故事,導演湯曉丹以一支水利勘察隊在尋找水源過程中遇到的重重艱難險阻為情節線索,以發現水源,戈壁灘呈現勃勃生機為結局,借助驚險樣式展示了開發邊疆的生產建設。“大躍進”高潮時期的《黃沙綠浪》(1965)展示的是新疆掀起的“大躍進”圖景,表現“千年黃沙變成綠洲”的人定勝天主題。為做到糧食自給,在“大躍進”形勢鼓舞下人們擺脫自然環境的束縛,自力更生,改沙引水,讓塞外變江南,讓大漠換新裝。特別是影片中所展示的維吾爾族為了減少水蒸發,充分利用地下水的坎兒井灌溉工程,體現了當地人民與自然條件的適應性。《買買提的2008》(2008)則將“尋找水源”與“奧運精神”融為一體,主旋律意味濃厚。曾經生態富饒的“阿拉干河”早已干涸,風沙的蠶食使沙尾村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生存挑戰,“打井”成為沙尾村人維持生存的迫切需求。影片最終通過孩子們的足球隊將村民的心凝聚在一起打出了井水。
上述影片一方面反映出綠洲生態環境的脆弱性與穩定性之間的關系,即水的存在與消失意味著綠洲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穩定與脆弱,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現出人類群體的干預程度也是主宰綠洲生態系統興衰的鮮明主旨。就后者而言,這種主旨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宣揚之下往往會演化成為某種“精神”,電影中對這種精神的依賴與崇敬實際彰顯出綠洲生態系統中水、制度與權力之間的關系。“在綠洲里,誰控制了水源,誰就控制了綠洲社會,也就有了管理綠洲的權利。”[4]在此意義上,電影《大河》(2009)的隱喻意義得以彰顯,如果說在淺層次上百姓對水的既愛且恨(桃花水的危害、冬妮婭的死、塔河勘探的磨難與水的親近感相互交織)超越了宗教作用化為與綠洲社會相共生的神圣情感只是體現出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互動的話,那么在更深層次上影片主要的目的是想通過“解放前自由散漫的塔里木河——解放后建水庫——新時期炸大壩”的情節過程表達“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大河才能被治理”這樣一個基于“水、制度與權力”的關系之上的明顯的意識形態旨歸。
生活在綠洲上的人類為求自身的生存發展,不斷地在生態環境中獲取所需的能量和資源,同時,遵守生態環境的變化的規律,調節自己生活習慣和生產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會對綠洲生態環境產生一定影響,成熟的綠洲生態系統也通過影響自然環境進而作用于人。氣候干旱,光照充足,晝夜溫差大,無霜期長,年蒸發量數百倍于年降水量的生態環境造就了吐魯番獨特的生態景觀——葡萄棚架構成的田野、村鎮和宅院,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唱出的《吐魯番情歌》(2006)頗具意味。作為當地農村社區最基本的生態單元,由葡萄晾房、房屋建筑、葡萄架及房前屋后的巷道毛渠構建而成的“葡萄人家”通過影片得到完整體現,葡萄既為土地遮蔭,還改善居住環境,晾房節約田地資源,每個“葡萄人家”的存在與葡萄的生產相伴相生,充分體現了人與自然相生相諧的生態文化特征。與之相適應,影片還以四首經典新疆民歌《吐魯番的葡萄熟了》《半個月亮爬上來》《阿拉木罕》《掀起你的蓋頭來》與村長“哈力克”家兩代人不同的愛情故事相互交織,且像葡萄串一般串聯起來,體現音樂敘事的強大魅力,也彰顯出“葡萄人家”的生活智慧及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不畏艱難、樂觀向上的性格精神。
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綠洲生態系統中的胡楊是塔里木特有的古老樹種。因其喜光、喜濕、耐寒、耐鹽堿的生物特性,加上在塔里木河流域的面積大、分布集中、保存完整、生命力超常,被人稱為“綠洲人的生命搖籃”。對胡楊的崇拜往往與崇拜蒼天、樹木、大自然及相信萬物有靈的薩滿教以及伊斯蘭教有關, 《古蘭經》告誡人們:“你們應當吃,應當喝,但不要過分,真主確是不喜歡過分者的。”還寫到“在大地上行走的獸類和用兩翼飛翔的鳥類,都跟你們一樣,各有種族的……”。參見《古蘭經》(馬堅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3頁。 它使得胡楊在眾多的綠洲樹種中獲得神性;而如果與生存環境相結合,人與胡楊就會相互受益,人的命運也會與胡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又會使得胡楊獲得人性。《胡楊人》(2008)以艾爾肯與阿瓦古麗的愛情故事為主線,以發展經濟與保護胡楊的斗爭為副線,表達人與胡楊的相互依賴依存。影片中當父親木沙江與兒子艾爾肯之間關于是否開墾胡楊林產生爭議時,父親的話點明了影片的主題——“我們在沙漠邊上生活的人,胡楊就是我們的家,沒有了胡楊就沒有了地,沒有了地就沒有了家,沒有了家還哪里有人呢?”。而片名本身就具有隱喻的價值:胡楊見證了艾爾肯與阿瓦古麗的愛情,阿瓦古麗最終與艾爾肯再續前緣一起留在鐵干里克種樹御風沙;胡楊是艾爾肯的父親木沙江“默默無聞,不屈不撓,不求所得,無私奉獻”人格魅力的象征,為了對年輕時帶領村民砍樹開荒招來黑風暴的行為贖罪,他堅決制止亂砍濫伐,為此將兒子送進監獄;胡楊更是生活在南疆艱苦環境中的維吾爾族不屈不撓的精神寫照。這種通過電影生產方式創造出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胡楊文化”實際上在維吾爾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動中處于核心地位,它與維吾爾族“敬天厚地”的傳統生態倫理觀是相一致的, 其內核為:崇尚自然、敬畏生命,以綠洲生態系統的完整與穩定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條件為前提,承認大自然的完整與多樣性,以道德力量減少或緩解人類與自然的沖突,與自然共生共存。 而且對南疆地域經濟的發展、人文精神的影響、民俗民情的引領都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當然,作為一種精神象征,更是為區域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提供了強有力的文化支持和精神支持。
二、草原與文化
以草原生物之間的能量交換而連接成為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的草原生態系統是天山以北和以西陸地生態系統的主要類型,草場—家畜—人是此生態系統的三要素,放牧是草場與家畜之間實現能量轉換的必要環節,據此,三者之間和諧依賴,促進草原生態系統的發展。所以,“放牧是草原文化的源頭”“沒有放牧就沒有草原文化”,[5]草原民族依賴這種長期與自然相融合的生計方式,在生活方式、社會制度、思想觀念方面逐步形成了游牧民族樸素的草原生態文化。
草場是畜牧業生產的基礎,對草場的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是保持草原生態平衡的主要途徑。生活在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區的哈薩克族自古以來以游牧生產為主,千百年來游牧生活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代代相傳,最終形成較為固定的生態游牧文化。《草原雄鷹》(1963)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哈薩克傳統牧業生產中的草場管理技術經驗,它甚至成為影片敘事的推動力。“如何治療馬病”是影片中所有矛盾沖突的基礎,因為長期在一個地方放牧而導致草場退化是引起馬頻發病的主要原因,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在解決草場同時還要突破防疫治療的缺口”,注重本土經驗的卡德爾積極尋找防疫治療的突破口,大學生阿里則一心開辟新牧場。后來由于阿里的盲目自大,最終導致大量懷孕母馬在春天的暴風雪中流產,給天山牧場帶來嚴重損失。影片從側面反映出草場在畜牧生產中的重要性。因此,為了提高畜牧業生產力以及躲避自然災害,牧民以春、夏、秋、冬四季劃分草場,在嚴格遵循牧場的四季變化和生態特征的條件下,一年中進行4次轉場,不僅解決了牲畜與牧場之間矛盾,而且在流動中保護了生物多樣性。更重要的是,年年歲歲,循環往復,在轉場中他們認識了世界,收獲了生態倫理,完成了生命的循環。《永生羊》(2010)就是以牧場的空間轉換來結構,通過四次轉場的空間剪輯,展現哈力一家的人生之旅。四次轉場完全與情節、情緒融為一體,起到渲染情緒的作用。
對待草場如此,對待牲畜更是如此。《永生羊》實際上反映出哈薩克人草原生態觀的核心,即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解決人與生態環境間出現的問題。為此,以草原生態系統為整體,將生活在草原上的所有生物當做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與之保持平等關系,使之具有人的生命與情感,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所以拉德卡(Joachim Radkau)認為:“人與家畜的關系是一個帶有很深的感情因素的領域,要客觀分析它就會像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的關系那樣困難。”[6]這其中當然不排除對哈薩克族有根深蒂固影響的薩滿教“萬物有靈”論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草原生態文化的影響。所以,關于“羊”,在哈薩克的生活中有著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圍繞著羊形成的草原文化,既涉及哈薩克族的日常世俗生活也深入到神圣生活。在日常世俗生活中羊是重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料,是“四畜”當中最為重要的牲畜,也是牧民的財富象征;在神圣生活中,羊成為向“安拉”獻祭時的供品,同時具備了象征的意味。這兩方面的影響不僅造成哈薩克族的民族心理與羊“本性和性格”上產生了一些相似點,而且還使他們能像對待人一樣,將羊作為道路上的朋友,生活中的樂趣。所以《永生羊》中宰殺羊之前的“你死不為受罪,我生不為挨餓,原諒我們”的復雜表達,既有對生命的敬畏,同時充滿感謝,正是羊的死成全了人的生,生命因此獲得永生。而恰恰就在這不斷的生死輪回之中,世間的一切才得以生生不息。哈薩克族也以同樣的方式對待“馬”,把馬當作人來對待,人對馬的情感也是對人的情感,有時甚至可能超越對人的情感,體現出一種更博大的精神境界。《美麗家園》中駿馬“玉頂黑”不僅是阿曼泰與瑪依拉之間的感情紐帶,與人物的命運息息相關,而且最終以宰殺“玉頂黑”完成對已故父親胡納泰的祭奠方式映襯出“玉頂黑”的人性,動人且情感效果突出。可見,以草原為家,視水草為血液,視牲畜為家庭成員確實早已成為哈薩克族影響自然、融入自然的觀念形態,它在人、牲畜、草場之間的交替輪回中真正體現出哈薩克族的草原文化觀。
三、基于草原的游牧本土知識
人類學中的“本土知識”概念主要是指長期生活在一定區域內的人群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共同構建的一套知識體系,其根本是根植于當地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也有人稱其為“地方生態知識”(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草原哈薩克族的“本土知識”是他們在放牧牲畜、利用草原的過程中傳承積累起來的游牧社會知識以及對待生存環境的態度。這套知識通過民間故事、諺語、禁忌及電影等形式滲透到日常的生產生活中得以延續。“黑鳥出山,星月無光,這是暴風雪的征兆。”(《風雪狼道》)多少年來總結出來的抗雪救災經驗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做出了巨大貢獻。《草原雄鷹》與《天山的紅花》中除了上文所述反映出哈薩克傳統牧業生產中所包含的草場管理技術的經驗之外,畜群管理技術及對自然災害與畜病防治的本土知識也是電影的亮點之一。《草原雄鷹》中主要人物是圍繞“理論與實踐如何結合?”的問題來塑造的,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能否與本土知識相結合、能否積極向牧民學習。阿里與阿米娜空有一套大學學來的理論知識,不與本土知識結合,最終遭批判;而卡得爾之所以被稱為“山鷹”,是靠自己多年的勤奮好學——盡管是中專文化,但積極向當地牧民學習本土經驗,他除了向各種馬的疾病作斗爭,也向獸醫學習土法治療,并從實踐中加以總結。土法偏方與科學研究相結合,救活了伊犁馬,救活將死的被阿米娜放棄的馬駒,戰勝各種馬的疾病。卡德爾與阿里分歧的實質就是如何對待本土性畜病防治知識,只不過這種分歧在當時被“兩條路線”斗爭遮蔽了而已。本土知識特別對干旱、風暴、白災、黑災等自然災害應對有效,所以在電影中也出現了諸多的避災、防災、減災的內容。卡德爾的調查和老百姓的傳說都顯示黑山風雪大,但都被阿里譏諷為迷信,他不聽牧民勸阻私自勘察黑山新草場,不注意新草場的水源、地形、氣候,私自將馬群調往黑山,最終遭遇暴風雪,導致懷孕的母馬流產,給牧場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天山的紅花》(1964)的背景是“三面紅旗”時期,牧場屬于集體財產,影片多次出現集體打牧草的場景,為的是冬季牲畜能夠吃到干牧草;在產羊羔的春季,突然遭遇暴風雪,社員們與技術員同心協力抗寒防凍,防止肺炎蔓延,備好治療羊羔肺炎的藥品。這些都為情節的進一步展開埋下伏筆。以上兩部電影從側面反映出游牧本土知識與草原生態系統的相互協調關系,顯示游牧本土知識業已成為草原牧業抗災保畜的基礎及重要保障。
四、環境塑造下的多元生計策略
依賴于一個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而采取的謀生方式或手段稱其為“生計方式”,因環境多樣化的影響而具有社會性、文化性及多樣化的特征,成為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生存模式。獲取食物是人類最重要的生計,在獲取食物的過程中人類創造了豐富的文化。“自然環境并不產生文化,而是穩定文化的因素;賦予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因素是經濟形態,尤其是食物的獲取手段,即表現于部落生活中最顯著的地域性特征,乃是食物的獲取。由于食物領域的不同,與食用習慣有密切關系的工具及房屋、服飾等也不相同。”[7]所以,任何民族的生計方式都是在特定的生態條件中建構起來的,綠洲生態系統與草原生態系統從本質上造就了兩種不同的生計方式——農耕與游牧,也造就了他們不同的文化選擇,所以,從根本上來說,一個民族的生計方式是一種文化選擇。
維吾爾族的生計方式屬于“綠洲耕牧型”[8],在干旱地區的綠洲上,以種植農作物、瓜果為主,雜有畜牧因素,所以我們在新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見到的農業場景成為維吾爾族的主要生活場景,早期如以農村合作化運動為背景的《綠洲凱歌》(1959)和以“大躍進”為背景的《黃沙綠浪》,前者因取材于以維吾爾族為主體多民族聚居的極干旱地區獨特自然生態環境與綠州文明典型代表的吐魯番,而命名為《綠洲凱歌》;后者以“糧食自給”為動力,講述在“大躍進”形勢鼓舞下維吾爾族農民擺脫自然環境束縛自力更生的故事。近期則以《吐魯番情歌》及《胡楊人》為代表,前者充分表現吐魯番特殊的自然生態條件與吐魯番居民選擇以種植葡萄為生計之間的關系,展示吐魯番人尊重自然,自覺利用自然規律,與當地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的葡萄文化;后者也通過艾爾肯學習農業知識、考察南疆沙漠種棉花的可行性、致力解決缺水缺地等問題,側面反映新疆“一黑一白”經濟戰略對維吾爾農民的深刻影響。
盡管自然環境是一個民族選擇生計方式的重要依賴,但從特定意義上說,依賴于社會環境的協調而對一個民族環境的選擇利用、加工改造及文化模塑的作用更大,進而對生計方式產生影響。“與自然環境相比,社會環境對民族生計方式形成的影響更為直接,無須經過預先加工就可以直接作用于該民族的生計方式。但社會環境對民族生計方式的影響缺乏穩定性,因為社會環境的變化速度比自然環境要快得多,數十年間一個民族的社會環境可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而自然環境卻可以延續數百上千年也不會發生明顯的變化;社會環境對民族生計方式的作用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9]也就是說,長期以來依賴生態環境所建立起的穩定的生計系統在社會變遷中會遭遇強大沖擊,會改變原有資源利用方式及文化選擇,甚至會形成新的生計方式,而與原有生計系統產生文化上的沖突。
傳統社會中以游牧為生計的哈薩克族一直以來所形成的“草原文明”在《美麗家園》(2005)中遭遇到現代社會沖擊,從而形成影片的敘事張力。影片中父親胡納泰、嫂子加娜與大學生瑪依拉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就是兩種生計方式選擇上的沖突,而阿曼泰的兩難選擇——選擇與戀人瑪依拉生活在城市還是遵從父命娶了嫂子固守家園——則表達了游牧民族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遭遇的困境。這個困境在兩人初次約會時就表露無遺:
瑪依拉:阿曼泰,你是不是打算在草原上放一輩子羊?
阿曼泰:這我沒想過,放羊有什么不好嗎?我們哈薩克人世世代代不是就這樣生活的嗎?
瑪依拉:對比草原我還是喜歡城里的生活。
阿曼泰:瑪依拉,我想你要能留下來多好。
瑪依拉:這不可能。阿曼泰,我覺得你也應該到城里去看看。其實,夏牧場離城市也不算遠。騎馬走近路半天就能到。
后來,當瑪依拉為找工作的事一籌莫展時,這種對比更加明顯:
阿曼泰: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回草原嘛,那里有牛有羊,餓不死我們。
瑪依拉:每天六點鐘起床,擠奶子打酥油,一日三餐,劈柴洗衣,就和你嫂子一樣忙到深夜才能睡覺,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唱歌,唱歌是我的生命。我必須留在城里。
瑪依拉最終選擇嫁給了城里的男同學,嫂子加娜拒絕了郵遞員海拉提的求婚,遵循父命留在山上,而阿曼泰選擇了離開和買車,這些都預示著傳統生計方式在面對現代生計方式沖擊時的脆弱無比。這樣看來,阿曼泰在影片開始時所說“父親說過,哈薩克人的靈魂是屬于草原的,他也希望我能夠屬于草原,可是我卻讓父親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這是我心里永遠的傷痛,我不知道,我對生活的選擇與追求是否正確,我只覺得人應該往前走。”更加映襯出阿曼泰在與傳統生計方式告別時的矛盾心理和復雜情感。
相同的困惑也發生在《牧漁人》(2011)中,只不過這個困惑的對象轉變成了“游牧”與“定居”。牧民哈斯木愁于下山后無法生活,堅持傳統生計方式不去定居點,成了山上的唯一的釘子戶。后因為孩子上學、妻子生病等問題無法解決,被迫下山。定居后的哈斯木嘗試著擺脫游牧生計方式,通過發展家庭養殖漁業,很快改善了家庭生活條件,融入到了現代生活之中。在這里,哈斯木的困惑只不過是表象而已,由“我們哈薩克族什么時候養過魚?”到“早知道定居點是這樣,我早就搬下來了”,彰顯出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也反映出政府實施的“定居興牧”民生工程的影響遠遠超過了長期以來自然生態環境對牧民的影響,它帶動了更多的哈薩克族牧民走上轉型之路。值得注意的是,電影中最終引導哈斯木轉向“牧漁”的是來自南方的技術員,這從另一側面表明,許多年以來新疆綠洲始終被現代社會的生計方式和內地生計系統影響,新的文化因素同時也進入了新疆綠洲,這也成為新疆綠洲社會變遷的強大力量。至此,《美麗家園》中所形成的敘事張力在這里完全被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社會環境化解了。
結 語
毋庸置疑,生態人類學與新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關系密切,一方面,生態人類學視野與中央新疆工作會議精神中的民族團結、共同繁榮、堅持可持續發展、環保優先生態立區的總體定位與發展目標相適應,與新疆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文化生態資源相匹配。另一方面,在如今這樣一個虛擬和現實正在發生倒轉的“影像社會”中,影像已經“成為我們最后安放文化遺產的地方”[10],新疆少數民族文化借助影像化可以準確地把握文化適應、生理適應、環境適應的發展邏輯,并找出調適的手段。當然,生態人類學的理念也可以在新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升華成為一種創作理念,以生態整體觀為根本,消解人類中心主義,復活自然作為生命體的本來面貌,表達生態理想,重建精神家園,從而具有了“母題”的價值與意義。
參考文獻:
[1] 尹紹亭.人類生態研究的歷史與現狀[C]//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中國民族學縱橫.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19.
[2] 〔英〕凱·米爾頓.多種生態學:人類學,文化與環境[C]//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人類學趨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320.
[3] Emilio F. Moran. The Ecosystem Concept in Anthropology[M].Westview press, 1984:205.
[4] 崔延虎.綠洲生態人類學研究的若干問題[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1(02).
[5] 任繼周.放牧,草原生態系統存在的基本方式——兼論放牧的轉型[J].自然資源學報,2012(08).
[6] 〔德〕約阿希姆·拉德卡.自然與權力:世界環境史[M].王國豫,付天海,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63.
[7] 石川榮吉,佐佐木高明.民族地理學的學派及學說[J]. 尹紹亭,譯.民族譯叢,1986(05).
[8] 林耀華.民族學通論(修訂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95.
[9] 羅康隆.論民族生計方式與生存環境的關系[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4(05).
[10] 明江.民族電影:影像時代的非遺安放之所[N].文藝報,2014-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