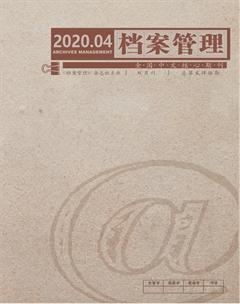堅守與拓展:中國檔案學研究邊界探析
趙春莊
摘? 要:明確檔案學的研究邊界是保持檔案學科獨立性的基本要求,檔案學研究邊界的確立應采取“堅守為主、拓展為輔”的策略,堅持“在拓展中堅守、在堅守中拓展”的基本原則,重點應在理論聯系實際、學科獨立、核心概念與理論、學術評價與反思等方面堅守底線,并在研究方法、學科體系、學科功能等方面進行適度拓展。
關鍵詞:檔案學;研究邊界;堅守;拓展
Abstract: Defining research boundary of archives science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to maintain the independence of archival discipl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archival research boundary should be based on stand fast, not being based on expansion, and insist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ersistence in the expansion and expansion in the persistence. The key point should be to stick to the bottom line in the aspects of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discipline independence, the core concepts and theories,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reflection and so on,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discipline system and discipline function and other aspects appropriately.
Keywords: Archives science; Research boundary; Persistence; Expansion
1 前言
檔案學研究邊界問題關乎檔案學科的獨立性、科學性和適用性,迫切需要從理論上加以研究和回應。“從國外 2015 檔案年會主題分析來看,國外同行開始立足宏觀層面,理性思考當下和未來檔案及檔案專業的邊界問題。最典型的是澳大利亞 2015 年會設置了‘檔案的邊界主題,運用前瞻性眼光,來審視檔案的本質以及檔案專業的核心價值和業務。”[1]筆者以“檔案學+研究邊界”為檢索詞,以篇名為檢索項,在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中進行模糊檢索(檢索時間2020年3月20日),共得到2篇相關研究論文,分別為周毅的《變革時期檔案學研究邊界的適度拓展》(以下簡稱《周文》)和張霞、吉萍的《檔案學跨學科研究的邊界:以“問題”為導向的復雜網絡邊界劃法》,此外,我國學者馮惠玲、黃霄羽、于海娟、崔文健等也對該問題進行過研究和論述。檔案學研究邊界的確立需處理好“堅守與拓展”的矛盾關系,采取“堅守為主、拓展為輔”的策略,堅持“在拓展中堅守、在堅守中拓展”的基本原則,重點應在理論聯系實際、學科獨立、核心概念與理論、學術評價與反思等方面堅守底線,并在研究方法、學科體系、學科功能等方面進行適度拓展。
2 檔案學研究邊界的涵義解析
在現有的研究文獻里,關于檔案學邊界的涵義還未有具體闡述,筆者在此僅是個人的一些理解。檔案學研究邊界是指由檔案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客體和研究內容所規定的研究范圍,也即是檔案學研究對象、研究客體和研究內容所涉及的全部事物。這里的研究邊界并不是常規意義的靜態的物理邊界,而是動態的、抽象、不斷調整的邏輯邊界,它隨著研究對象、研究客體、研究內容的變化而變化。研究對象是研究客體、研究內容、研究邊界的聚焦,是研究客體、研究內容、研究邊界的抽象與概括;研究客體是指研究對象所涉及的具體領域的客觀事物;研究內容則是與研究對象有關的各種事物,包括主體、客體,學科體系、研究方法等。“研究內容可以用本學科的理論作基礎,也可以用其他學科的理論作基礎,甚至兼而有之,因此各學科的研究內容可以有交叉,但研究對象絕對不能交叉,否則就會喪失學科的獨立性。”[2]由此可見,檔案學研究對象規定著檔案學的研究客體、研究內容和研究邊界,檔案學邊界問題的研究,首先要從檔案學研究對象開始,探索檔案學研究對象與檔案學研究邊界(也可稱為檔案學科邊界)的關系。
“1956年,檔案學被列入《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草案)》,正式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標志著學界開始真正對檔案學研究對象進行有意識的思考和探索。”[3]1957 年程桂芬在《關于檔案學問題》中指出:“檔案學是研究檔案文件和檔案工作的發展歷史以及全部檔案工作實踐活動的理論體系。”[4]1981年吳寶康先生在《三十年來我國檔案學的研究及其今后發展》中指出:“檔案學就是以檔案和檔案工作這一現象領域內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5]1986年吳寶康先生在《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一書中指出:“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研究檔案和檔案工作領域內有關檔案的科學管理和提供利用的客觀規律以及檔案工作的歷史發展規律。”[6]到了1988 年,吳先生對檔案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進一步的簡化,指出:“檔案和檔案工作是檔案學的研究對象。”[7]1989年,任遵圣在其主編的《檔案學概論》中指出:“檔案學是以檔案、檔案工作和檔案事業為研究對象,并探索研究對象的結構、功能、運動規律以及與其相關學科相互關系的一門科學。”[8]在20 世紀 90 年代有關檔案學研究對象的問題開始出現了新的觀點。如1994年陳永生指出:“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檔案現象及其本質規律。換句話說,檔案學就是研究檔案現象及其規律的科學。”[9]這一說法,顯然較此前的提法更為簡潔和抽象。2006年,馮惠玲、張輯哲在第二版《檔案學概論》中,也認為:“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檔案現象及其本質和規律。”[10]直到現在該觀點仍是學界的主流認識。
綜上所述,我國檔案學界對檔案學研究對象的認識大致可以概括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是把檔案、檔案工作和檔案事業作為研究對象;第二種是把檔案、檔案工作和檔案事業的運動過程及規律作為研究對象;第三種是把檔案現象及其本質和規律作為研究對象。第一種情況研究對象屬于具體的客觀事物,研究邊界較為清晰,第二、第三種情況研究對象比較抽象和概括,研究邊界日益模糊。因此檔案學研究對象與檔案學研究邊界就存在這樣一種關系,即研究對象越抽象,研究邊界越模糊,反之,研究對象越具體,研究邊界越清晰。
3 檔案學邊界問題的研究歷史與現狀
學科邊界是學科構建和開展學術研究的范圍,因此檔案學研究需要從歷史和發展的角度審視檔案學研究邊界問題。《周文》“圍繞著檔案學研究邊界為什么需要拓展,以及在研究邊界拓展過程中如何處理檔案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等重大理論問題進行了論述,并從分析競爭、協作、變化與用戶等四個因素入手(簡稱4C),研究了檔案學邊界拓展的基本趨勢,討論了檔案學研究邊界拓展的三個基本原則”[11]。張霞、吉萍在《檔案學跨學科研究的邊界:以“問題”為導向的復雜網絡邊界劃法》一文中指出,“檔案學邊界具有多維復雜性、模糊關聯性和適度整合性,提出了以‘問題為導向的復雜網絡邊界劃法”[12]。
此外,關于檔案學研究邊界問題,其他學者在其相關研究論文中也有所涉及。例如馮惠玲、周毅在《檔案學科的“十五”回顧與“十一五”展望(續)》中指出:“隨著檔案管理活動技術含量的提高和社會對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利用提出的全新要求,檔案學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的內容都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與充實。在這個過程中,檔案學的學科邊界可能會發生以下顯著變化:一是從研究檔案的運動與管理擴展到研究文件(含檔案)運動的全過程及其管理;二是從研究文件與檔案信息管理擴展到同時關注各種有形信息以至隱性知識的管理;三是從重點研究傳統管理理論與方法擴展到關注大量技術應用及其帶來的理論創新;四是從研究文件信息流的管理與重組擴展到對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本身進行研究。”[13]黃霄羽、于海娟、崔文健在《腳踏實地應變固本,仰望星空期許愿景——據 2015 年檔案年會主題分析國外檔案工作的最新特點和趨勢》(發表于《檔案學研究》2015年第3期)中提出:“面對學科交叉與融合的發展趨勢,如果缺乏理論層面的探討和總結,檔案專業的邊界有可能變得模糊,專業發展將會面臨走入歧途的風險。”[14]另外,黃霄羽在《核心概念宜立邊界,支柱理論方護根基——“來源觀”的演變及其特點和影響評價》中也有相關內容的論述,該文提到:“從19世紀至今,來源觀經歷了實體來源觀、概念來源觀和社會歷史環境來源觀三個歷史演化過程,依據它們對來源理解和界定的表述,當前來源概念呈現內涵日趨抽象和外延邊界日益模糊的特點,給檔案學研究帶來了潛在風險,因此來源概念需擴展卻不宜喪失邊界。”[15]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我國檔案學界已經開始關注檔案學研究邊界問題,并在研究邊界拓展的原因、原則、領域、方法、核心概念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學科交叉與融合的背景下,如何既能保持檔案學科的獨立性、又能在研究邊界上適度拓展,如何在學科交叉融合中保持本學科的專業特色,如何劃分檔案學的研究邊界,如何在劃分檔案學研究邊界過程中處理“堅守與拓展”的關系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認真研究和探討。
4 檔案學研究邊界拓展中的堅守
4.1 基本原則:堅守理論聯系實際。檔案學理論由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兩部分組成,“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是在檔案管理領域普遍起作用的基本規律,它是有關檔案、檔案工作及檔案學自身的本質特點和客觀規律的、高度抽象概括的知識體系”[16]。由此可見,檔案學基礎理論用于揭示檔案現象及其本質和規律,對檔案實踐具有間接的指導意義。檔案學應用理論是關于“怎么做”的理論,研究具體的檔案工作策略、措施、方法、操作手冊等,對檔案工作實踐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檔案學基礎理論是對檔案學應用理論的高度抽象,檔案學應用理論是對檔案學基礎理論的具體化,它們都來源于檔案工作實踐,就像一臺機器,基礎理論研究的是機械原理,應用理論探討的是操作手冊,兩者的功能不同。
“實踐——理論——實踐的圖示概括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基本內容和過程,它包含著兩個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層次:實踐——理論、理論——實踐。前者就是所謂認識世界(理論探討),后者就是所謂改造世界(理論應用)。顯然,完整意義上的理論聯系實際應包括理論的來源和理論的應用兩個方面。”[17]也就是說,檔案學理論來源于檔案工作實踐,但同時也要回到實踐中去,指導實踐并接受實踐的檢驗,這一過程也即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過程。
由于檔案實踐的變化,新的檔案現象和問題不斷涌現,檔案學研究邊界也在不斷拓展當中,檔案學理論工作者具有較強的思辨和理論概括能力,但缺乏對具體實踐工作的經歷和了解,實際工作者對檔案工作實踐了如指掌,知道實踐中需要哪些理論,但理論抽象、概括能力相對較弱,因此檔案理論工作者與實際工作者應該精誠合作、相互理解和支持,做到檔案學理論與實踐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防止盲目拓展研究邊界,共同推進檔案學理論與實踐工作的發展。
4.2 基本底線:堅守學科獨立性。在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關于檔案學獨立性問題學界一直未達成共識,“1956年國務院制定和頒布了兩個文件,對檔案學獨立性的討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是國務院《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該文件明確指出國家檔案局和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對檔案學及其輔助科目,應加強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學水平;二是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制定的《一九四五—一九六七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該文件明確把檔案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列入了科學規劃”[18]。從此以后,檔案學是一門獨立學科的觀點逐漸占了上風。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如果不以觀點的完全一致而是以某種觀點占據絕對優勢為衡量標準,關于檔案學是一門獨立學科的觀點在檔案界才最終達成共識”[19]。
檔案學基礎理論規定著檔案學的研究邊界,也是保持學科獨立性的理論基礎。但是在各種學術成果中屬于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范圍的寥寥無幾。例如:筆者以“檔案”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進行題名檢索(檢索時間為2020年3月22日),共獲得博士論文61篇,但是其中沒有一篇屬于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范疇。“2005至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云南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上海分院等高校共有檔案學科博士論文選題62個,其中屬于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的選題僅有2個,占3.22%。而且檔案學專業博士論文題目中不見‘檔案二字的現象有增加趨勢。”[20]檔案學基礎理論是檔案學科獨立的根基,基礎理論研究的缺乏勢必對檔案學科發展與獨立性產生不利影響,檔案學研究邊界拓展應以保持檔案學科的獨立性為基本前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以損失檔案學科獨立性為代價盲目拓展檔案學科邊界,這是檔案學科發展的基本底線。
4.3 生存之本:堅守核心概念與理論。沒有理論就不能稱之為科學,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身的理論體系,而核心概念與理論則是學科理論構建的邏輯起點。來源原則、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和檔案鑒定理論是檔案學的三大支柱理論,而來源原則可稱作檔案學的核心支柱理論,來源可以稱作檔案學的核心概念。因為只有堅持來源原則,才能保證檔案與形成者的歷史聯系,才能確保檔案的本質屬性(原始記錄性)。檔案的本質屬性是檔案價值的源泉,是檔案學科構建的價值基礎,是保持檔案學科獨立性的基本條件,也是檔案學科屹立學科之林的生存之本。
“來源原則的基本內容可以歸納為三個基本點,即尊重來源、尊重全宗的完整性、尊重全宗內的原始整理體系。”[21]黃霄羽在《核心概念宜立邊界,支柱理論方護根基——“來源觀”的演變及其特點和影響評價》(發表于《檔案學通訊》2014年第5期)中“梳理了 19 世紀至今來源觀演變的三個階段,即實體來源觀、概念來源觀和社會歷史環境來源觀”[22]。從來源概念的演化可以看出,來源概念的內涵從具體變得抽象,從單一變得復雜,從靜態轉向動態,來源概念的邊界從清晰變得模糊。學者們結合檔案實踐,不斷推動理論創新的精神值得贊賞。但是,這種理論的創新也使得檔案學研究的邊界日益擴展和模糊,如果繼續這種擴展,檔案學的核心概念將面臨挑戰,檔案學科也將面臨生存危機。因此,無論檔案學的概念和理論如何拓展、演化和變遷,檔案學研究都應堅守其核心概念和理論,否則,檔案學研究就可能走向歧途。
4.4 基本動力:堅守學術評價與反思。“學術評價是對評價對象是否符合一定的學術標準及符合程度做出判斷的學術活動。”[23]應該說,學術批評、學術評論都屬于學術評價的范疇,“學術批評是專門針對學術研究的體制、方法、指導思想、學術研究氛圍、學風以及各類研究成果進行的批評,它對學術研究具有辨明方向的作用;學術評論是緊緊圍繞特定的成果進行的,它的結果只是對原有成果的推介、評論、批評,最終使成果得到提高”[24],學術評論不僅具有學術批評的功能,而且具有宣傳推介研究成果的功能。學術評價是學科健康發展的基本動力,它既是一種約束機制,也是一種激勵機制,從一定意義上說,任何學科進步與理論的發展過程,都是學術評價和反思的過程,學術評價“首先是為了學術建設,其次是為了學術公益,再次是為了學術交流,最后是為了激濁揚清”[25]。
“反思是主體對自身運動(經歷)進行反復思考以求把握其實質的一種思維活動。”[26]這里的主體指的是學科共同體,只有學科共同體對自身學科發展歷史的反思才能稱為反思,如檔案學科共同體對檔案學進行的反思。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檔案學界曾經出現過一次反思的熱潮,但在80年代末期冷卻之后,“人們就不怎么再講反思了,似乎反思是必然與觀點的偏頗、立場的錯誤連在一起的”[27]。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反思既有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功能,也有總結經驗教訓和規律,探索學科定位及未來發展方向的功能。
學術評價與反思是推動檔案學科健康發展的不竭動力,通過學術評價與反思,可以辨明學科發展方向,明確學科定位和研究邊界。眾所周知,中國檔案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根本原因在于其獨特的研究對象與功能,如果繼續盲目地拓展檔案學的研究邊界,脫離了檔案學研究對象所規定的研究范圍,檔案學科就可能失去自身特色。因此,我國檔案學研究應立足于中國的檔案工作實踐,認真評價與反思中國檔案學的發展歷史及現狀,深刻反思中國檔案學的發展方向、研究邊界及生存空間,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推進檔案工作和理論的創新。
5 檔案學研究邊界堅守中的拓展
5.1 拓展檔案學的研究方法。“方法是人們為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達到某種目的所采取的方式、程序和手段的總和。”[28]科學研究方法是指正確進行科學研究的理論、原則和手段,也即是人們在進行科學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它是人類長期進行科學實踐的結晶。檔案學研究方法是指檔案學研究者和檔案工作者在開展檔案學研究中所使用的理論、原則和方法,它是檔案實踐的結晶和檔案學研究的工具。研究方法是檔案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規范性直接反映著檔案學研究的科學化水平,科學選擇和使用檔案學研究方法對檔案學研究和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于各種各樣的檔案學研究方法,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標準進行類別劃分,國內主要存在以下幾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層次論”觀點。主張檔案學研究方法應分為相互關聯的四個不同層次。“即第一層次是哲學方法;第二層次是檔案學的綜合方法,包括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第三層次是檔案學的一般方法,包括概念分析、調查、觀察、實驗、統計、科學抽象、歷史方法等;第四層次是檔案學的專門方法。”[29]二是“雙定法”觀念。“即按照固定與定量的標準將檔案學研究方法劃分為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30]三是“三層次說”。“即從方法論的角度,按照普遍性程度和使用范圍,將中國檔案學研究方法體系分為哲學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特殊的專門研究方法三個組成部分。”[31]該觀點是目前學界比較一致的觀點。
由于檔案實踐變遷和檔案學研究發展的需要,我國的檔案學研究方法也在不斷拓展當中。研究方法只是學科研究的工具,檔案學研究方法的選擇和使用取決于所研究的問題,因此,檔案學研究方法的拓展應以研究問題的需要而拓展,不應盲目地引進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同時,還應注意區分檔案學研究方法和檔案工作方法,檔案學研究方法是指研究的思維方式,而檔案工作方法是指具體的工作方式和手段。兩種方法的拓展都應以研究的問題為導向。當前,我國檔案學研究應堅守歷史主義的方法,并靈活運用定性和定量兩種研究方法,以提升檔案學研究的科學性、規范性。關于什么時候采用定性方法什么時候采用定量方法,主要取決于所研究問題的性質。
5.2 拓展檔案學的學科體系。陳永生認為:“檔案學體系,是指檔案學內部分支學科構成的有機整體,它的實質是檔案學的內部結構,而中心問題是檔案學內部各學科分支的劃分和歸屬。”[32]檔案學的學科體系問題是檔案學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也是檔案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對檔案學科體系的研究有利于人們了解檔案學發展的整體狀況,有利于檔案學沿著科學的道路發展。那么,如何構建一個科學、合理的檔案學科體系呢?至少應滿足以下幾個要求:一是滿足和適應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需要;二是揭示出檔案學的整個內部結構,反映學科發展的基本趨勢;三是核心科目應體現檔案學科特色;四是說明各門分支學科的聯系和區別,保持各分支學科之間邏輯的嚴密性;五是“應當反映出檔案學的各門分支學科在檔案學總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各門分支學科的研究對象和任務”[33]。
檔案學科體系的拓展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分支學科數量的拓展,即由于學科研究領域和研究問題的拓展而分化出的新的分支學科,如檔案專業史學、電子文件管理學、計算機檔案管理學等。新的分支學科一般具有完整的知識體系和理論建構,以及獨立的研究對象和自身特色。二是由于檔案工作實踐變化而引起的各分支學科內部知識結構、理論構建、體例結構的調整、充實與更新。例如檔案管理學、檔案文獻編纂學、檔案保護技術學等檔案學分支學科也在不斷修訂、調整、充實和拓展當中。
5.3 拓展檔案學的學科功能。從功能的內涵來看,功能是“對象能夠滿足某種需求的一種屬性”[34]。對檔案學來說,功能也可以理解為客體對主體的有用性,“它是主體(檔案利用者及其利用需求)與客體(各不同時代產生的各種類型、載體、內容的檔案)之間關系的范疇”[35]。因此檔案學科功能是指檔案學研究對國家、社會組織或個人的有用性。檔案學科的功能拓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表現在人們對檔案學科功能認識的不斷深化。筆者以“檔案學+功能”為檢索詞,以篇名為檢索項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進行精準檢索,檢索時間為2020年3月23日,共獲得相關研究文獻17篇。其中,陳永生在《檔案學功能探索——兼論檔案學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發表于《湖北檔案》1991年第3期)中指出:“檔案學對檔案和檔案工作具有解釋功能、預測功能和指導功能。”[36]楊桂仁認為:“檔案學理論具有預見作用和現實指導作用。”[37]林清澄、尹晉英認為:“檔案學理論具有對實踐的指導功能、預見(測)功能和解釋功能。”[38]此外,胡鴻杰在《中國檔案學的理念與模式》中系統論述了“檔案管理學、檔案文獻編纂學、檔案保護技術學和檔案學概論的結構與功能”[39],使中國檔案學的結構與功能認識引向深入。孫大東在《中國檔案學功能的方向問題研究》(檔案學通訊,2016年第5期)中指出,“以默頓的負向功能論為依據,中國檔案學的功能存在方向問題,其可分為正向功能和負向功能”[40],使得檔案學界對檔案學科功能的認識進一步深化。
二是由于檔案學科體系的拓展而引發的檔案學科功能的拓展。檔案學科功能是檔案各分支學科功能的集成,不同的分支學科具有自身獨特的功能。如“檔案學概論主要研究檔案現象及其本質和規律;檔案管理學主要研究檔案的管理過程、程序與方法;檔案文獻編纂學主要研究檔案資料的匯編、考證、出版與傳播;檔案保護技術學主要研究檔案載體和內容安全;檔案史學主要研究檔案學的形成、發展及其規律”[41]。因此檔案學科功能的拓展取決于檔案學科體系的拓展,由于檔案實踐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新的分支學科不斷涌現,檔案學科體系也在不斷擴展之中,從而導致檔案學科功能不斷拓展。
參考文獻:
[1]黃霄羽,于海娟,崔文健.腳踏實地應變固本,仰望星空期許愿景——據 2015 年檔案年會主題分析國外檔案工作的最新特點和趨勢[J].檔案學研究,2015(3):114.
[2][3]潘連根.論檔案學的研究對象[J].檔案與建設,2016(6):5.
[4]程桂芬.關于檔案學問題[J].檔案工作,1957(1):27.
[5]吳寶康.三十年來我國檔案學的研究及其今后發展[J].檔案學通訊,1981(2):5.
[6]吳寶康.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108.
[7]吳寶康.檔案學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232.
[8]任遵圣.檔案學概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47.
[9]陳永生.檔案學論衡[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8.
[10]馮惠玲,張輯哲.檔案學概論[M].2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93.
[11]周毅.變革時期檔案學研究邊界的適度拓展[J].檔案學通訊.2007(4):21.
[12]張霞,吉萍.檔案學跨學科研究的邊界:以“問題”為導向的復雜網絡邊界劃法[J].山西檔案,2019(05):33-39.
[13]馮惠玲,周毅.檔案學科的“十五”回顧與“十一五”展望(續)[J].檔案學通訊,2005(5):4.
[14]黃霄羽,于海娟,崔文健.腳踏實地應變固本,仰望星空期許愿景——據 2015 年檔案年會主題分析國外檔案工作的最新特點和趨勢[J].檔案學研究.2015(3):114.
[15]黃霄羽.核心概念宜立邊界,支柱理論方護根基——“來源觀”的演變及其特點和影響評價[J].檔案學通訊.2014(5):23.
[16]何嘉蓀,潘連根.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發展的正確道路[J].檔案學通訊,1999(5):23.
[17][18][19]陳永生.檔案學論衡[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121,28,29.
[20]馮惠玲,周毅.關于“十一五”檔案學科發展的調查和“十二五”發展規劃的若干設想[J].檔案學研究,2010(5):9.
[21]馮惠玲,張輯哲.檔案學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47.
[22]黃霄羽.核心概念宜立邊界,支柱理論方護根基——“來源觀”的演變及其特點和影響評價[J].檔案學通訊,2014(5):23,25.
[23][24]王協舟.基于學術評價視閾的中國檔案學闡釋與批判[M].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09:15,16-17,82.
[25]楊玉圣,張保生.學術規范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1.
[26][27]陳永生.檔案學論衡[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22.
[28]王協舟.基于學術評價視閾的中國檔案學闡釋與批判[M].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09:15,16-17,82.
[29][30]計嘯.論檔案學的研究方法[J].湖北檔案,1993(1):16.
[31]王協舟.基于學術評價視閾的中國檔案學闡釋與批判[M].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09:87.
[32][33]陳永生.檔案學論衡[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45,49.
[34]國家標準總局.價值工程基本術語和一般工作程序(GB 8223-87)[S].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1988:2.
[35]馮惠玲,張輯哲.檔案學概論[M].2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47.
[36]陳永生.檔案學功能探索——兼論檔案學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J].湖北檔案,1991(3):8-9.
[37]楊桂仁.從檔案學理論的層次和功能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問題[J].浙江檔案,1991(7):16-17.
[38]林清澄,尹晉英.檔案學理論的三種功能[J].北京檔案,1997(2):25.
[39]胡鴻杰.中國檔案學的理念與模式[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40-141.
[40]孫大東.中國檔案學功能的方向問題研究[J].檔案學通訊, 2016(5):21.
[41]胡鴻杰.中國檔案學的理念與模式[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40-141.
(作者單位:河南理工大學檔案館 來稿日期:20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