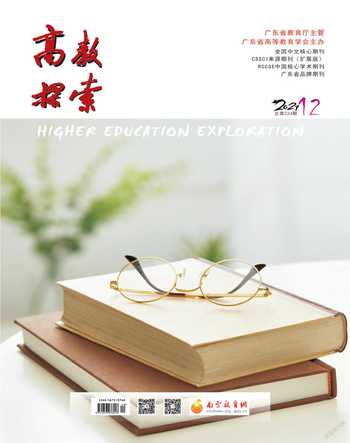澳大利亞霍克政府高校招生錄取制度改革述評
黃松青 顏廷
摘要:1983年澳大利亞霍克工黨政府上臺后,在致力于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的同時,亦高度重視高校入學機會的公平分配,因而對入學新生的種族、階層、性別、地域等給予特殊關注,并為增加社會弱勢群體學生的高等教育代表性在招生錄取制度上采取了一攬子改革新舉措。改革通過頒布入學機會均等政策、建立基于收入還款的學費制、大力拓展高校入學途徑、制定公平的戰略目標等手段,切實改善了社會弱勢群體學生的高校入學機會,對澳大利亞社會經濟發展與多元文化建設也產生了積極影響,但同時也存有一定的問題與挑戰。
關鍵詞:澳大利亞 ;霍克政府;招生錄取制度;弱勢群體;教育公平
作為當今世界教育發達國家之一,澳大利亞極為重視學生群體的社會結構,致力于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高校入學機會,力求實現高等教育中社會各群體的比例代表制,即每一目標群體在大學生中的比例要與其占人口總數的比例相等。為實現這一目標,澳大利亞確定了六大高等教育公平群體,并且有針對性地采取眾多手段和措施來保障不同公平群體的入學機會,現已形成了較為系統的關于弱勢群體學生公平入學的高校招生錄取制度。值得一提的是,霍克政府時期的改革在其間發揮了奠基性的關鍵作用,而目前學界對其進行專門研究的學術成果較少,尤其是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成果稀缺。②加之近年來,我國高校招生錄取名額分配不公、城鄉教育資源配置不平等、社會各階層受教育機會不公平、入學機會區域性失衡等與教育公平相關的問題愈益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黨和政府亦高度重視,強調要通過一切有效手段來保證人民群眾受教育機會的公平性。因之對霍克政府的高校招生錄取制度改革展開深入、系統的考察與研究,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對我國招生制度的改革以及加深對現行澳大利亞高校招生制度的認識亦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澳大利亞高校招生錄取制度的歷史回顧
澳大利亞高校招生始于1850年悉尼大學的創立。然而,自19世紀50年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其高等教育始終保持緩慢發展狀態,全澳也僅有六所大學,在校生人數亦是甚少。以1939年為例,大學入學人數累計達14,236人,僅占全澳人口總數(6,997,000)的0.2%。[1]當時只有少數社會上層階級家庭子女享有高校入學機會,故而這一時期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本質上是一種特權教育,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一局面才逐漸改觀。
(一)20世紀40-60年代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張
二戰以來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的發展,本質上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戰爭刺激下,澳大利亞各工業部門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產業結構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開始由農牧業經濟轉向工礦業經濟,使得勞動力市場對高技能工人和專業型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對此,傳統的精英教育顯然無法滿足,從而令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此同時,就業市場對人才的大量需求,使得大學生一畢業便能擁有很好的發展前景,越來越多的人視教育為一種可以帶來實質性回報的投資③而加以追捧。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民眾對高等教育需求量的迅速增加,聯邦政府開始大幅擴張高等教育機構的受眾范圍與數量規模,就此誕生了新南威爾士大學(1949年)、莫納什大學(1956年)、麥考瑞大學(1964年)以及紐卡斯爾大學(1965年)等一批新興大學[2],從而為社會民眾提供了更多就讀高等教育的機會。在建立大學的同時,聯邦總理孟席斯(Menzies)更是針對高等教育一元化體制進行了改革,于1965年宣布建立一批與大學處于同等地位的以培養專業技術人才為目標的高等教育學院,以進一步擴充高等教育機構。1963年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機構只包括10所綜合性大學,而到1973年已有17所綜合性大學和77所高等教育學院[3],且高等教育學生總人數大幅上升,1974年高等教育就讀總人數共計達250,051人[4]。隨著澳大利亞高校和學生數量的增長,其高等教育開始趨向大眾化進程。
(二)20世紀70年代高等教育免費政策的頒布
20世紀40至6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迅速增加,但廣大工人階級家庭子女仍普遍缺乏進入高校學習的機會,在高等教育學生總數中的占比仍舊偏低。根據澳大利亞教育研究委員會對1959-1960年度的114,000名中學畢業生的調查數據顯示,在父親是“大學專業人士”的學生中,有36%的男孩和24%的女孩進入全日制大學學習,而父親是非技術或半技術人員的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男女比例則分別不足2%和1%。[5]1971-1972年的后續研究表明,來自非技術或半技術家庭子女的入學比例雖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幅度十分之小,其中男女比例分別升至32%和24%,而同一時期專業人士家庭背景子女的男女比例分別增至39%和28%。[6]為促進高校入學機會的均等,惠特拉姆(Whitlam)領導的聯邦政府于1974年宣布開始實施高等教育免費政策,并且推出了基于經濟狀況調查的高等教育援助計劃。[7]作為高校招生錄取民主化的一次偉大嘗試,免費政策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掃除了學生特別是低收入家庭子女入學的經濟障礙,極大地促進了教育機會的平等。
綜上言之,20世紀40至70年代,在戰后社會經濟發展需求與高等教育機會平等理念的指導下,伴隨著高校規模的擴張以及免費政策的實施,高等教育的受眾范圍迅速擴大,社會民眾的入學機會顯著增加,由此逐步打破了二戰前的精英教育模式,這為80年代霍克(Hawke)政府的進一步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霍克政府高校招生錄取制度改革
為進一步推進教育公平,1983年繼任的霍克政府致力于解決高等教育參與率不足,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高等教育參與不公平問題。因此,聯邦政府著力推進高校入學機會改革,將提高傳統上受教育機會有限的低社會經濟地位、鄉村及偏遠地區、土著居民、女性等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各學生群體的高等教育代表性作為主要目標,進而對高校招生錄取制度進行了系列改革。
(一)霍克政府時期教育公平理念的變化
盡管往屆政府為促進入學機會公平做了相當大努力,并最終免除了高等教育學費,但高等教育學生的社會經濟背景結構并未發生較大變化④,且諸如種族、地域、性別等不利因素仍極大地限制了學生的高校入學機會。20世紀80年代,在澳大利亞經濟衰退與全球經濟競爭日漸加劇的形勢下,聯邦政府開始將高等教育視為挽救經濟危機與增強國際經濟地位的強有力手段,要求充分發揮人力資本優勢,從而使得高等教育職能逐漸偏離70年代聯邦政府設定的關于實現社會平等的政治目標,而更加側重于經濟目標,即為增強澳大利亞國際經濟競爭力培養受過良好教育與具備高技能的熟練勞動力。霍克總理在1984年9月舉行的“參與和公平計劃”會議上便發表了重要講話:“隨著先進技術的出現與世界的快速變化,人們必須擁有必要的教育水平,具備與時俱進的能力與技能以及創新性,以適應動態變化的世界,為實現該目標,必須更有效地利用人力和物力資源,在人力技能上大力投資,這對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8]可見,改善高等教育公平已不僅僅是社會公平問題,更是實現經濟目標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這便需要將獲得技能的平等機會擴大到所有勞動力群體,尤其是入學機會有限的社會邊緣群體。事實上,早在1983年新任教育和青年事務部部長蘇珊·瑞恩(Susan Ryan)在7月發給聯邦高等教育委員會的教育經費指導方針中便明確宣布了政府有關教育政策的兩大目標:增加高等教育參與和公平。[9]1987年12月澳大利亞就業、教育與培訓部長約翰·道金斯(John Dawkins)明確指出:來自經濟困難家庭、鄉村及偏遠地區、土著居民群體的學生參與高等教育的機會十分有限,某些學科領域的女性與特定的移民群體以及非英語背景群體在高等教育入學方面亦存有重大障礙。[10]基于此,聯邦政府繼而將增加高等教育歷史上沒有得到充分代表的學生群體的入學機會作為國家教育政策制定的主題與優先發展事項。相較于70年代以消除財政障礙為目的的免收學費政策,霍克政府采取了更具針對性且更加積極高效的招生政策,主要表現為針對不同的弱勢群體學生制定和實施區別性舉措,以便增加高等教育學生群體的多元化與代表性。
(二)社會各群體參與公平與高校招生錄取制度改革
為提高弱勢群體的高校入學率,聯邦政府大力增加高等教育可供學額,在高校招生錄取制度上則針對代表性不足的弱勢群體采取多項公平化措施,其改革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1.頒布入學機會均等政策
自澳大利亞大學創辦以來,女性群體在高等教育入學方面長期處于劣勢地位。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女性參與高等教育的狀況才逐步得以改善,在高等教育學生總數的占比從1976年的42%緩增至1985年的48%[11],但其主要集中于教育、藝術、健康專業,而在工程、技術、建筑等學科領域中的占比十分之少。如工程與技術專業,1985年女性在該學科總人數中的占比僅為5%。[12]為增強女性受教育需求意識、保障女性的入學機會與提高女性在非傳統領域中的入學比例,1987年9月聯邦政府頒布了澳大利亞歷史上第一個有關女性受教育的國家政策,即《澳大利亞學校女性國家教育政策》(National Policy for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Australian Schools)。該政策明確提出了包括提升女性受教育需求意識、確保女性平等參與學科選擇、創建益于女性受教育的校園環境、保證學校資源公平分配在內的改善女性入學機會的四大目標。[13]為確保上述目標的實現,聯邦政府出資50萬澳元用于增強女性受教育意識的信息宣傳活動,19萬澳元建立國家女性教育數據庫,為提升女性參與非傳統專業領域的教學項目提供的資金更是高達100萬澳元。[14]而相較于女性群體,其土著居民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則更少。據數據顯示,1972年僅有72名土著學生就讀于高等教育機構。[15]1989年,聯邦政府頒布了旨在保障土著居民與托雷斯海峽島民受教育機會的《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國家教育政策》(National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Education Policy)。該政策圍繞教育決策、教育服務、教育參與、教育成果平等四個方面制定了21項有關土著民族和托雷斯海峽島民教育發展的長期目標,旨在通過改善教育服務的可得性、反應性與有效性,使之成為保障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接受教育的重要手段。[16]為實現這一政策設定的廣泛目標,聯邦政府于1990年首次提出《土著居民教育戰略行動計劃》(Indigenous Education Strategic Initiatives Programme),次年又進一步設立了《土著居民教育直接援助計劃》(Indigenous Education Direct Assistance),為各項促進土著學生入學的計劃均給予了巨額撥款。[17]總之,聯邦政府入學機會均等政策的頒布與實施為各教育機構、聯邦政府、各州及領地政府就女性與土著民族教育戰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原則,在提高其高等教育入學比例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2.建立基于收入還款的學費制
隨著入學人數的持續增加,高等教育培養成本不斷上升,遂給公共教育支出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導致1974年起實行的高等教育免費政策開始變得難以為繼,聯邦政府急需尋求一種新的資助方式,為不斷上漲的高等教育學額提供資金。1987年,聯邦政府首次嘗試對高校學生收取250澳元的高等教育行政費,但約有35%的學生免收學費。[18]繼高等教育行政費之后,為緩解財政預算的緊張局面,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的融資途徑,聯邦政府決定正式廢除自1974年起實施的免收學費政策,全面推行收費政策。但為保障低社會經濟背景學生的入學機會,聯邦政府并沒有讓學生獨自承擔全部費用,而是由聯邦與學生按比例共同分擔,其中聯邦政府承擔了絕大部分教育成本,與此同時,還建立了基于收入還款的學費制。這在1989年1月1日聯邦正式頒布實施的《高等教育貢獻計劃》(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on Scheme)中有詳細規定,根據該計劃:(1)所有就讀于聯邦政府資助學額的學生承擔一定標準的高等教育生均培養成本費,剩余的則由聯邦政府支付;(2)學生在入學前若預先支付學費則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反之則可以通過請求聯邦政府幫其支付而選擇延期付款;(3)學生的債務還款與“消費者價格指數”直接掛鉤,以保持物價的實際價值;(4)學生的供款債務不收利息,當其“債務還款收入”達到指定還款門檻時,必須開始償還債務,但若能證明還款會造成嚴重的財政困難,則有可能推遲償還時間,還款門檻每年會進行相應調整;(5)若債務人死亡,還款的義務將被取消,死者的家屬則不需要承擔任何剩余債務。[19]相比惠特拉姆政府的免費政策,霍克政府的高等教育貢獻計劃雖聽起來遠不及其美好,似乎與教育公平的目標背道而馳,但其是在完全不同于往屆政府的經濟緊張環境下做出的重大改革與嘗試,實則是一項公平的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學費的延期支付且以收入為基礎的償還模式,在有效緩解財政壓力的同時也極大地減輕了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的學費負擔。
3.大力拓展入學途徑
澳大利亞幅員遼闊,大學普遍位于都市地區,因而對鄉村及偏遠地區學生而言,通過遠程教育進行校外學習是其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途徑。為給農村及偏遠孤立社區的居民提供高等教育入學機會,聯邦政府大力加強遠程教育學習的基礎設施建設,于1987年計劃資助建立六個遠程教育中心,負責開發和傳遞更加多樣化且高質量的課程材料,并確保這些新建教育中心能夠深入偏遠的鄉村地區。[20]與此同時,區別于一般的以高中畢業證書考試成績排名為依據的招生方式,大多數高校都針對土著居民、農村及偏遠地區學生等特定招生群體制定了特殊的入學政策。例如新南威爾士大學便實施了一項“特殊入學計劃”,為有學術潛力但長期處于受教育不利地位,無法滿足一般入學條件的弱勢學生提供入學機會,而且在這些學生入學后優先為其提供各項支持服務。[21]鑒于許多低社會經濟背景的中學畢業生并未進入高等教育機構,而是集中于TAFE學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⑤,聯邦政府還致力于加快TAFE學院與高等教育機構的學分轉換進程,構建不同教育機構間的學分互認制體系,為學生開辟另一條高等教育入學路徑。在此之前,大學與TAFE學院之間的學分轉換僅限于各州及領地內部以及少數專業課程,且換算過程繁瑣復雜。1988年聯邦政府明確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學分轉換的指導原則,包括認可申請者在先前教育機構所獲的課程學分、加強高等教育機構與TAFE學院在學分轉換方面的對話與合作、各教育機構必須在招生過程中公開發布本校有關學分轉換的相關信息等等。[22]作為TAFE學院與高等教育之間有效銜接的橋梁,學分轉換極大地拓寬了高校的入學路徑。1991年,澳大利亞大學新生錄取人數共計137,984人,其中通過傳統的中學畢業證書考試錄取的有72,655人,通過TAFE課程錄取的有4,437人,通過特殊入學計劃錄取的有3,561人,通過成人入學計劃錄取的有7,681人,其余的來自其他各種入學途徑。[23]隨著遠程教育學習方式、特殊入學計劃以及學分轉換的實施與推廣,澳大利亞高校入學途徑逐漸呈現多元化趨勢。
4.制定明確的招生戰略目標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聯邦政府還針對特定群體制定了具體的戰略目標。1990年聯邦政府又進一步頒布了名為《所有人的公平機會》(A Fair Chance for All)的報告,不僅提出了高等教育公平的總體目標是實現比例代表制⑥,即“確保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澳大利亞人都有機會成功地參與高等教育,這將通過改變學生群體人數的平衡來實現,以便更緊密地反映整個社會群體的構成”。而且,針對特定的弱勢群體學生,聯邦政府制定了具體而明晰的公平戰略目標:到1992年,所有高校必須為低社會經濟背景學生制定特殊入學安排;到1995年,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學生注冊人數增加50%,非傳統專業領域(工程學除外)中的女性人數至少增長40%,工程學專業的女性人數增長15%,同時增加研究生學位課程中的女性比例,大學一年級入學的殘疾學生人數增加一倍;到1992年,鄉村及偏遠地區高校必須為當地中學提供有關大學課程與入學的詳細信息;位于非英語背景人群主要聚集區的學校必須為這些學生開設增強高等教育意識的相關課程。[24]由此可見,聯邦政府試圖通過制定不同群體的公平指標來確保所有人都享有參與高等教育的機會,進而改變高校學生群體社會結構的不平衡狀態。為實現上述戰略目標,該政策文件還明確強調各高等教育機構的招生計劃必須考慮國家高等教育公平的總體目標和各個弱勢群體的公平目標,每年要對院校公平項目計劃的實施結果進行評估并向聯邦政府提交相關報告[25],并針對每一群體的不同特征提出了相應的公平措施,包括為弱勢群體學生制定特殊入學安排、推廣遠程教育模式、加強學分轉換進程、提供高等教育入學信息咨詢服務等等一系列方案。[26]這是聯邦政府首次在全國范圍內針對弱勢群體制定的戰略目標,對各高校公平目標的制定與項目計劃的實施具有重要的先導作用。
綜上所述,霍克政府自1983年上臺伊始,為促進公平目標的實現,便致力于增加高等教育參與率,并確保新增學額能夠公平分配給代表性不足的弱勢群體。通過一系列高等教育招生政策改革,霍克政府切實改善了土著居民、女性、低社會經濟地位、農村及偏遠地區等弱勢群體學生的高校入學機會。也正是由于這一連串改革政策的實施,澳大利亞高校招生錄取制度公平框架與運作機制得以形成。
三、高校招生錄取制度改革的影響
霍克政府時期高校招生錄取制度不僅切實改善弱勢群體學生的高校入學機會,更對其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為經濟發展輸送了大批優質人才
作為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招生錄取制度改革是霍克政府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采取的重大戰略之一。聯邦政府致力于通過改善高校入學機會與公平,增加高等教育參與率,進而培養經濟發展所亟需的高技能專業人才。20世紀80-90年代,在澳大利亞產業結構由以制造業為主的傳統產業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級產業升級轉變的經濟背景下,非技術性、低技能工作逐漸消失,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崗位對高技能工人和專業人員的需求持續增加,從而使得高等教育學歷日益成為順利就業的重要條件。如1995年澳大利亞就業、教育、培訓和青年事務部發表聲明指出:“社會各行業對管理人員和專職人員提供服務的需求將強勁增長,在未來10年新增的就業崗位中,這些職業將占很大比例,機器操作員和普通勞工等許多低技能職業的就業將下降。”[27]在霍克政府的改革下,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學生總數從1983年的348,577人迅速增長至1991年的534,510人,1993年進一步增加到575,616人,十年間增長了65.1%。[28]不可否認,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參與率的急劇上升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素質人才的需要,為促進經濟增長與提高國際經濟競爭力培養了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級專業人才。
(二)加強了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部門的宏觀調控
作為典型的聯邦制國家,澳大利亞聯邦憲法明確規定教育事務的管理權歸屬各州及領地政府。但自二戰以來,隨著聯邦政府對各州教育資金援助幅度的不斷加大,其對教育的管控權也愈益增強。20世紀80年代,為深入推進高等教育公平化,確保弱勢群體能夠充分參與高等教育,聯邦政府開始以全局觀來審視教育公平問題,通過頒布政策、制定法律與資金撥款等多重手段保證高等教育競爭條件與能力的平等,這極大地提升了聯邦政府在促進教育發展進程中的影響力。在聯邦政府宏觀政策的調控下,各高校享有較大的自主權,可以根據政府制定的政策目標結合實際自行采取相應措施,如為弱勢群體制定具體的招生計劃與入學條件,創建便于公平群體入學的程序和機制等等,但必須受聯邦政府監督,定期匯報關于公平計劃的進展概況與實施成效等方面的教育報告。[29]霍克政府在招生錄取制度改革中首次引入競爭機制,即根據各高校的招生人數與其對國家公平目標的完成情況給予撥款數額,進一步增強了聯邦政府對教育部門的宏觀管控權。
(三)推動了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社會的建設與發展
20世紀80年代,霍克政府致力于推動多元文化社會建設,并于1989年明確表明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社會的長期目標:無論背景如何,所有澳大利亞人都享有平等的機會和待遇,消除種族、語言、文化、性別等障礙,確保所有人的智慧和才干都能得到充分發揮與有效利用。作為實現多元文化社會目標的重要戰略之一,社會弱勢群體學生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改善不僅保障了其公平獲得社會資源的權利,而且為其發揮個人與群體才能、平等參與國家生活提供了重要前提。通過多項公平政策的實施,各社會弱勢群體學生的高校入學機會與絕對數量顯著增加。其中,增長幅度最大的為女性群體,1983年在高等教育學生總人數中的占比尚為46.3%,1991年已增至53.3%。[30]此外,土著居民學生的入學人數亦呈上升趨勢。1982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土著學生僅有854名,而到1991年已增加到4,807人,增長率高達460%,在學生總人數中的占比由0.3%增至0.9%[31],從而促進了土著教育與文化的發展,強化了族群認同感。隨著高校入學機會的提升,越來越多的弱勢群體學生能夠進入大學學習,這有利于提升其就業機會特別是從事技術性職業的機率,從而改善其經濟條件,提高其政治地位,進而推動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社會建設。
四、招生錄取制度改革的不足之處
盡管在招生錄取制度的改革下,澳大利亞社會處境不利群體學生參與高等教育的機會與數量顯著增加,但這還遠未達到比例代表制的平等水平,澳大利亞在實現高等教育公平總體目標方面仍然面臨著嚴峻困難與挑戰,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對弱勢群體學生入學障礙的認知不足
弱勢群體學生在高等教育入學方面的不利地位并非源于某種單一因素,而是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等多重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就直接決定了改革任務的艱巨性。而霍克政府的招生政策改革過于強調高等教育層面入學機會的擴大和改善,某些公平政策雖然消除了入學障礙,但缺乏對受教育不利原因的深層次分析,以致于忽視了高等教育體系之外的其他隱性因素。以低社會經濟背景學生為例,盡管“高等教育貢獻計劃”的實施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其入學的財政壓力,但諸如缺乏家庭支持、中等教育學業水平成就低、高等教育志向不足等同樣是影響低經濟背景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入學的重要因素。據數據統計,1992年澳大利亞大學來自低社會經濟背景的學生有76,813人,占高等教育國內學生總數的14.6%,這一比例還遠低于其25%的全國人口占比。[32]因此,若要持續有效提高弱勢群體學生的高校入學率,必須對造成這一劣勢的原因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分析,以及采取更為復雜具體的解決方案。這不僅需要高等教育機構為其制定優先戰略計劃,更有賴于在中等及以下教育階段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
(二)中學階段受教育水平不平衡
雖然高校入學途徑呈現多元化趨勢,但高中畢業證書考試仍然是大學招生的主流模式,而社會弱勢群體學生的中學課程完成率與學業水平成就普遍較低,這嚴重降低了弱勢學生進入大學的潛在生源。加文·穆迪(Gavin Moodie)在對1994年和1995年南澳大利亞州大學本科課程的申請、錄取與入學人數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弱勢群體學生高等教育代表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不在于他們能否成功獲得錄取通知書,而是因為申請人數太少。[33]由此可見,改善弱勢學生的中等教育機會,提高學業水平成就,增加中學鞏固率對提高其高等教育入學率而言意義重大。然而,相較于社會上層階級家庭學生,澳大利亞低社會經濟地位背景學生的中學畢業率仍十分之低。據統計數據顯示:1987-1996年間,高社會經濟地位背景學生中學12年級的完成率始終位于65%以上,1990年后均穩定在75%以上;反觀低社會經濟地位背景學生的中學完成率,雖然在1991年顯著提高,一度由1990年的50%多增至60%以上,但其后也從未超過65%,甚至有所下降[34],這極大降低了低社會經濟地位背景群體學生的高校申請人數,從而影響了入學率。同時,學校性質的不同也是造成中學教育差距的重要因素,這主要表現為私立學校的高等教育升學率顯著高于公立學校。特雷弗·威廉姆斯(Trevor Williams)等人對中學12年級畢業生高校入學情況進行了分析研究,指出在1989年,私立中學超過70%的畢業生進入高等教育,而公立中學的比率則低于40%。[35]優勢階層子女可以憑借獨特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本優勢進入私立學校和重點中學。普通家庭子女尤其是低社會階層學生則只能進入公立學校和普通中學,而這又與高校入學機會的獲取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學階段受教育水平的不平衡將是澳大利亞高校招生錄取公平改革面臨的另一重大挑戰。
(三)高等教育機構內部公平政策的實施機制不完善
盡管聯邦政府明確規定了高等教育機構在實現國家公平目標方面的重要責任,并將公平作為對高等教育機構撥款、監控與審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各高等教育機構在公平政策的實施機制方面仍存在重大問題。由于各高等教育機構在使命、組織結構和總體規劃方面都存有較大差異,導致不同高校對公平項目的管理與執行方法也不盡相同。許多大學負責執行公平政策的工作人員和高級管理決策者之間在觀點上存有較大分歧,而且這些工作人員在公平政策制定方面很少或根本沒有作用,其執行工作與機構的政策進程完全脫節,這大大降低了公平政策的可行性與有效性。拉姆塞(Ramsay)在1995年舉辦的第二屆全國高等教育公平會議上指出:“在大多數大學,公平計劃的決策者與執行人員分散在多個不同單位,且政策執行人員在高等教育機構普遍處于無權地位,彼此獨立工作。而且機構對公平問題的責任一般由高級管理層人員負責,其與執行人員并無太大聯系,以至于全面實施公平計劃的領導力和協調性無法實現或沒有效果。”[36]高等教育機構公平計劃的實施成效直接決定著弱勢群體學生公平目標的實現,只有各高等教育機構將公平目標納入決策主流,建立健全公平政策的決策與執行機制,才能確保公平計劃的有效實施,進而推動公平目標取得更大進展。
五、結語
綜上所述,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霍克政府通過針對不同類別的弱勢群體采取有針對性的招生入學政策,使得社會弱勢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顯著增加。在統一協調解決方案的實施下,學生群體比例代表制定義了高等教育公平的核心內涵,高等教育政策與資源開始向處境不利群體大幅傾斜,且公平目標正式上升為國家發展的重點戰略,成為各大學教育概況的強制性組成部分和聯邦對教育機構經費分配與審查的重要依據,這在當時澳大利亞乃至世界范圍內都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戰略決策。盡管公平群體的高等教育代表性仍然不足,但顯然已經向前邁進了關鍵一步,為后續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繼霍克政府之后的歷屆政府都較好地繼承了這一政治遺產,始終將解決高等教育代表性不足問題作為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主要目標,在秉持公平原則的前提下,持續改革完善其高校招生錄取制度體系。
注釋:
①本文教育公平主要是指高校招生錄取名額的公平分配,確保社會各群體公平參與高等教育。
②目前國外學界對澳大利亞霍克政府時期高校招生錄取制度進行專門研究的學術成果為數不多,僅有少量論文涉及相關內容的闡述,如Robert Pascoe的“Admission to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Vol.21,No.1,1999),Trevor Gale的“Fair Contest or Elite Sponsorship?Entry Settlements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Policy,Vol.12,No.1,1999),Peter Carpenter,Martin Hayden的“Improvements in Equity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ustralia During the 1980s”(Higher Education,Vol.26,1993)。與國外學界相比,國內有關澳大利亞高校招生制度的研究成果則較少,截至目前僅有一本學術專著和少量論文,如蔡培瑜的《澳大利亞高校招生考試制度研究》(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與其論文“澳大利亞大學本科招生制度的特點及啟示”(教育測量與評價,2016年)以及鄭聰艷的《澳大利亞以高校準入排名為基礎的高校招生制度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等,但這些研究成果大都將招生考試與招生錄取混合而談,并側重于對現行澳大利亞高校招生考試及特點的簡要介紹與分析,且主要集中于教育學科領域,系統、全面而深入的歷史學考察與研究成果則極少。
③這就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著名的人力資本理論。
④澳大利亞學者安德森等人對高等教育學費免除后學生群體的社會經濟結構進行了詳細考察與數據分析,結果表明免費政策的實施對高等教育學生社會經濟背景結構的影響甚微。(參見ANDERSON D,BOVEN R,et al.Students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A Study of Their Social Composition Since the Abolition of Fees[M].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0:199。)
⑤澳大利亞的TAFE學院是其中學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稱為職業技術與繼續教育學院,主要以工作培訓為主,屬于職業技術教育領域。相關調查研究表明,處于社會不利地位的弱勢群體更容易選擇就讀TAFE課程,而不是進入高等教育機構學習。(參見POWER C,BAKER M,ROBERTSON F.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Participation,Equity and Policy[M].Canberra:Commonwealth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1986:83。)
⑥這里是指某一目標群體在高等教育學生總人數中的占比與其在社會總人口數中的占比相等。
參考文獻:
[1]Committee o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R].Canberra:Government Printer,1957.
[2]杜海燕.澳大利亞大學發展史研究[D].河北大學,2011:62.
[3]西蒙·馬金森.現代澳大利亞教育史[M].沈雅雯,周心紅,蔣欣,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17.
[4]ANDERSON D,BATT K,BESWICK D,et al.Regional Colleges:A Study of Non-Metropolitan Colleges in Australia[M].Canberra:Education Research Unit,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5:28.
[5]Committee on the Future of Tertiary Education in Australia.Tertiary Education in Australia[R].Canberra:Government Printer,1964:35.
[6]ANDERSON D,BOVEN R,FENSHAM P,et al.Students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A Study of Their Social Composition Since the Abolition of Fees[M].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0:61.
[7]GALE T,TRANTER D.Social Justice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An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Account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J].Crit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2011,52(1):34.
[8]HAWKE R.Participation and Equity Program[R].Canberra: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Australian Government,1984:4-8.
[9]RYAN S.Minister Announces 1984 Education Funding Guidelines[R].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1983:3.
[10]Department of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Australia).Higher Education:A Policy Discussion Paper[R].Canberra,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7:21.
[11][28][30]Department of Education,Training and YouthAffairs,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Selected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Time Series Data 1949-2000[R].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2001:90-91,5,5.
[12]Commonwealth Tertiary Education Commission(Australia).Review of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n Higher Education[M].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6:90-91.
[13][14]MCINNIS S.Girls,Schools…………and Boys Promoting Gender Equity Through Schools:Twenty Years of Gender Equity Policy Development[EB/OL].(2007-10-26)[2020-11-20].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rp/RP9596/96rp24.
[15][34]WEST R.Learning for Life: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Financing and Policy:Final Report[R].Canberra,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98:138,93.
[16]Department of Education,Skills and Employment,Australian Government.National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Education Policy[R].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9:1-3.
[17]Australian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Education,Science and Training.Indigenous Education Strategies[R].Australian National Audit Office,2002:12-14.
[18]CARPENTER P,HAYDEN M.Improvements in Equity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ustralia During the 1980s[J].HigherEducation,1993(26):201.
[19]JACKSON K.The 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on Scheme[EB/OL].(2003-8-12)[2020-10-28].http://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lications_Archive/archive/hecs.
[20][22]Australia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Higher Education:A Policy Statement[R].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8:51,36-38.
[21][23][31]Department of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Australia.National Report on Australia’s Higher Education Sector[R].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93:225,197,217.
[24]Department of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Australia.A Fair Chance for All:Higher Education That’s within Everyone’s Reach[R].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90:3.
[25][26][29]Department of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Australia.A Fair Chance for All[R].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1990:4-5,73,5.
[27]Department of Employment,Education,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Australia’s Workforce 2005:Jobs in the Future[M].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95:98.
[32]JAMES R.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An Analysis of School Students’ Aspirations and Expectations[M].Canberra,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Department of Education,Science and Training,2000:6.
[33]MOODIE G.An Instrumentalist Approach to Equity,Quality an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R].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quity and Access,Melbourne,1995:3.
[35]GALE T.Fair Contest or Elite Sponsorship? Entry Settlements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J].Higher Education Policy,1999,12(1):81.
[36]National Board of Employment,Education and Training,Australia.Equality,Diversity and Excellence:Advancing 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quity Framework[M].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96:18.
(責任編輯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