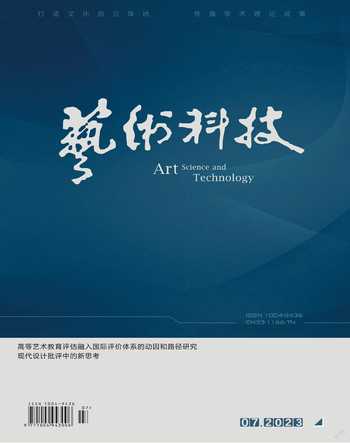民間文化進校園:高校花燈舞教學創新研究
摘要:2016年4月,貴州省出臺了《關于全面推進各級各類學校民族文化進校園工作的實施方案》。貴州花燈藝術作為民間藝術,呈現為詩、樂、舞合一的藝術形式,圍繞節日、節氣以及民間喜事進行儀式性的演唱。貴州花燈的藝術形式與活潑潑之生命精神呈現充分彰顯了自身特色。在藝術行進之中,參與者獲得認同感與滿足感。在人神互通的舞蹈過程中,體現出貴州自然地貌中自然人向社會人的演變過程。這是花燈藝術娛樂性與教育性雙向互動之中需要把握的關鍵。借用貴州花燈這一在民間自發成長且經久不衰的藝術形式開展教育,更能被當地民眾所接受,并且能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發揮教育的作用。基于此,文章提出,教師要在把握花燈藝術形式、內涵及文化邏輯的基礎上,從實地觀摩、藝術教學與改編、投入實踐與反饋三個部分進行教學設計:實地觀摩以使學生獲得直接的感性經驗,藝術教學與改編以創新花燈藝術形式,投入實踐與反饋以保證貴州花燈藝術不喪失其民間性。在教學中,促進高校花燈舞教學創新,為民間文化進校園助力。
關鍵詞:貴州花燈;文化認同;教學創新;寓教于樂;實地觀摩
中圖分類號:G8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07-00-03
貴州花燈,又稱為“貴州花燈舞”,作為民間文化較有代表性的藝術之一,其以接地氣的表現形式受到西南不同地域人民的喜愛。2016年4月,貴州省出臺了《關于全面推進各級各類學校民族文化進校園工作的實施方案》。根據貴州省教育廳的指示,民族民間文化項目將主要在藝術體育課程中開展教學實踐,以引導學生了解與保護民間文化。當貴州花燈真正在生活中進行表演時,大眾對生命情感的宣泄與表露之訴求遠遠超出將花燈舞規范化、秩序化地表現出來,這就難免會帶來貴州花燈本身藝術形式的粗糙化、隨性化問題。
面對花燈藝術存在的問題,藝術教學研究的任務不是一味將形式固定化,而應以思辨的眼光研究花燈舞的哪些形式構成這一活潑潑之精神的關鍵,并基于這些藝術形式完成對貴州花燈藝術教學的創新,使其既保留自身精神意味,又能在傳承中不喪失藝術特性。另外,花燈舞的粗糙化、隨性化或多或少造成了對活潑潑之生命精神的破壞,這種破壞相應地導致了審美教育目的的喪失或歪曲。受廣大群眾歡迎的花燈舞藝術面臨著藝術精神與形式上的雙重困境。從藝術教育的視角來看,對貴州花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校外活動實踐與中小學教學,而高校對花燈藝術教學的思考能夠借助藝術資源與足夠的時間來嘗試回應并解決花燈舞面臨的雙重困境。
1 貴州花燈藝術語匯與文化精神
貴州花燈舞與其他地域花燈舞存在不同,并且其內部因地理環境中居民分布的不同而產生不同類型的花燈。貴州黔北花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黔北花燈憑借歷史性及在歷史發展中呈現出的適應性,為研究貴州花燈藝術語匯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對貴州花燈舞藝術形式、文化精神的研究多以黔北花燈為例,輔以其他地域的花燈研究。
貴州花燈藝術是將詩、樂、舞合一的藝術形式。就貴州花燈的演唱主題或者花燈種類來說,主要圍繞節日、節氣以及民間喜事進行儀式性的演唱,主要有喜燈、壽燈、元宵燈三類。喜燈、壽燈主要圍繞民間喜事進行,喜燈包括婚嫁燈、升學燈,壽燈則主要以為老人祝壽這一主題進行,由此可以窺見貴州花燈有細致周到的主題分類。就表演形式來說,不同主題下的表演形式大體相同。以貴州黔北花燈為例,其表演大致可分為七個步驟,先后分別是開燈與盤燈、說春(說唐二、請妹)、掃方、掃土地財神、梳妝、參神、唱燈。在表演形式中,可以看到對話、唱誦占據貴州花燈藝術的重要部分。
在唱誦中,即在燈友對話互動中,藝術表演獲得趣味性和知識性。一般唱誦的內容包括當地風土人情、神話傳說等,內容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并無嚴苛的具體規定。不僅如此,這些流程并不是每次都要完整進行,演員會依據具體情況,盡自己所能,將藝術效果做到最好。與其將其定義為隨意性,不如結合具體實際來看,進入貴州花燈藝術表演本身,是為了將效果發揮到最佳。只有盡可能將效果發揮到最佳,觀眾才能在觀看與互動之中獲得樂趣。以一段貴州花燈唱詞為例:
顏氏夫人生孔子,韓氏夫人生老君。
牟尼夫人生我父,萬古流傳到如今。
吾到壇下走一走,揮動金鞭駕起云。
重將拂塵掃一掃,掃開主家大財門。
春開財門春季旺,夏開財門夏季行,
秋開材門五谷滿,冬開財門進金銀。
一年四季財門開,斗大黃金滾進來[1]。
可以看到,這段唱詞的內容主要圍繞民間事務,包括生子、升學、賺錢等,而唱誦極具神話色彩的背后是民眾最為樸素和直接的生命需要。不過,貴州花燈的唱誦部分在吸收儒、道、佛三家傳統文化的同時將其捧上神壇,容易產生迷信思想。因此,必須注意貴州花燈藝術這一不成熟和有待改良的地方,同時也要看到藝術形式背后的本質——生命需要。
民間藝術形式呈現的本質,并不要求具有嚴苛性,嚴苛性反而會扼殺貴州地域民眾活潑潑之生命精神。對藝術形式背后的活潑潑之生命精神訴求是貴州花燈文化最需要被看見和把握的關鍵。“如果我們認定,人類創造藝術是為了審美,而藝術的產生受生命動機的制約,那么,美與生命之間必然存在著一種激動人心的關系……事實上人除了肉體的生物生命之外,還有精神生命和社會生命。人是三重生命的統一體。”[2]這種活潑潑之生命精神可以從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會生命三個層次來看。貴州花燈藝術在表演中既符合民眾對基本生命需要的訴求,又基于生物生命的滿足,通過精神生命引領人走向社會生命,在儀式之中,三層生命需求均得到了滿足。
2 民間文化進校園政策下高校花燈舞課程的理論支撐
貴州花燈藝術主要通過唱誦、對話的形式使表演者與觀眾進入藝術場域,在這種場域中,人的三重生命需求得以滿足。雖然其藝術形式并不嚴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會引起質疑,但要把握活潑潑之生命精神訴求。正因有此精神訴求,貴州花燈藝術得以歷經時代演變而不斷發展與延續。明白了貴州花燈藝術背后的文化邏輯,就可以確切地認識到作為民間藝術至今存在并且需要被重視的文化意義上的有力支撐。通過對貴州花燈藝術形式的呈現與梳理,可以看到其與原始藝術間密不可分的聯系。“文,原始文化中的文身,意味著將人的自然之軀,按社會、儀式、觀念的要求加以改變,顯示了自然人向社會(氏族、文化)人的生成”[3],文意味著藝術形式之呈現。具體到貴州花燈藝術,貴州花燈藝術的禮節性、儀式性特點,人神互通的舞蹈過程,背后都反映著貴州自然地貌中自然人向社會人的演變過程。在舞蹈中,當地居民獲得對自身的文化認同,完成自身在社群中存在的確證。
不僅如此,要在教學中重視宣傳貴州花燈藝術。《論語》言:“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從教育學角度來看,孔子讓他的弟子們談自己的理想,最好的教育不是加之以師旅,也不是因之以饑饉等治理手段與方式,而是黎民百姓載歌載舞式地悠閑歸家。借用貴州花燈這一在民間自發成長且經久不衰的藝術形式進行教育,正好可以暗合這一最好的教育方式,更能被當地民眾接受,并且更能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發揮教育的積極促進作用。
借用賀拉斯《詩藝》中提出的“寓教于樂”理論來理解,詩作為一種藝術,需要同時達到趣味性和有益性兩種目的,但有的教學重視趣味而不能產生真正的教育作用,有的教學重視教育卻難以讓受眾進入藝術欣賞的語境,這兩種情況都無法發揮出詩歌這門藝術的真正作用。同理,貴州花燈舞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也面臨著娛樂性與教育性兩個方面的問題。娛樂性源于其根植于民間文化,具有大眾文化中最接地氣的趣味性。這種趣味是對民眾自身存在的確證:在一遍遍詩、樂、舞的呈現之中,民眾不斷獲得對自身存在的一遍遍確證,能夠完成自身自然性向社會性的轉變和認可。這種娛樂性是貴州花燈藝術需要被照見之處,通過其表現形式就認為貴州花燈藝術的娛樂性是粗俗化的,這種論述是片面的。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其過度娛樂化會產生不良影響。
而就其教育性而言,花燈舞藝術憑借接地氣的形式,能夠潛移默化地影響、改變當地民眾,這是貴州花燈最需要被看見的優勢所在,如果以其他教育方式進入當地,就可能無法被民眾很好地接受。由此,花燈舞藝術的教育性需要在此基礎上加入更具內涵的文化精神。貴州花燈藝術能夠使人在樂趣之中受到教育,實現教學目的與娛樂目的的平衡、共存甚至雙贏。在舞蹈之中,教學目的與娛樂目的合一,并以一種游戲性的藝術形式實現更有趣味的展現,這才是貴州花燈藝術在教學理論設計中應該重視和把握的兩個層次。
3 民間文化進校園政策下高校花燈舞課程實踐設計
通過對貴州花燈藝術形式與文化精神的探討及對其背后文化邏輯、理論支撐的思考,可以更合理地進行貴州花燈藝術課程實踐設計。課程設計包括實地觀摩、藝術教學與改編、投入實踐與反饋三個部分,三者缺一不可,以此構成一個整體性的教學課程。
就實地觀摩學習來說,觀摩并進行評論是必要的,只有這樣,學生才能進入貴州花燈藝術的語境,了解藝術背后的活潑潑之生命精神。“在傳統教學方法的基礎上,觀摩評論法進行了更為深層次的延伸,它將傳統練習法進行了升華。觀摩評論法就是在已有舞蹈成品的基礎上,通過反復聯系,得出相應的舞蹈作品,然后每個學生對其進行評價,發現其中的優點和缺點,最后大家對舞蹈中的問題進行討論,將優點繼續發揚,并避免其中的不足,整體地提高舞蹈質量。”[4]在實地考察中,教師應該首先引導式地提出一些問題:一是貴州花燈藝術經常被質疑其形式粗糙化,結合實地觀摩,對此應如何回應;二是貴州花燈藝術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形式是其內容、動作、主題還是其他,在表演貴州花燈藝術時不喪失貴州花燈藝術的特色等。在教學中,教師主要圍繞這兩個問題,結合前文對貴州花燈藝術形式、精神以及背后文化邏輯的把握,進行啟發式、引導式教學。同時,教師要樹立開放性觀念,鼓勵學生基于實地觀摩分享自己的觀點與想法。
有了這些經驗材料及實地考察資料,學生便能夠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在課堂教學中,教師不會言之無物,學生也更容易進入課堂教學的語境和場域。基于實地觀摩,教師進行藝術形式和理論的結合性教授。以教師為主開展教學,主要目的是將貴州花燈藝術的精神與形式以清晰的樣貌加以呈現。在教學的基礎上,教師應鼓勵學生進行藝術改編,即以學生為主體開展教學,通過指定主題與出演角色來鼓勵學生進行藝術編排與匯報演出。在編排中,教師要主動了解學生的編排過程并給出建議,幫助學生合理編排。同時,也要積極鼓勵學生進行藝術形式的創新,從而促進貴州花燈藝術在形式上的創新。其中,課程的實踐需要把握貴州花燈舞藝術形式主要的呈現和文化精神,以及其內在的文化邏輯和理論支撐。只有這樣,對花燈藝術的實踐設計才能更具特色,從而與其他藝術區分開來。
“貴州花燈作為民間藝術的一種類型,它自身所蘊含的相對穩定性與創新性本質上來源于民間藝術的本質屬性,民間藝術具有生活化的特征。”只有處在生活語境之中,才能完成對民間花燈藝術的檢驗與教學。在教學步驟上,即在學生改編的貴州花燈藝術表演中,教師應考慮回到藝術現場進行表演。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到這些表演是否掌握了貴州花燈藝術的精髓。在詩、樂、舞的表演中,教師應該觀察當地民眾是否全身心投入表演,以及表演之中的互動次數與質量等。在表演結束后,采訪觀眾,獲得反饋信息。而后回歸課堂,與學生就實地表演體驗展開討論。只有不斷進入實地考察,回到藝術語境之中,才能保證貴州花燈藝術不喪失民間性,而其活潑潑之生命精神也不至于在劇場化的過程中被扭曲甚至喪失。
4 結語
通過對貴州花燈藝術形式與文化精神的探討及對其背后文化邏輯、理論支撐的思考,可以在此基礎上更合理地進行貴州花燈藝術課程實踐設計。課程設計包括實地觀摩、藝術教學與改編、投入實踐與反饋三個部分,三者缺一不可,以此構成一個整體性的教學課程。
參考文獻:
[1] 崔克昌,夏明均,李永林.黔北花燈初探[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43.
[2] 封孝倫.人類生命系統中的美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87-89.
[3] 張法.中國美學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12.
[4] 黃山.高校舞蹈教學模式構建與表演理論研究[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21:57.
作者簡介:賀元(1983—),女,貴州貴陽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中國民族民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