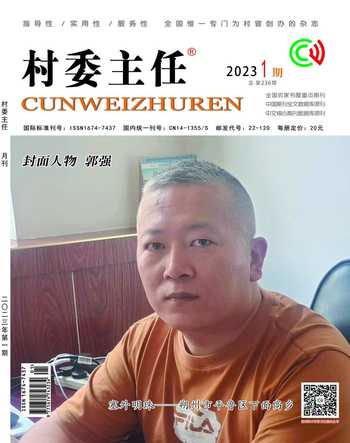黑龍江墾區城鎮化質量調控的理論邏輯與路徑選擇
馮浩城
摘要:城鎮化質量既事關墾區土地、水、環境等資源要素的可持續利用,又深度制約墾區城鎮體系與經濟社會的結構-質量全面優化。黑龍江墾區作為中國糧倉,城鎮化發展面臨農業經濟主導、城鎮職能單一、企業型政府外力干預等顯著問題,亟需反思城鎮化發展脈絡、檢視城鎮化目標戰略。研究認為:墾區這一特殊地域系統的城鎮化調控理論邏輯是融合集聚經濟與集約發展、重視城鎮化效率與社會福利增進同步;新型城鎮化與墾區主體功能指引黑龍江墾區城鎮化質量調控實現路徑有二:一是轉變城鎮化方式實現人口市民化與產業結構優化,二是厘清墾區城鎮化制度障礙、健全城鎮化運行機制實現政府、市場與企業協同。
關鍵詞:黑龍江墾區;城鎮化質量調控;提升路徑
文章編號:1674-7437(2023)01-0036-03? ? ? ?中國圖書分類號:F299.27? ? ? 文章標識碼:A
黑龍江墾區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適應國家糧食增產、邊疆國防建設、安置大批轉業軍人與城市未就業青年等背景發展起來的兼具“屯墾戍邊”“國家糧食保障”等地域功能的聚落體系。黑龍江墾區歷經1947-1955年的開荒建場、1956-1978年開發興場、1978年至今的轉型經營三階段[1],因不同時期城鎮化的動力、特征存在較大差異[2-4],因此,黑龍江墾區城鎮化過程及其質量會呈現獨特的區域特征。墾區城鎮化研究備受中國科學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關注[1,2,4],但重點在于探索三江平原墾區城鎮化的過程與空間組織模式,尚未深入探究黑龍江墾區城鎮化質量及其調控路徑。為此,辨析城鎮化質量調控的理論邏輯,深入剖析黑龍江墾區城鎮化瓶頸與路徑,闡明促進黑龍江墾區城鎮化質量提升的現實策略,為中國區域城鎮化質量調控研究增新內容。
1 黑龍江墾區城鎮化的內涵及質量調控的理論邏輯
1.1 城鎮化質量的內涵
城鎮化質量是研究城鎮化質量調控的起點,對城鎮化質量理解差異直接決定了構建的城鎮化質量調控體系、比較與評判、政策措施的差異。葉裕民(2001)[6]如果說城市現代化是城市化質量的核心內容的話,那么城鄉一體化則是提高城市化質量的終極目標。陳明(2012)[7]、郝華勇(2013)[8]、郭葉波(2013)[9]分別對國內城鎮化質量研究過程與現狀進行了深入總結與評述,認為城鎮化質量構成要素可從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居民生活和就業、生態環境、空間集約和城鄉協調等方面予以表征;城鎮化質量過程可圍繞經濟城鎮化、人口城鎮化、空間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等方面量測;城鎮化質量狀態可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抑或公共服務均等化測度,這構成了城鎮化質量研究的三位一體,即現有研究重點關注城鎮化質量的過程—結構—格局—機理中的某一方面或兩方面,未系統考慮城鎮化的過程—結構—格局—機理,因而會形成概念與內涵、測度指標體系等的差異。
1.2 歷史時期墾區城鎮化質量的構筑邏輯
黑龍江墾區城鎮化過程可分為1947-1978年自上而下的緩慢城鎮化、1979-2012年的自下而上為主的快速城鎮化兩階段,城鎮化動力主要是內源性動力,即墾區農業發展與經濟、人口快速增長主導的城鎮化發展[2]。然而,不同階段內源性動力存在顯著差異:1978年之前以人口集聚與農業生產的經濟增長為主,1978年之后主要是第二、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具體來說,1978 年前墾區城鎮化的各種要素由國家統一控制與分配,戶口、就業、福利一體化特征非常明顯,大批復轉軍人、內地農民、城市待業青年在國家政策引導下進入北大荒開墾土地、興建農場,完成原始經濟積累,當然機械化與規模化的農業生產方式直接使農場以較少人口耕作廣袤的土地,因而形成地廣居民點稀的村鎮格局。1978年后墾區緩慢推行家庭農場責任制與工業優先發展,戶籍政策等國家政策改革,催生了大批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建筑工業企業。農場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過程使墾區社會剩余資本、勞動力、產品與土地轉化不斷結合,大批以農場生產為主的農戶進入墾區分局所在城鎮居住,同時外來人口也集聚在各分局所在地進行二、三產業活動,墾區企業快速發展。
對比兩階段墾區城鎮化建設機制,發現墾區城鎮化存在如下特征:(1)墾區城鎮化內源性動力中農業貢獻度仍較高,部分中心城鎮產業結構弱、吸納就業有限,屬于城鎮化的低級階段;(2)墾區城鎮體系結構失衡、職能單一,原因在于墾區城鎮建設戰略過于倚重管理農場生產活動,缺乏服務于現代農業生產與農場職工生活;(3)墾區城鎮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低且相關權限缺失,如墾區70%的農場沒有按標準建立體現國家公共服務的文化館、圖書館和體育館,無法滿足正常生活需要;以及墾區城鎮未相應賦予國家縣市城鎮財稅權限,但仍要征繳土地使用稅等城市建設稅費[10]。總之,黑龍江墾區城鎮化是在國家體制背景下通過農墾自主積累建成的經濟聯系松散、運行成本較高、城市職能單一、發展動力不足的城鎮,且逐漸產生體制依賴。
1.3 墾區城鎮化質量優化的理論邏輯
1.3.1? ?整合集約發展與集聚經濟
城鎮化本質是經濟活動集聚產生知識與技術、社會公共服務等的外溢效應、擴散效應與輻射效應,然而過度集聚就形成城市病等問題,因此城鎮化質量的提升或優化必然要綜合平衡集聚經濟與集約發展。集聚經濟是促使產業技術不斷創新與升級、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公共氛圍,有利于提高城鎮創新能力與整體競爭力,并在衍生產業鏈、深化產業分工等方面功效顯著。城鎮集約發展是依靠生產要素優化組合、科學管理與技術進步等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等實現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增加,推動城鎮全面進步的發展方式。城鎮集約發展是克服集聚經濟弊端的有效方式之一,因此,墾區只有實現人口集聚與產業集群的同步,實現以農業現代為產業鏈主線的墾區工業化與農場城鎮化,才能有效整合集聚經濟與集約發展模式,提升城鎮化質量。
1.3.2? ?城鎮化效率與社會福利增加的同步
城鎮化質量優化、提升的核心內容是提高城鎮化的效率與增進區域社會福利[11],提高城鎮化效率就是將城鎮化發展過程各種要素充分科學配置,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最高效和城鎮運行的可持續,這其中主要包括經濟質量理性提升、生態環境趨好、社會福利增加等的多維同步,核心問題是要處理好城鎮的“職能、規模、空間”結構與城鎮的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的協調。當然,科學、合理的城鎮化必然帶來大眾生活水平和社會福利的提高,而適宜規模的城鎮化會引起經濟集聚效率的提升及其帶動區域城鎮化的全面優化。
2 黑龍江墾區城鎮化瓶頸
2.1 墾區功能波動蓄積了低質的城鎮化基礎
黑龍江墾區始建于1947年,至1949年末建成100個國營農場。1958-1959年近10萬解放軍、3萬山東支邊青年、6萬山東移民入駐北大荒。到1967年已建國營農場102個、生產隊2 157個、總人口達103.8萬人。然而伴隨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墾區成立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并接受了54.9萬來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知識青年,至1976年墾區成立11個國營農場管理局轄153個農牧場3 522個生產隊,擁有耕地2 891萬畝,總人口189萬人。直到1994年末墾區才全面推行“以家庭農場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到2007年底,墾區9 個管理局、113 個農(牧)場及若干分場的所在地,自然形成了140 多個小城鎮,原有2 532個生產隊(居民點)呈自然村落狀態分布在墾區各地[3]。
在6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黑龍江墾區并未直接建設城鎮,直到2008年黑龍江農墾總局提出構建“四五”城鎮體系的構想,即規劃建設5 個中心城、50 個重點鎮、50 個一般鎮和500 個管理區。究其成因:一是黑龍江墾區始終以糧食生產為主要功能,決定了該墾區以半機械化或機械化為主體的生產方式,直接影響墾區居民點空間分布,無法形成規模;二是黑龍江墾區以糧食生產為主的功能定位存在間歇性波動,如中蘇關系緊張導致該墾區全民皆兵成立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持續了近20年,導致該墾區人口高度集聚在建三江等邊境地區,奠定了建三江分局的80多個城鎮現狀;三是改革開放后受市場經濟影響與國家對黑龍江墾區管理體制調整,該墾區以企業法人為主的社會定位,使面向高經濟效益的產業發展成為該墾區從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中的主導,導致該墾區各分局低質招商引進工業企業,加劇了墾區城鎮居民點低效擴張。
2.2 墾區主體功能定位與企業型城鎮化博弈
黑龍江農墾總局為提升墾區經濟總量與經濟效益,2008年以來全面推進墾區工業化、農業現代化、農場城鎮化。雖然撤生產隊并管理區或一般城鎮為墾區土地資源集約與開源奠定了基礎,但大規模的工業園區建設,尤其是中心城市、重點鎮建設所占土地與撤隊并鎮所增補土地并未形成動態占補平衡,甚至遠未達到國家對墾區主體功能定位的耕地及其后備資源的增量要求[5]。顯然,國家對黑龍江墾區的主體功能定位與作為市場主體的公司定位之間存在博弈,集中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黑龍江農墾總局及下屬各分局作為市場主體,參與經濟社會綜合競爭時必然面臨各類入駐企業、農場職工及外來務工者、上級政府等多重標準的評價,以農業生產為主體既不能創造較高經濟效益,又無法滿足墾區居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因此,推進農業現代化、墾區工業化是墾區發展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墾區農業化與墾區工業化,必然催生一批生產性服務業、工業等新生行業企業,這些企業需要集聚地,即現代城鎮,在此背景下,產業結構調整必然會催生城鎮化,為此如何落實國家主體功能定位成為墾區面臨重要戰略抉擇。
3 黑龍江墾區城鎮化質量調控的路徑選擇
3.1 著眼新型城鎮化實現方式轉型、人口市民化與產業結構優化
結合黑龍江墾區歷史時期城鎮化運行機制和城鎮化問題,認為黑龍江墾區城鎮化調控路徑有三:一是從體制框架中走出尋找市場主導的城鎮化方式,如針對墾區不同農業產業支撐的城鎮推進旅游城鎮、農業加工企業集群城鎮、分局管理與科技研發城鎮等模式的興起與可持續;二是實現“以人為核心”的“人的城鎮化”,即給予墾區非農場直職工及其家屬的全面社會保障待遇,全面推進墾區城鎮與居民點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人口的社會保障與勞動力素質;三是以農業現代化為主線,推進墾區工業化與農場城鎮化,即圍繞墾區“三農”問題優化調整農業加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生產性服務業等的內部結構與布局,提高產業的就業吸納率與生態環境保護效益、土地集約利用率和公共服務供給輻射范圍,從而實現城鎮化效率與增進社會福利的同步。
3.2 厘清墾區城鎮化制度障礙,健全城鎮化運行機制實現政府、市場與企業協同
墾區城鎮化的關鍵在于優化產業結構與土地集約利用的協調,這需要整合區域相關制度環境,破除或建立城鎮化的相關制約因素或激勵政策。黑龍江農墾總局作為國有企業,其治轄各農墾城鎮不具備相關政府權限,為此需要明確墾區城鎮的責、權、利,并開拓投融資渠道保障墾區城鎮基礎設施、社會文化事業等公共服務均等化。
健全墾區城鎮化運行內在機制,圍繞市場(農墾總局及各分局作為企業)、政府(國家農業部、黑龍江省)與墾區內招商的各類非墾區資本企業在墾區產業結構優化、吸納就業、創造財稅、土地集約利用等方面整合目標,實現三方合力轉變當前城鎮化方式,因地制宜的利用企業促進生產要素,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和墾區工業在中心城鎮集聚,讓地方居民與墾區各級管理機構更多參與城鎮化過程,提高墾區城鎮化效率。
4? ?結束語
黑龍江墾區作為中國糧倉,城鎮化發展面臨農業經濟主導、城鎮職能單一、企業型政府外力干預等顯著問題,亟需反思城鎮化發展脈絡、檢視城鎮化目標戰略。研究認為:墾區這一特殊地域系統的城鎮化調控理論邏輯是融合集聚經濟與集約發展、重視城鎮化效率與社會福利增進同步;新型城鎮化與墾區主體功能指引黑龍江墾區城鎮化質量調控實現路徑有二:一是轉變城鎮化方式實現人口市民化與產業結構優化,二是厘清墾區城鎮化制度障礙、健全城鎮化運行機制實現政府、市場與企業協同。
首先,墾區亟待探索如何轉變農墾總局及分局的職能,以統籌城鎮化發展戰略;其次,是面對墾區人口嚴重外流與高素質勞動力短缺困境,如何整合現有社會福利制度推進已有非農場職工市民化;再次,是墾區發展的根基——農地資源及農業現代化,也面臨快速城鎮化的建設用地侵蝕,集約利用土地亟需新舉措;最后,制約墾區城鎮化的核心是現有城鎮第三產業弱小、第二產業吸納就業能力有限,如何衍生與延伸農業工業化的相關產業鏈,實現農業工業企業集群發展,支撐墾區城鎮化等問題亟待通過墾區城鎮化質量調控破解。
參考文獻:
[1]李靜.三江平原墾區城鎮化過程與空間組織研究[D].長春:中國科學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2012.
[2]劉世薇,張平宇,李靜. 黑龍江墾區城鎮化動力機制分析[J].地理研究,2013,32(11): 2066-2078.
[3]劉錫榮.黑龍江墾區城鎮化建設回顧與展望[J].農場經濟管理,2013(6):14-17.
[4]李靜,張平宇. 三江平原墾區城鎮化特征和發展對策[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34(01):50-54.
[5]劉德忠,姜法竹.黑龍江省城鄉一體化的基礎:農民集中居住、土地集約利用[J].農學學報,2012,2(07):66-71.
[6]葉裕民.中國城市化質量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1,(07):27-31.
[7]陳明.中國城鎮化發展質量研究評述[J].規劃師,2012(07):5-10.
[8]郝華勇.城鎮化質量研究述評與展望[J].江淮論壇,2013(05):18-23.
[9]郭葉波.城鎮化質量的本質內涵與評價指標體系[J].學習與實踐,2013(03):13-120.
[10]李靜,張平宇.墾區城鎮化綜合閥安裝水平測度與比較分析[J].人文地理,2012(06):62-66.
[11]王圣云,馬仁鋒,沈玉芳.中國區域發展范式轉向與主體功能區規劃理論響應[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2(06):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