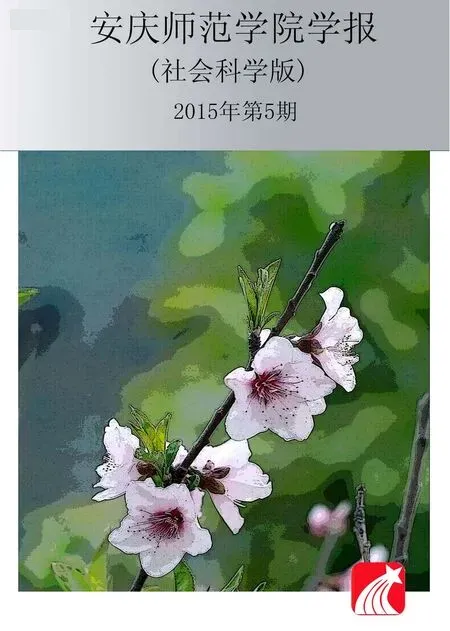太平天國時期蘇滬官紳安慶請兵述論
徐 偉 民
(安慶師范學院人文與社會學院, 安徽 安慶 246133)
?
太平天國時期蘇滬官紳安慶請兵述論
徐 偉 民
(安慶師范學院人文與社會學院,安徽安慶246133)
摘要:1861年9月湘軍攻克安慶后,應蘇、滬官紳的多次請示,曾國藩派遣組建不久的淮軍東援江蘇、上海。淮軍自安慶分三批搭乘蘇滬官紳以重金雇請的七艘外國輪船東下至上海,從此走出了安徽,迅速走上了軍事近代化的道路。
關鍵詞:曾國藩;李鴻章;安慶;淮軍;近代化
1861年9月5日,湘軍攻克安慶。于是蘇、滬官紳提請從安慶搬取救兵,剛成軍不久的淮軍隨即東援江蘇、上海。本文擬對蘇、滬官紳如何西上搬取救兵,淮軍怎樣東援蘇滬的過程及其影響做一探討。
一
咸豐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湘軍克安慶后不久,江蘇金匱縣知縣華翼綸一行三人自上海至安慶,拜會曾國藩,“言下游望余大兵,情甚迫切,又上海每月可籌餉六十萬兩之多,并言紳民愿助此間餉項,冀上游之兵早赴江東。”[1]670這是江蘇紳士的第一次請兵。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江蘇上海龐寶生派戶部主事錢鼎銘來安慶請兵,此為江蘇紳士第二次來搬取救兵。1860年,太平軍大舉進攻蘇南,錢鼎銘逃亡上海。1861年,當湘軍攻克安慶后,他即西上安慶乞求曾國藩分兵東下上海鎮壓太平軍。曾國藩于湘軍大本營里會見了錢鼎銘,以“吾無兵可分,他處乞援者終未一應”為托辭婉拒援救[2]94。二十一日,錢鼎銘又與曾國藩長談,“語次聲淚俱下,叩頭乞師,情詞哀迫”[4]94。此次安慶請兵,客觀上催生了淮軍的誕生,這是曾、李、錢等人始料未及的。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七,翰林院庶吉士范鴻謨又自上海來安慶請兵。這是來安慶的第三次請兵。所不同的是,范鴻謨是為故鄉請兵。其時省城杭州被太平軍圍如鐵桶一般,城內60萬人已斷糧多日,且已餓斃三萬余人。曾國藩當即寫信給左宗棠,催促其速速進兵援浙,算是對范鴻謨請兵的回應。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江蘇紳士錢鼎銘、潘馥復來請援,此為第四次來安慶請兵。此次至為關鍵,不同以往。第一,此次請兵,解決了李鴻章淮軍從安慶至上海所搭乘的交通工具問題。第二,淮軍搭乘輪船駛赴上海,故先前預定的淮軍從巢縣、和州、含山至江蘇鎮江的陸路行軍路線不得不隨之改動。第三,此次安慶請兵,江蘇官紳花費巨大。曾國藩在與李鴻章談及此次江蘇來安慶請兵一事時說:“其雇洋船來接官兵,用銀至十八萬之多,萬不可辜其望,拂其情。”[3]725
蘇、滬官紳之所以三番五次西上安慶請兵,是因為:第一,太平軍在江浙滬一帶猛烈攻勢迫使其不得已而為之。隨著九江、安慶相繼被克,湘軍在長江中上游處于有利態勢。但在江浙地區,太平軍一鼓作氣,連下丹陽、常州、無錫、蘇州、松江等地,建立了以蘇州為首府的“蘇福省”。李秀成所部太平軍則進軍浙江,于1861年下半年連克金華、處州、臨安、余杭、杭州,浙江巡撫王有齡被逼自殺。李世賢部則克港口城市寧波。
當太平軍席卷蘇南、浙江,進逼上海之際,上海的官僚、地主、買辦一片惶恐。其時,清廷無力在短期內剿滅太平天國,對外國又心深懷戒心,唯恐“借師助剿”不成,反引狼入室,自取其辱,于是密諭地方官吏指使買辦商人同洋商“自為經理”。“洋槍隊”即是在此背景下組建的。“洋槍隊”成立之初,在松江、青浦等地被太平軍打得潰不成軍,華爾本人也身負重傷。顯然,若靠這支烏合之眾不足以拱衛上海。于是,蘇撫薛煥遣上海道吳熙求援于英、法領事,請其派兵協防。上海毗鄰太平天國轄區,是中國最大的對外通商的港口城市,是西方國家商貿利益集中之地,多家外國使領館設立于此。英、法公使當即宣布他們將協助“保衛上海”,成立了“中外會防公所”,策劃防守事宜,之后,在上海增兵達數千人之多,并改“洋槍隊”為“常勝軍”,擴編至5 000人。有了英、法軍和“常勝軍”撐腰,蘇、滬官紳心下稍安,然相較于太平軍的優勢兵力,區區數千人的隊伍欲與之抗衡,無異于以卵擊石。無奈之下,他們自然想到了連續攻克太平天國兩座名城重鎮且遠在安慶的湘軍和曾國藩。
第二,曾國藩統帥的湘軍相較于八旗、綠營而言頗具戰斗力。當蘇、滬用兵吃緊之際,江蘇巡撫薛煥應蘇滬紳民之請,主張“借師助剿”。但曾國藩反對借兵助剿,認為借洋兵助守上海,確保此地中外人民生命財產則可;若借洋兵助剿蘇州等地,收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洋人之在滬者,恐不足恃。其與我和好,究竟唯利是圖。一有事機吃緊之時,往往坐觀成敗。若欲少借其力,必至要結多方,有情理所斷不能從之處。……洋人既不足恃,仍須該大臣酌派名將勁兵前往,方可萬全無患。”[4]2037-2038
在太平軍圍攻鎮江的緊急情況下,清王朝下令曾國藩派李鴻章率水陸軍從速增援鎮江的馮子材,“如能早行趕到,不獨鎮城可資保衛,亦可壯江北聲勢”[4]2042。可李鴻章遲遲未能起程。清王朝復下令派曾國荃率軍馳赴上海。安慶克復后,曾國荃即回原籍湖南招募湘勇,擴軍再戰。清廷的計劃是,李鴻章與曾國荃,一到鎮江,一赴上海,“則南北兼籌,壁壘一新,足以折服外國人之心,自可力圖保全,以裕餉源。”[4]2051
同治元年正月,面對同治帝及兩宮太后的屢屢催促,曾國藩對形勢的分析判斷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認為:“自古江南用兵,以鎮江為險要。目前局勢,鎮江尤屬必爭之地。若圖金陵,則俟鮑超一軍攻克寧國后,由東壩、溧陽進,而鎮即出兵會之;若圖蘇、常,則俟揚州一軍肅清江北后,由靖江、泰興進,而鎮江亦出兵會之。”“李鴻章統帶水陸,下駐鎮江,原為將來進取地步。惟鎮江現有馮子材、黃彬等軍,如果扼守得力,不須添換。李鴻章或移駐通、泰或駛往上海。”至于曾國荃一軍,“曾國荃新勇募到,擬進攻巢縣、和州一路,……未便遠赴上海,顧彼失此。”[4]2055這與清廷原來的預設正好相反。導致曾國藩態度改變的主要因素是曾國荃 “不愿往上海、恐歸他人調遣,不能盡合機宜,從違兩難”[1]690。于是,李鴻章便成了替代曾國荃的不二人選。但淮軍行軍路線如何敲定,開拔費用尚無著落等問題亟待解決。同治元年二月十九日,江蘇委員厲學潮至安慶,同時解來軍餉白銀8萬兩,使淮軍的開拔費用有了著落,行軍路線也隨之確定,“由巢縣、和、含陸路東下”[3]724,即陸路由巢縣、和州、含山再到鎮江(并非上海)。至此,有關李鴻章、曾國荃兩軍何去何從的問題已基本有個眉目了。這天二更以后,江蘇紳士錢鼎銘、潘馥復至安慶又來請援,請求曾國藩派遣李鴻章一軍由輪船徑赴上海(而非鎮江)。錢、潘的到來,使原計劃又將面臨新的變動。如上所述,曾國藩思考再三,決定淮軍由水路東下,直赴上海。
二
按照雙方商定的請兵計劃,淮軍將分三批駛赴上海。曾國藩在日記中記為每批7艘輪船,每批可載三千人左右,以此類推,淮軍駛赴上海的應為九千人左右。梁啟超《李鴻章傳》中記為“八千人”[5]18,據羅爾綱考證,認為淮軍編成時的人數“共六千五百人”[6]10,其中湘勇二千,淮勇三千五百,外加楚勇兩營一千人,共六千五百人。筆者認為 “九千人左右”之說較準確。
從曾國藩日記中可知,李鴻章的淮軍是分期分批東下的。第一批啟行日期定為三月初七日。除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隨江蘇請兵代表錢鼎銘、潘馥同來的火輪船一號外,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又有兩艘輪船駛至安慶,“洋船之來接少荃一軍者,本日又到二只。”[3]726按事先約定,輪船至安慶后,因淮軍登船前須稍作準備,須停泊三天(從初四至初六)。三月初七日一早,曾國藩親自來到碼頭為首批啟程的淮軍送行。第一批淮軍啟行日期確為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至此,通過蘇滬官紳的不懈努力,由曾國藩親自策劃的淮軍東援江蘇、上海的目標終成現實。三月十六日,曾國藩收到李鴻章從上海捎來的信件,得知李已于初十日抵達上海。據此分析,李鴻章應是乘首批運送淮軍的輪船一同抵達的。三月十三日,曾國藩又出城至洋船送淮勇樹字、銘字兩營啟程。三月十七日,送春字營、鼎字營赴滬。三月二十四日,送慶字營淮勇與鼎字一哨,林字二哨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送林字營淮勇。四月二十二日,送垣字營坐洋船至上海。五月初二日,送熊字營赴上海。五月十一日,送熊字營兩哨上洋船赴上海。總之,自同治元年三月至五月,淮軍親兵營、開字營、樹字營、銘字營、春字營、鼎字營、慶字營、林字營、垣字營、熊字營等十營淮軍先后由輪船運抵上海。這10營淮軍,除去曾國藩日記中有明確記載的親兵營1 300人、開字營1 300人,共2 600人外,其余8營,如按一營505計,則共4 040人,總計10營淮軍(正規軍)6 640人。
淮軍至上海的時間,按原計劃是“壬戌三月初七啟行,四月初一齊到,后隊水師于七月初旬亦到”[2]94。實際因輪船自上海始發時間早遲及中途可能遭遇的各種情況的干擾,至安慶的時間早遲不一,因而返滬有早有遲,并未完全依原計劃行事。淮軍至滬后,扎營于城西南三里許的松江來路上。至此,蘇滬官紳終于將李鴻章及其淮軍從安慶請到了上海。
三
淮軍從安慶開拔至上海,不僅是上海這個彈丸之地增添了一支攻防力量,其產生的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就連曾國藩、李鴻章本人均始料未及。
首先,此次淮軍自安慶搭乘輪船徑赴上海,不僅是對清廷先前淮軍由陸路馳至鎮江戰略設想的改動,且使清廷增援蘇滬的設想變成了現實,對未來剿滅太平天國的整個戰局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淮軍抵達上海后,其進攻路線是由下游往上游即由東向西進攻,而湘軍則是由上游往下游即由西往東進攻,對太平天國形成了東、西兩面夾擊的作戰態勢。在湘軍已克安慶的前提下,李鴻章的淮軍于1863年、1864年先后攻克蘇州、常州,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危如累卵。事實證明,淮軍徑赴上海,自東攻西,確為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略步驟。
第二,淮軍自安慶開赴上海,一方面,淮軍自此地走出了安徽,由閉塞走向了開放;另一方面,淮軍至滬后,充分利用上海各方面的有利條件,一變而成為一支近代化的軍隊,其后更發展演變成清王朝的國防軍,推動了中國軍隊的近代化。
淮軍是李鴻章受曾國藩所托于1861年底至1862年初在皖北開始招募的。淮軍剛至滬時,曾因裝備粗糙簡陋而遭到駐上海的外國人的譏諷嘲笑。“淮軍之初至上海也,西人見其衣帽之粗陋,竊笑嗤之。”[5]李鴻章卻不以為然,認為衡量一支軍隊,軍容嚴整與否當然重要,關鍵在于能否打仗,戰斗力強與不強。李鴻章督促將士日夜操練,時習修營浚壕之事,而不急于與太平軍一決高下。待訓練有素后,淮軍躍躍欲試,在虹橋與太平軍發生遭遇戰,并擊退太平軍;太平軍復大股來攻虹橋淮軍營盤,李鴻章親督各營再次打敗太平軍。經此小勝,上海的外國人不得不對淮軍刮目相看,李鴻章與淮軍的威望與日俱增。
淮軍至滬后,利用上海的有利條件,一改湘軍舊制,迅速“西化”,成為中國第一支近代化的軍隊。上海的關稅、厘金不僅是清王朝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而且是曾國藩湘軍、李鴻章淮軍軍需的重要生命線。充裕的餉源,使淮軍一至上海即有了向近代化邁進的堅實的經濟基礎,五口通商之地,對外貿易中心城市的地位使淮軍迅速近代化占盡了地利。淮軍至滬后不到兩年,即由原來的13營發展擴充到百余營。李鴻章到上海后,目睹了西方近代化武器的威力,痛下決心,把淮軍的刀、矛、小槍、抬槍各隊一律改為洋槍隊,使各營戰斗力劇增;成立6個洋炮營,使用的炮彈即是被李嘖嘖稱奇為“神技”的開花炸彈,其殺傷力較之過去的劈山炮大大增強。隨著洋炮營的設立,制造槍炮彈藥的軍事工業也應運而生。1863年,李鴻章設立了上海洋炮局、蘇州洋炮局,其后的金陵機器局、江南制造總局等軍工企業更使中國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進。隨著營制及武器裝備的改變,沿襲湘軍舊制,再也不適應時代的需要了,于是,李鴻章又在淮軍中改用西式陣法和戰略戰術,聘請了一批西方軍官來進行教練,淮軍迅速走上了軍事近代化的道路。
參考文獻:
[1]曾國藩全集·日記一[M].長沙:岳麓書社,1988.
[2]太平天國史料專輯[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曾國藩全集·日記二[M].長沙:岳麓書社,1994.
[4] 曾國藩全集·奏稿四[M].長沙:岳麓書社,1988.
[5] 梁啟超.李鴻章傳[M].廣州: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19.
[6]羅爾綱.晚清兵志[M].北京:中華書局,1997:2.
責任編校:徐希軍
中圖分類號:K254;E29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730(2015)05-0090-03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5.021
作者簡介:徐偉民,男,安徽太湖人,安慶師范學院人文與社會學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5-07-25
網絡出版時間:2015-11-11 10:42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1111.1042.0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