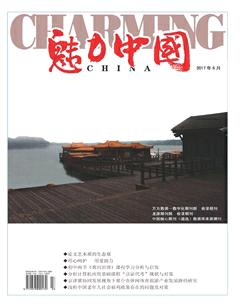基于生態安全保障的城鄉規劃思考
高淑玲++向發敏
摘要:本文由京津冀霧霾天氣和水環境惡化引出城市生態安全,簡述狹義城市生態安全及其與傳統規劃層次關系,分析廣義城市生態安全概念,梳理環境、物種、生命、城市等潛在隱患因子,提出基于生態安全保障的各類安全隱患因子的“規劃預案”。
關鍵詞:生態安全;城市規劃;隱患因子;生態系統
引言
近年秋冬季節華北地區霧霾天氣尤為突出,多數研究認為霧霾源于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汽車尾氣排放增加、能源結構不合理、基建房地產項目揚塵等[1]。同時,京津冀“水”生態安全也日益嚴重,如河川徑流利用率高達90%、水資源開發利用率高達123%、地下水超采和水域濕地面積不足原有20%等。筆者認為,除以上原因外,環境惡化更重要的是因為區域性人類活動擾亂的長期積累,“基底”(土壤、水體、植被等)相輔相成的體系遭受嚴重破壞。
一、城市生態安全
一般定義生態安全是人的生活、健康、安樂、基本權利、生活保障來源、必要資源和人類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脅的狀態,又細分自然、經濟和社會三方面生態安全子系統[2]。城市化進程中,生態環境退化和生態破壞及其所引發的環境災害和生態災難對區域發展、國家安全、社會進步的威脅越來越大;生態安全己成為國家安全、區域安全的重要內容[3]。筆者認為,生態安全是人類活動始終保持在自然生態系統自我調節能力的承受范圍狀態,應側重于原生生態環境。在城鄉規劃中對應不同生態本體環境,應該有生態保持、生態修復、生態建設理念;對應不同生態要素在不同的空間尺度都應持保留“原態”、“原生”的敬畏之心。
二、狹義生態安全與城鄉規劃
城市生態安全體系離不開區域生態安全保障的背景基礎,水、大氣都是區域性流動要素,土壤是糧食生產基礎,直接關系食品安全,必須在大區域、大范圍乃至全國范圍確保安全,因此生態安全不同于生態城市建設。生態安全核心在尊重自然生態系統功能的前提下推進城市開發建設,需要從區域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城鎮體系規劃、城市總體以及控制性詳細規劃,乃至城市設計、工程設計和工程建設過程中貫穿全過程。生態城市建設提出土地利用、單位GDP排放、碳排放、噪聲控制等控制指標,在一定程度符合生態安全保障工程技術應用要求。可見生態安全保障理念與生態城市建設理念又互不矛盾[4]、[5],前者是道法自然的系統性哲學思想,后者基于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的自我約束方式和理念。
三、廣義生態安全與城鄉規劃
蔣明君(2012)《生態安全學導論》認為,生態安全有更廣泛的含義,除自然生態安全外還包括生態系統安全和人類生態安全,可細分8大類22小類。安全隱患因子互成因果,最重要的是人類活動,特別是大規模聚集的城市人的活動,因此要通過城鄉規劃約束人類活動,抑制或減弱安全隱患因子的出現或破壞性。基于生態安全保障的城鄉規劃就是要為各類安全隱患因子制定“規劃預案”,針對前因抑制、威脅應對和災后修復不同階段,擬定方案。8大類生態安全具體為:
(一)環境安全。
涵蓋3個隱患因子,對應規劃事項分別為:全球氣候變暖→新能源體系在城市開發建設中的空間安排,區域或總體規劃擬定濕地、灘涂和森林保護;土地荒漠化→納入土地利用規劃或國土安全規劃;淡水污染→水生態系統保護規劃。
(二)物種安全。
涵蓋3個隱患因子,對應規劃事項分別為:物種滅絕→區域瀕危物種保護區劃定及建設規劃;物種入侵→城市生物群落建設;森林植被減→城市郊野公園、森林公園。
(三)生命安全。
涵蓋3個隱患因子,對應規劃事項分別為:人口規模→匹配城市人口規模的公共服務設施安排;貧困與饑荒→城市貧困救濟空間、設施與制度設計;疾病傳播→健康管理與城市空間結構合理規劃與設計。
(四)城市安全。
涵蓋4個隱患因子,對應規劃事項分別為:城市內澇→海綿城市建設與技術;地面沉降→區域規劃在地下水保護中的約束要求;空氣污染→生產生活能源結構與空間、步行空間系統規劃等;水系水質惡化→城市景觀與城市綠地建設系統性空間構建。
(五)資源安全。
涵蓋2個隱患因子,對應規劃事項分別為:水資源匱乏→城市給排水與水循環利用體系建設;能源匱乏→太陽能、風能在城市空間的安排和規劃設計。
(六)自然遺產安全。
涵蓋1個隱患因子,對應規劃事項:地質公園、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區域規劃對地質公園、保護區建設的約束。
(七)核安全與輻射。
涵蓋1個隱患因子,對應規劃事項:光、電和化學輻射→城市光、電輻和化學輻射的建筑技術創新。
(八)非傳統安全(除戰爭外)。
涵蓋5個隱患因子,對應規劃事項分別為:自然災害→應急避難場所規劃;國土安全→區域規劃與土地利用規劃的結合;食品安全→土壤修復規劃以及產業布局結構優化;糧食安全→區域規劃在保護農業生產空間的約束、現代農業與城市空間規劃;恐怖威脅→民族、地域文化沖突與城市空間規劃協調,城市應急安全保障規劃。
四、結論
基于生態安全保障的城鄉規劃就是自然生態系統與生物生態系統與城鄉空間有機結合良性發展理念,需要綜合統籌和多學科結合能力的支撐,從規劃管理角度講,與“三規合一”不謀而合,但基于生態安全保障理念的城鄉規劃需從更廣闊的角度評估和審視城市發展與人類活動對總體環境的破壞性,以更謙卑的態度對待自身能力和技術擴張。空間上城市生態系統與區域生態環境不可分割,城市生態安全有賴于“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大氣、水和土壤環境;時間尺度上,生態災難的“時間節點”都是由于某些潛隱患因子長期積累。因此基于生態安全保障的城鄉規劃不僅要對規劃學科體系和規劃管理制度重新構建,還有全局生態安全理念樹立。
參考文獻:
[1]李曉燕. 京津冀地區霧霾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生態經濟[J]. 2016(3):144-150.
[2]劉中梅. 大連生態城市建設中的生態安全保障法律機制探析[C]. 遼寧:遼寧對外經貿學院. 2006.
[3]張良. 區域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方法與評價研究[D]. 天津:南開大學,2008.
[4]王云,陳美玲,陳志端. 低碳生態城市控制性詳細規劃的指標體系構建與分析. 城市發展研[J]. 2014(1):46-52.
[5]仇保興.“共生”理念與生態城市. 城市規劃[J]. 2013(9):9-17.